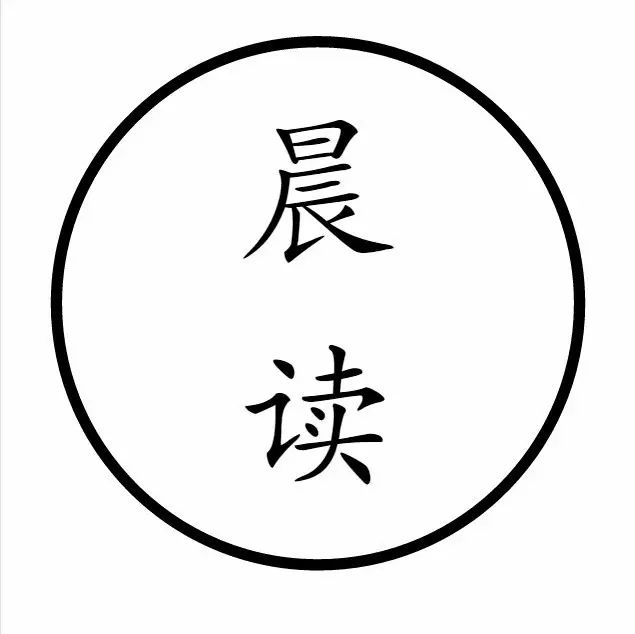这
个幼儿国学班我闻名已久:每周末上一个头午,前半年不收学费,主要规则是家长必须和幼童共同听课,一节课不许缺,假如孩子发烧高热之类,可以宽免,但家长必须要来。没想到我有位朋友真坚持了半年。所以很满足地说:我家也缺过一堂,差点儿被清退了,幸亏动员了社会关系去疏通,暂缓了处分,现在正留观察看。如今,这个国学班已经很难进,再报名需要父母都到场,检验孩子是否“全福人”、阖家能量正不正,才能于员外候补;纪律改为父母都要听堂,派截辈人听课不行。我问这班的买卖怎么样。朋友不大高兴,说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中午还管一顿饭呢!
我未免有点儿惊讶,像我这种脏心烂肺、没怎么在外闯荡过的人,实在是猜不透这里的营利模式。如果说就是单纯地既喜欢做饭又爱弘扬儒家文化,我虽然没闯荡过,也不信。我又问这国学都怎么教呢,说是主要靠背,《三字经》已经不到半年就背完了,现在正在背《孝经》。这倒是常见,自台湾开始,国学班大多遵循“默而识之”。按说,读经不讲,如种地不耪,拿一个白本看,是方家才有的本事。可本地的国学大师们真要讲,恐怕讲得还不如于丹教授;就算真讲得跟于丹似的,可也不怎么值钱呢。
我不免还有点儿担心那位朋友,他家嫂夫人是搞化妆品传销的,那家公司很绝,谁碍于朋友情面订购一次,下次就会被要走信用卡和身份证号,之后按月划账。推销这生意的女士们,专捡身边人下手,热忱都像是度人,利用我们感情的一种逻辑谬误——骗人的不算不够朋友,能狠心不上当的才算。我猜她迟早会触犯“相见相,隔一丈”的行规,在人家圆好的场子里发展下线。
一处理中年危机比我体面得多,周末跟朋友去做礼拜。我记得我国关于宗教自由的法令与老傅论婚外恋差不多,大概是“有信的自由,有不信的自由,有信你的自由,有信祂的自由,有过去信现在不信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现在又信了的自由”,何况纵然没有政策,我也不敢管,只是问问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基督教的哪一派,是教会还是团契,以及中午还回不回来吃饭。
她像个真正的改革者一样回答说:“那谁知道,先看看再说吧。”
回来后,她先是感叹那位朋友多才多艺,能讲、能边弹风琴边唱、能打非洲鼓,然后说了点儿顾虑:今天听到的事儿,好像都和信仰无关。并不是由哪一章、哪个话题而来,而是凑在一起讲各自见证的神迹。我问如此说来是天主教么?她说也不是,她虽然看到的是红十字,但她的朋友坚持说“我们这不是宗教,而是信仰”。
神迹的结构一般是这样的:某姊妹产检时发现胎儿有先心病,大夫建议不要生,姊妹和娘家姥姥都说这是神的孩子,必须生下来。生下来之后,虽然确实是先心病,然而,在教友们的祈祷下,孩子很快痊愈了,如今很健壮,可见是神迹。啊,对了,祈祷的同时,还做了十来个小时的外科手术来着。她说,这也不是信仰啊,这不就是愚昧么。我想这事儿从教徒的角度大概解释得通,就说你再讲一个。
她说还有一种,不是他们亲历的,是从哪儿读来的,比如说,某个台湾黑社会老大,在被警察追捕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向上帝求助,默念说你要是让我躲过这次,我就带着小弟们全都信你,果然他躲过了追捕。一愤愤地说,这黑社会倒是高兴了,那些被他祸害的人呢?这种事儿,有一点儿道教的意思,不过道教和巫术可以直接用现世的物质抵偿,以“信你”做交换,也可以视作基督教的原始状态吧,你再说一个……
“没有了,都是这玩意儿。我下礼拜不想去了,该怎么和她说呢?”她扒着刚才发的香蕉问。我的建议是不妨再去两次看看,也许只是针对你这样新来的人,才特地由浅入深、从现象到本质。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大多自幼学得是“嘴上信”,到能够做到自主“不信”,已经不大容易,再到“信”,恐怕是时间和道路已经不够了,或者与空间无关,根本就没机会,但是能够目睹一些,总算是灵魂上多了一种可能。能活信活用,得是林彪那样的大才,然而才大,祸事也大。“国学”之中,真正至今还有心理现象的,能马上想到的只有“不可一日无父无君”,但必须是现实中的、能直接降下灾祸来的君父,所以,宗教想不说现象神迹而直接谈精神,和搞对象想不提钱一样困难。任何宗教要在中国发展,都得多少与道家或巫术苟合,科学越发达,竟然越是如此。何况,你拿了人家这么多的香蕉,还有挺厚的一本书,只去这一次,有点儿说不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