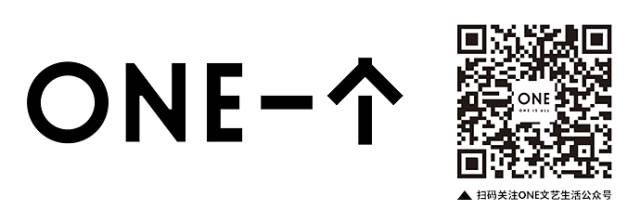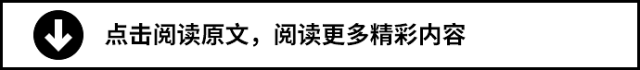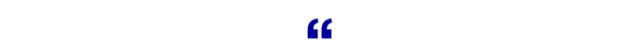
如果你想把某个地方当成故乡,就在这里谈上几段恋爱,再试图忘记几个人,然后它就会真的变成你的故乡。


爱德华•诺顿:
你好呀。最近我所做的,是推倒我心里一堵又一堵的高墙,我原本以为推到后,只能见到一片荒原,和几个零碎的句子。但意外地,我却见到了真理。推倒那些墙后,我走在路上,时常听到真理在耳边回荡。走在路上的人谈论着、电影里播放着、广告墙上用粗大的黑体字写着,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以前就看不到呢?
后来我知道,是因为在言辞里表达真理,就像用一台有故障的发报机发送密码情报,总是不能确定怎么才能被收到。诺顿,现在,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阿兰•德波顿说的,他真是个聪明人。不过还好,现在我已经陆续接受到了某些关于真理的密码,也在正确地破译它。
诺顿先生,如果真理说的没错,我将在八月梦到你。你敲了门,我开了门,你和我谈论起门口的鞋子。如果我醒了,有人在敲门,那我打开门,我就会看到你。最近我参加了部分社交活动,谈论起很多事情,我坐在饭桌对面,不时点头。
当个人主义、沟通霸权、语言碎片日常化,回应变成表演,人们一边走神一边赞许,一边收拾车钥匙一边说真有趣。有人曾告诉我,我们倾听不是为了回应,而是为了理解。我想这很对,人表达的永远不是他所说的内容,而是渴望被理解的心情。诺顿先生,你看,我破译了一些密码。
我住的楼层很高呢,诺顿先生。深夜偶尔会挂起很大的风,风呜呜叫的时候,窗棂响动,总会有点吓人。我不再深夜出门散步了,开始读很多书,深夜在书房里,做满了笔记。我交替读着,读了某本小说的开头,跳到了另一本指南的结尾,在不连贯的阅读里,找到到某种延续,这对我来说是种特别的体验。我以前无法在咖啡馆里看书,但是现在,一小段的空闲时间,我都能随地翻出一本书来,专注地读上几页。我想要是你知道了,肯定会鼓励我。
有人曾告诉过我,如果你忙到停不下来,就不会再想起任何人了。诺顿先生,我尝试让自己更忙。对你而言,北京是个陌生的城市吧?一个所有人说着陌生语言的地方。如果你想把某个地方当成故乡,就在这里谈上几段恋爱,再试图忘记几个人,然后它就会真的变成你的故乡。我想北京也是我的故乡吧。
诺顿先生,我最近对温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识了一位很厉害的辩手,头脑灵活,巧言善辩。我猜想辩手的脑部回路,大概和普通人真的不一样。他们可以一边监控表达的内容,一边检查着对方的反馈,及时调整,最后压倒性地说服对方。
后来有个厉害的辩手告诉我,他人生最温暖的事,就是看到这群长袖善舞的人突然变笨了,只有在他们爱的人面前,他的大脑会逐渐停止活动,变得钝钝的。
我不仅破译密码,也努力突然语言的边界。在语言学中,有句很著名的话说,“能被表达的,才能被看见”。我琢磨这句话真是厉害极了。我想,我只能写下我可以表达的真理,但那些看不见的真理,就真的不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正在奋力突破语言的边界,用一种清晰的、宽阔的方式来表达和接收真理。关于人生,我不停地发问,不停地学习,随着那一堵堵的墙倒下,我不知道会去往什么地方,可是诺顿先生,我现在有了些勇气,于是我并不害怕我要去的地方。
人生是未知的,但自我是可知的,这让我觉得安全。 `
最近我不仅开始学习探索真理、温暖的边界,也开始逐渐确认幸福。这是从我睡了一个漫长的觉开始的。以前我起床的时候,总能大概知道醒来的时刻是几点,但是现在,我能睡的很熟,熟到起床的那一刻,忘了此刻是几点。某一天,在南方吧,在漫长的午睡醒来后,老旧的空调正在嗡嗡作响,窗外的游泳池里蓝色的水面折射出金色的光,我推开窗户,热风与宁静,屋里的人还在睡,而那一刻,我确认了某一种幸福。
有时候我想起小时候穿着背心和短裤,在燠热的南方午睡醒来的后,走在滚烫的柏油路上,穿着塑胶凉鞋,捏着几毛钱去买冰棍的时刻,那时候时间似乎很长,冰棍像冻硬的糖水,又想起在暑热渐消的傍晚,拿起水管冲洒屋门前的水泥地,还有在树下,老人们点燃艾草,在竹床上纳凉的时刻,关于夏天,记忆里似乎都和幸福有关。 那到底是为什么,世界变得那么陌生又可怕了,夏天并没有变,是吗?
诺顿先生,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吗?我总是害怕,觉得世界巨大而陌生。但在这个夏天,我学习到了如何去碰触它。我们触碰世界,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当我开始认识自己,学习某种确认的方法,世界就在我眼前清晰起来。这世界,不过如此,我变得安全起来,能在很多时候睡个好觉。
是的,睡个好觉吧,诺顿先生,这世界并没什么好怕的,不是吗?
您东半球官方指定唯一的女朋友
苏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