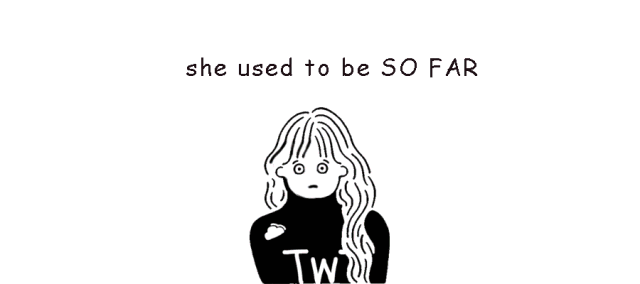
“我从来不敢让爸妈知道我的生活费一大部分被用来还花呗了。”
说出这句话的小A同学,刚刚用花呗分期付款,拍下了一双球鞋。
小A同学每月的生活费是2000元,在同龄人中,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自从有一天,他获得了5000元的花呗额度之后,他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了。
“以前舍不得买的一些球鞋和衣服现在可以用花呗分期付款了,而且付款之后,银行不会给我发来提示余额的短信。感觉自己的钱是够花的。”小A一边说,一边翻看手机。
“可是每月的9号,简直是审判日。还不上就只能继续分期。”他苦笑着说。
“其实,花呗使我更加贫困。”

小A看起来有吃有穿有玩,生活光鲜亮丽,可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他超前消费的基础上。
而“本月买,下月还”的消费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入不敷出”的窘迫,使得小A是“隐形的贫困”。前不久,新世相这个公众号推了一篇描述“隐形贫困人口”的文章,紧接着,人民日报跟进了一篇评论,使得“隐形贫困人口”成了舆论热词。
“隐形贫困“之所以隐形,说白了,是因为消费需求远大于实际消费,但总是大于收入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根源无非是”消费主义“四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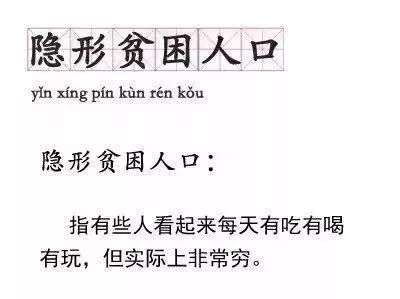
本文在探讨消费主义及消费文化的时候,仅仅是从社会宏观层面来探讨消费主义的运行逻辑,而不针对个人微观的消费行为。
 “我喝的是咖啡吗?我喝的是环境。”
“我喝的是咖啡吗?我喝的是环境。”
“护肤品、化妆品、控制饮食、健身”,这是当代新中产阶级的四大消费符号。而作为中产阶级预备军的大学生,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及营销号的指挥下,也渐渐认同并接驳这种生活方式。于是,我们便可以提出消费主义的一个侧面。即消费主义是一种“符号化”的消费。
什么是“符号化”的消费?在让·波德里亚那里,它指的是消费物质产品之余,更多的是消费一种价值观产品。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消费过程中,无疑是对于消费符号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认同,乃至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重塑。
举个例子,对于现在的大部分都市白领而言,买日用品去无印良品,买家具去逛宜家,每周健几次身来keep fit,吃牛油果沙拉,每天去星巴克坐一坐……这些碎片化的消费行为,渐渐拼凑起都市生活这个宏大的图景。

消费是都市生活的主题。都市的庞大躯壳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消费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都市的文化与价值观认同,大多数都是建立在消费之上的。而作为都市生活的主力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蕴含的价值观,往往是资本细细打量的对象。
所以,针对中产阶级量身打造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区别于小饭馆、小商店的原始简陋的精装修与规范化运营,满足中产阶级与“不健康、没品位”的生活方式划清界限的心理;丰富的文化附加和独特的品牌风格,满足中产阶级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就迅速成为都市生活的主流。
 “消费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消费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偶尔见到一些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文章,往往高发于各大“购物节”前后。他们的观点大多给人一种尖锐甚至偏激的感觉,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呼吸了太久的消费主义空气。
消费文化是当代都市文化的主流。在新世相的推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新的消费观与消费行为赋予青年的那种青春的活力,确实是一种和父辈们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并构成现在的时代风貌。而在人民日报的评论中,消费行为也被定义为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点。
消费主义的平权内核也是值得关注的。
举个例子,今年天猫在“女王节”的营销活动中,打出了“不做小公主,活出女子力”的大旗,就是消费主义平权内核的体现,虽然最后呈现的效果令人啼笑皆非。而在一些营销号的宣传中,不乏“你是独立女性,应该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的论调。当然我们要指出,消费主义对于男性的改造与影响,运用的是同样的手法。

但是消费主义能扛起平权的大旗吗?消费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缓解生产过剩的工具,而并非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一些营销号、美妆博主、时尚博主在启动宣传时,往往会坠入一个强行制造性别分野和性别对立的怪圈,例如什么“直男问卷”、“直男审美”。在这里,“直男”明显是对传统男权视角的简要概括,但是这种景观化的对立往往会催生新的性别刻板印象。藏在背后的资本和营销号幻术师操纵着这一切,隐藏起平权的真正价值,而用新一轮的物化去抵抗物化。
盆满钵满之后,留下一地鸡毛。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要买买买啊”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要买买买啊”
消费主义的运行在于通过贩卖焦虑来制造需求,建构起一套“生产-消费“的新逻辑,并通过贩卖价值观产品来重新建构并固化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脱离了消费本身,是一种对价值观的认同和对生活方式的共情。
进一步讲,消费主义是通过构建一种肌体完整、逻辑自洽、无懈可击的消费文化,从而把每个人笼罩在迷雾之内。消费文化寄托在物质产品之内,和不同的亚文化圈子互相体认,从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