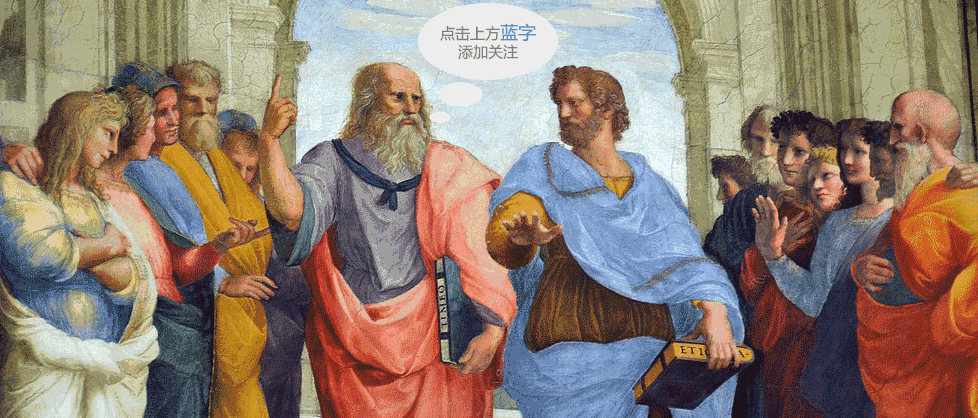
“
政治科学
”
之
“
家园
”
——
北美访书记
《政治思想史》书评,
2011
,
03

一、托克维尔和阿隆
记得我曾在自己的一篇
“
部落格文字
”
中
“
追忆
”20
年前在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求学时节之某个清晨,于现已改为上海书城的那家新华书店购得商务绿皮《论美国的民主》时的狂喜心情,这其中的一个原委乃是我此前反复在我们位于万航渡路的院图书馆借阅此书的
“
美国丛书
”
版而未得。
1993
年
4
月,我北上津门考学,事毕顺访京城,和其时已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大学室友李传新同学在琉璃厂闲逛,并在那里
“
邂逅
”
了其实早一年就已经出版的已故冯棠先生所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精装本,其书印数仅
2,000
册。无可讳言,新时期以来,托克维尔在中文法政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一直处于一种
“
不温不火
”
的状态,我无法对此给出一种深层诊断或深度解读,而只能
“
形式主义地
”
认为此种
“
不温不火
”
也许正是与托克维尔本人的思想特质相称的。我也只是在多年前的《两种自由的分与合》一文中引用过他,而这种征引还是通过一位
“
名不见经传
”
作者的《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一书,这位作者在他的这本有一个非常恰如其分标题的书中把托克维尔的自由概念解读成三个层次:个人权利、公民管理自己的权利,尊重法律的命令,以及由宗教教义赞同的一种做好事的责任。我其时这样引用托克维尔其实只是为了
“
先入为主
”
地
“
证明
”
像泰勒这样的社群主义者对前者的反复引证只不过暴露了他们自己对于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
依违其间
”
的态度,虽然我那时
——
一定程度上包括现在
——
并不清楚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究竟是什么,我现在大概会认为这个理念就是
“
自主性
”
,而我那时只能确认那一定不能就是
“
消极自由
”
!
话说我虽非托克维尔的研究者,但我对于他确实是有一种
“
特殊的情感
”
,这种所谓
“
特殊的情感
”
乃是与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那么重要甚至塑造了我们的
“
认同
”
、但并不需要我们去刻意惦记培植、却又会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涌现奔流在我们面前的那些令人眷注
(attachment)
的东西相关的。因此,当我在全店的书排列起来有
15MILES
长的
STRAND
的书架上见到托氏全集主编者迈耶
(J.P.Mayer)
的《托克维尔传》
(Alexisde Tocqueville,A Biographical Essay in Political Science, translated
by M.M.Bozman and C.Hahn, NewYork: The Viking Press,1940)
时,我确实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而当即就决定把它收归囊中了,其时它在
STRAND
应当已经躺了快有半个年头。顺便说一句,如果要我从此行所访求到的全部书籍中挑选出最珍爱的
5-10
种,那么这个其实只有
233
页而看上去却有四五百页的蓝布精装本子就一定是名列其中的,我正是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
FRIENDCENTRE
与我朝夕相伴的那幅大概堪称托克维尔最著名的漫画像之
“
出处
”
,而出版此书的这家
Viking Press
就是后来阿伦特《论革命》的初版发行者。
据迈耶在此书导言中说,在他
1939
年写完这本书之前,托克维尔的思想在整个西方世界也并未引起多大程度的重视和兴趣
———
至少是重新解释的兴趣。此前只有勒迪耶
(AntoineRedier)
的一本题为《托克维尔如是说》
(Comme Disait M.de Tocqueville)
的法语著作在这个领域有创榛辟莽之功
———
勒迪耶在
1925
年不无讽刺地把他的书题献给
“
所有那些迄今不知道托克维尔的人
”
。不过迈耶却注意到他的同胞德国哲学家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早在
1910
年就称誉托克维尔是
“
自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以来最卓越的政治分析家
”
,但这位
“
对于西方民族的智识史根源具有莫大权威的战前德国思想家
”
的言辞却无人问津。迈耶似乎没有详细谈论托克维尔思想遭到忽视的根本原因(我猜想社会主义运动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风起云涌一定是一大因素,阿隆的这句话似乎是对此的一个
“
旁证
”
:
“
在社会主义传播之前,托克维尔关于走向地位平等的运动不可抗拒的论点,同阐明野蛮的资本主义和无产者的起义并不相悖。
”
),但他明确指出,
“
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政治经验,特别是所谓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无疑使得重新审视托克维尔的政治和社会告诫变得迫切了。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都根本不了解现代民主大众社会的现象
”
。迈耶认为,就如同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城邦的政治哲学家、西塞罗是罗马共和的政治哲学家、阿奎那是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是
16
世纪绝对主义的政治哲学家、洛克是
1689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是首位揭示大众民主时代之原则的政治哲学家。
这些看法当然是
“
卑之无甚高论
”
,不过我觉得除了题为
“
沃尔特
·
白哲特论路易
·
波拿巴
‘
政变
’”
和
“
亨利希
·
海涅作为托克维尔的同代人
”
这两篇附录,至少就中文语境而论,迈耶这部传记之题为
“
遗产
”
的最后一章是写得颇为
“
出彩
”
的,特别是其中谈到托克维尔之
“
潜在影响
”(subterranean
influence)
时所抉发的那个线索。
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常识的读者都可以理解,至少在
“
新时期
”
以前,托克维尔在中文政治思想史领域中的
“
尴尬地位
”
乃是由于马克思曾经在《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点过他的名。迈耶对这段
“
公案
”
及其
“
余波
”
的处理在我看来
———
特别是结合我一直以来的某些关注点
———
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颇值得玩味的。根据迈耶的考察,上述所谓
“
潜在影响
”
在蒲鲁东那里特别清晰可辨,并通过蒲鲁东影响到马克思,而在乔治
·
索雷尔那里得到最为显著的表现。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觉》中证明,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受到了托克维尔所表述的平等原则的启发,而他的处女作《什么是财产?》则体现了《论美国的民主》的影响。《神圣家族》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熟悉《什么是财产?》,而马克思更是在《哲学的贫困》中猛烈批判了蒲鲁东和托克维尔共享的平等原则之
“
天命
”(providential character)
。迈耶认为,这种口诛笔伐同样适用于托克维尔,因为
“
马克思并无意于追溯蒲鲁东命题的来源
”
。针对《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
———“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认为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来代替过去各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否认后一代人改变前一代人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
”———
迈耶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托克维尔本人也不会否认,于是问题就在于蒲鲁东对托克维尔的理解是否正确。值得注意的是,迈耶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虽然
“
雄辩
”
但确实有些
“
大胆
”
的断言:
彼时,《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具有比马克思更为广泛和透彻的历史知识,而且意识到
———
马克思则没有
———
西方历史中的平等趋势出现于
中世纪晚期,而不是首先出现于
19
世纪
……
平等原则的天命植根于托
克维尔的宗教观,这种观点把人类看做上帝的自由和平等的造物。民主是一种天命只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本人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描述成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秩序。他没有像托克维尔那样看清,就原则和目标而言,他的社会哲学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
如果我们回到揭示大众民主时代之原则这个首要任务,问题的实质就会看得更为清楚。这里最好还是用迈耶的原话:
大众的兴起已经植入到我们人类的命运中。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既是一种预言,也是一种责任,还是一种警告。他与他那个世纪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有这种责任,因为这种责任也被像歌德、雅各布
·
布克哈特、尼采、索雷尔和马克斯
·
韦伯感知到了。也许马克斯
·
韦伯的工作为托克维尔对于问题的表述提供了最适当的重述,差别仅仅在于看待问题的一种更为普遍的视界
———
因为韦伯也考虑了东方文化
———
也在于对于一个已经脱魔的时代之清醒凝视。
韦伯被引入这幅思想图景使得迈耶对于托克维尔之
“
潜在影响
”
的追溯更形丰富完整,正是在托克维尔、马克思和韦伯的这种复调
“
对话
”
中,托克维尔所谓平等或民主的
“
天命
”
这个现代大众民主时代最深刻的谜题才能被揭开或者才能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迈耶一方面断言,只有把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智识成就冶于一炉,才能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奠定全面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告诫,他对于托克维尔之政治哲学的解释不应当被误解成是要独断地采用马克思的立场来寻求对前者的一种必要的校正。这是因为,在迈耶看来,马克思虽然开启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一种经济学批判,但却没有很好地理解现代大众国家的制度和政治组织问题。沿着这个路径对马克思的
“
批判
”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无需在此详细复述。不过,我们确实不能不认真面对由此所提出的所谓政治精英的难题,因为迈耶同样认为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弱点恰恰在于他回避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托克维尔在致密尔的信中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最后把它的解决归之于
“
现代民国
(nations)
的命运
”
。在迈耶看来,从托克维尔的前提看,他提出问题却又无法解决问题乃是最自然不过的,因为作为政治精英的贵族已然消亡,而从缺乏政治德性的资产阶级脱颖而出的政治精英在托克维尔看来乃是一种用语矛盾
(contradictioinadjecto)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迈耶认为索雷尔那种无产阶级精英的理论可以说是从托克维尔的前提得出的
“
逻辑结论
”
。
其实迈耶当然并不信服索雷尔的无产阶级精英论,他不无调侃地用
“
力不从心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resh is weak)
来形容抵御资产阶级诱惑之困难,并最终在他的《托克维尔传》中把自由的设准与现代平等的大众社会相调和作为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政治哲学家们所献身的一个未竟课题。
迈耶生于
1903
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抵抗过纳粹、又遭受过纳粹的迫害,利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期间纳粹反犹政策的放松逃到英国,在把几乎毕生的精力献给托克维尔著作的整理和研究(他还在英国的雷丁大学创立了托克维尔研究所),并在亲眼目睹冷战结束之后于
1992
年以九旬高龄谢世。我们不知道从
20
世纪
30-40
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复兴托克维尔研究的迈耶对于
70-80
年代后以雷蒙
·
阿隆为主要推手的托克维尔热会作何感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阿隆似乎仍然接续了迈耶那种通过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相互比较来阐发现代社会之自由问题的框架和思路。阿隆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就叫做《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这篇文章收在他的题为《论自由》的小册子中。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在
STRAND
得到的两个阿隆选集
(Politics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by Raymond Aron, collect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riam Bernheim Conant,
NewYork:FreePress, 1978; History, Truth, Liberty, Selected Writings of Raymond Aron,
edited by Franciszek Draus with a Memoir by Edward Shil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都收入了这篇文章,但却有两个不同的英文标题,除了《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外,另一个标题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定义》。不过在谈到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简要介绍一下阿隆的《重新发现托克维尔》一文。
阿隆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
革命后社会
”
,他认为
“
选择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结果作为中心课题
”
的托克维尔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思考革命后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社会的,而马克思也是把革命后社会作为自己主要的甚至排他性论题的。之所以要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就是因为
“
今天的自由欧洲在许多方面更像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欧洲,而不是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积累所预言的那个欧洲
”
。从这个意义上,阿隆把托克维尔身后的
“
时来运转
”
主要归功于历史的
“
峰回路转
”
。阿隆如是说:
“
对于我们这些饱受马克思主义浸淫的人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
资本主义复苏时期被重新发现的托克维尔身上看到的令人感到焕然一新的东西,恰恰是对于以社会平等和政治自由为中心的历史的思辨,而不是关于阶级斗争或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思辨。
”
正是基于阿隆将其定位于西方思想之核心的自由-平等的辩证法,《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一文集中论述了托克维尔的三重独创性:第一条是按照条件的平等,也就是根据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来构建社会;第二条是对历史和将来采取一种或然论的观点;第三条是拒绝把政治从属于经济。阿隆这里强调的重点在于,一旦用社会意义上的民主定义替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定义,就必须交代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关系。如果说孔德和马克思由于把政治制度归结为社会地位的产物或上层建筑,就切断了与古典哲学的联系,那么
———
还是用迈耶在《托克维尔传》中比较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时的说法
———
在托克维尔的世界观中,却还是把政治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
法律、制度、情感、激情、观念以及宗教、道德惯例和信条乃是无法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
”
。缺少一种政治结构之整体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论会被托克维尔当做一种
“
不能接受的抽象
”
,那么最好还是让阿隆本人来现身说
“
托
”
:
各种事件不论大小,今天无不给托克维尔增添光彩。有谁预料到起源于贵族的代议制机构在
“
先进的工业社会
”
中依然是个人自由的唯一的最好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铸造了特定的大西洋的团结,把欧洲民主与美国民主之间的比较提上了议事日程,从而也就把托克维尔的著作推上了前台。我力排众议,将这篇评论拟了一个
“
重新发现托克维尔
”
的标题,不知是否有道理?(阿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载《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二、尼布尔,尼布尔
我是从何时开始记住莱因霍德
·
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这个名字的,现已不能确记了。近
20
年前,我在杭州大学这所
“
名校
”
念博士学位时,曾在系资料室
“
借而不阅
”
港版
“
历代基督教名著集成
”
中的《人的本性与命运》。我的同事包利民教授兼治基督教公共神学,多年前我和他
“
不约而同
”
到浙大玉泉教工食堂共进午餐时曾有多次听他聊起尼布尔的重要性,有一次他还建议我把《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列入我那些年爱
“
张罗
”
的丛书中的某个系列。正所谓
“
近朱者赤
”
,或者也要归因于尼布尔本人影响之巨,当我的访书行程
“
尘埃落定
”
时,检视之下,竟发现尼布尔的著作也有不少种跑到了我这个其实对基督教神学和社会思想甚少素养
———
这说起来当然是件有些令人汗颜的事
———
的西学从业者之行囊中。
话虽这么说,我之所以能够在访书历程中开始注意尼布尔,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的。记得我刚到普林斯顿时,就发现这个如
“
世外桃源
”
般的小镇的一个最大
“
缺点
”
恐怕就在于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用说好的旧书店了;我只是在靠近那个著名校门的大学生活动中心的一个兼营
“
文化衫
”
的
“
卖场
”
中,找到一家二手书店。于是,每当夜幕降临,客居异乡无佳处可去而又不能常在租住的陋室中
“
闲敲棋子落灯花
”
的我就常常会到那家书店转悠,并一早就在那里发现了尼布尔的早期作品《一个温顺的愤世嫉俗者之笔记》
(Leaves from the Note book of
a Tamed Cynic, Westinster/John Knox Press,1929/1990)
。坦率地说,除了尼布尔的大名,吸引我的主要还是书名中的
“tamedcynic”
这个听上去有些
“
吊诡
”
的词组!但从那以后,我竟于不经意间开始有些留意起尼布尔的著述来了。
2007
年深秋,正是波士顿红枫盛开的时节,我在时在哈佛访问的张国清兄陪同下来到哈佛广场附近一家甚有
“
品位
”
的旧书店
———
因为这家书店中有些罗尔斯生前用过的书(是在
“
寄卖
”
?),国清戏称之为
“
罗尔斯书店
”
。除了得到《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精装本,我还在这里拣了一册《尼布尔精要》
(The Essential
Reinhold Niebuhr : Selected Essays and Addresse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obert
McAfee Brow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编者布朗在为这个选集所写的导论中把尼布尔称做
“
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a pessimistic optimist)
。布朗承认,在不熟悉尼布尔的读者眼中,
“
悲观的
”
和
“
乐观主义者
”
这两者的组合听上去确会有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