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群学君
老话说,冬至大如年。古人认为“冬至阳生”,天地阳气日渐兴盛,意味着下一个时间循环的开始,乃大吉之日。从前的冬至有滋有味,裹在淡淡的烟火里,藏在小小的仪式里。
冬至前夜,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总是琳琅满目:蛋饺、蹄髈、鲈鱼、羊糕四色节菜固不可少,一杯清甜的冬酿节酒,更体现了几百年来所谓“肥冬痩年”习俗。
不过对我来说,冬至当令,最想念的,却是一碗腌菜笃豆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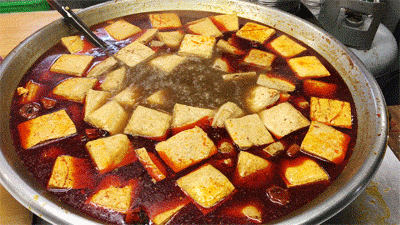
说起来,最能体现中国人文化品格和精神涵养的“国菜”,大约就是豆腐。既是清寒人家的恩物,也是高门大宅的清品,雅俗共赏,左右得道,举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很少买不到豆腐,不爱吃豆腐的中国人,也少。
一百年多前,高阳李石曾先生在巴黎创办豆腐厂,用新法制造豆腐,一时名声大噪,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在耶稣降生前很多年就发明了豆腐,真可算得文化史上的奇迹。
康熙年间,河南人宋荦七十多岁跑到江苏来做官。皇帝南巡,在苏州召见这位号称“天下清廉第一”的巡抚,体恤他老成忠厚,让御膳房的司厨太监密传了一道豆腐锅子给巡抚衙门的勤行,“日日受用,可以益寿”。只是这道看似寻常的豆腐火锅,却是靠了十几种山珍海鲜吊味,岂是一个薪俸微薄的“豆腐官”可以消受起的?
慈禧当朝,民间传说御膳房四十九口蒸锅昼夜炉火不熄,每口锅里都是镶着珍珠的豆腐,四十九天而珍珠软嫩如豆腐,这样老太后每天吃一块“珍珠豆腐”,这就是她吞珠食玉,驻颜有术的秘诀。
及至民国,南北的知名菜馆,以豆腐为招牌的不在少数,北平同和居的砂锅豆腐、奶汤豆腐,杭州楼外楼的鱼头豆腐,都是名荐。
东北百姓,把萝卜缨切碎了,腌成腌菜,用来炒小豆腐,清爽脆嫩。到了华北,每逢秋末冬初,用葱花、咸菜丁、肉丁、虾米皮和豆腐同煮成糊,蹲在门口,呼呼呼就能下去三大碗。
山东日照,农历二月底,用第一次收成的“满头黄”(就是虾黄)炖豆腐,是时令的美物。江西内陆,有一味名菜“墨鱼红焖仁生条子”,仁生条子就是豆腐干,用墨鱼炖到通透,内中灌满卤汁,是招待贵客的珍品。

寻常看来,豆腐的妙处,在于本身清淡无味,却可以和各种颜色,各种香味相配,能使番茄更红,木耳更黑,菠菜更绿。和火腿、鲥鱼、竹笋、蘑菇、牛尾、羊杂、鸡血等等没有不结缘的。
食欲不振的时候,做一味香椿拌豆腐,或是皮蛋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佐餐,清爽利落,口舌生津。时间允许,做一味麻辣烫三者兼备的麻婆豆腐,或煎得两面焦黄的家常豆腐,或毛豆烧豆腐,绿的碧绿,白的洁白,只颜色就令人醉倒了。假如就一碗蒸得松松软软的白米饭,只此一味,就令人百尝不厌了。
民国时有著名的文武两豆腐。
文豆腐是南京马祥兴的“二胡(胡翔冬、胡小石)豆腐”,豆腐辅以鸡肝、虾仁、笋尖等鲜嫩配料,清嫩味美、鲜香脱俗,前两年南大的学生排演《蒋公的面子》,算是把这道胡先生豆腐发扬光大了。
武豆腐是谭延闿家的“组庵豆腐”,一块几分钱的豆腐,却要用三斤以上肥鸡并火腿、猪肉、干贝、关东口蘑和猴头来吊,跟刘姥姥吃的茄鮝一样,名义上是吃豆腐,其实豆腐在这里,不过就是个末等的陪衬罢了。
相比起这一班老饕,虽然寒素,却更显温情的,是朱自清先生记忆中的白水豆腐: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口小洋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朱先生后来说过,豆腐跟白菜并称,惟其平淡,所以才可以常吃常久,才最为养人,最能教人做人。这一锅清清白白的豆腐,仿佛就是朱先生的人生底色。

“天下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
豆腐在中国社会中,是贫苦老实和勤劳的象征。章回小说与旧剧中,也常喜欢安排一对孤苦无依的老婆老头以磨豆腐为生,如《天雷报》里面的张元秀。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副产品,确是文学史上一个美好的副产品——“豆腐西施”形象的出现,比如《芙蓉镇》里的胡玉音:
胡玉音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子。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习惯于喊她“芙蓉姐子”。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芙蓉仙子”。说她是仙子,当然有点子过誉。但胡玉音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她待客热情,性情柔顺,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论穿着优劣,都是笑脸迎送:“再来一碗?添勺汤打口干?”“好走好走,下一圩会面!”加上她的食具干净,米豆腐量头足,作料香辣,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一角钱一碗,随意添汤,所以她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线。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本镇屠户,这一圩竞捎来两副猪杂,切成细丝,炒得香喷喷辣乎乎的,用来给每碗米豆腐盖码子。价钱不变。结果米豆腐摊子前边排起了队伍,有的人吃油了嘴巴,吃了两碗吃三碗。无形中把对面国营饮食店的顾客拉走了一大半。
胡玉音不过就是个湖南乡野当垆卖米豆腐的村妇,整整三十年前,经过刘晓庆的演绎,真有了颠倒众生的魅力。刘晓庆阿姨当年三十出头,丰姿妖娆,如今年逾花甲,却依然风采犹存,是不是吃了慈禧太后的珍珠豆腐,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