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阎连科
如果说文学场,多少也是个名利场,那么在这个场域里,翻译家是为别人的名利添柴加薪的人;甚或说,他(她)自己也是别人名利炎热的柴薪吧。如果说,好作品是和名利无关的物,那写出好作品的人,无论他的作品已经译出去,或是还如梵高、塞尚的静物画样寂在自己本土的语言里,想他在当世的文化里,不可能不是读了许多翻译作品的人。而这时,写出好作品还在寂处静坐的人,并不是文学场上最孤独、静默的哪一个,而是那些把寂作好文译进、译出的人,是那些给他写出寂静好文带来润物营养的翻译家。
翻译家在热闹的文学场,就像一项工程竣工庆贺时,被忘在角落参与重要设计和劳作的工程师;在寂好的文学作品里,他就是一个农人看见丰收而坐在田头抓起凝望着的那把土。
对当代文坛言,如果说每个中国作家都是一棵巨大的树,那么翻译家,则是那棵树裸露在外的最大的一条根,不仅要给那树提供充足的养,还要被人们踏来和踩去,蹲坐和踢打;如果说,每个中国作家都是一条通向文学未来的路,而翻译家,则是那个路上许多界牌和里程碑中被砸断埋去、再也没人想起去扶正的那块断倒并埋在路边的碑石了。
我们忘记翻译家,就像容易丢掉用过的一支笔;疏忽翻译家,像端起一碗好食时,而疏忽了在厨房做饭、炒菜的人,哪怕那个人是伟大的厨师或母亲。
就前天,28日的傍晚,Sylvie Gentil(林雅翎)到底离开了中国这个文学场。

▲
Sylvie Gentil
她是翻译家;是极好极好的翻译家。她对中国文学的爱,胜过许多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爱;对中国作家的爱,也胜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爱。法国人,却有近20年的时光都住在北京工体的周边上,就像一个中国人,半生都在国外默默地蛰居和生活,读书、写作和翻译。把阅读、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当成自己的吃饭和穿衣。
莫言、徐星、李洱、冯唐、杨继绳和我等,许多中国作家走进法国是通过她才打开了巴黎文学场上的那扇门。《红高粱》、《无主题变奏》、《花腔》、《万物生长》和《墓碑》,那些在中国或响亮、或沉寂的虚构或者非虚构,由她的心血浸润、翻译后,才在世界文学在法国那最为巨大、热情的卖场上,有了中国作家的响动和一丝丝的光。

人都说,法国读者是对中国文学最有热情的人。在世界各国、各语言的翻译作品里,大势是中国文学只有在法国才有一点回到家的样;有一点走向驿站而不被歧视当作主人接待的样。可在这个温暖的过程中,Sylvie Gentil是那种传递温暖最为执着、敬业而默默的一个了。无论她获得法国文学翻译奖、还是中国傅雷翻译奖、再或是法国文化贡献最高荣誉勋章等,她的这些荣耀和光芒,对我们就像一个母亲把一桌好菜摆在桌上后,自己躲在厨房吃那剩下的菜;而我们,关心的是桌上的饭菜是否好吃和好看,是否替自己在客人面前搬回了一成面子和虚荣。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作品被译到法国后,有多少读者和书评,有多大的响动和影响力,至于那些翻译家,如Sylvie Gentil这样的人,如把一个个中国作家带往法国交给翻译家的陈丰那样的人,都已经不在我们的视线了,都已经被我们放入可遗忘的名册里。只有作品译去在法国那个文学大国里,在巴黎那个世界文学的大卖场,无声无息时,我们才又想起他们来,想起把无声无息结出的怪罪之果和抱怨掷到他们的头上去;把一切与文学有关、无关的冷落都嫁到他们的头上和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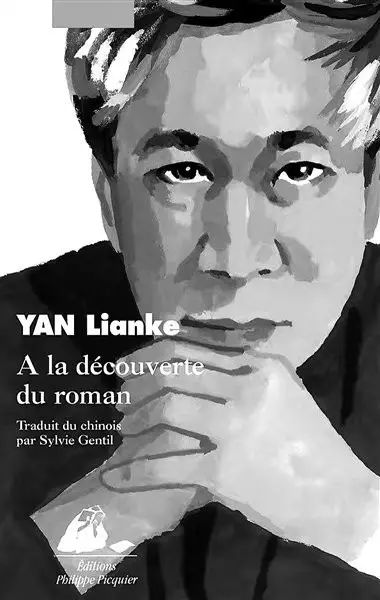
到现在——Sylvie Gentil女士离开我们了,在59岁时,她离开了中国这个文学场,这时的我和“我们”们,才想起徐星和他的几本小说,是她最早将其视为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探索之星译介并推向法国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等,是她最早译去让法国读者眼前一亮的;《墓碑》在法国的响动,是她帮助在那儿掷地有声的。还有别的作家和作品,数十本的当代中国文学,有响的和无息的,都浸泡着她翻译的心血和寂寞。

而今的这个我,无论在世界上是响或息 ,闹和寂,细究起来,都是从法国出发起脚的。都始于陈丰的推介和Sylvie Gentil、Brigitte Guilbau(中文名:金卉)二位才华出众的翻译家及Claude Payen(中文名:巴彦)老人的翻译。

在我由法国Picquier Poche出版社已出的十部作品里,有五本是经由Sylvie Gentil的翻译才在出版后有些响动的。《受活》《四书》《炸裂志》《耙耧天歌》和《发现小说》等,还有她刚着手翻译就不得不永远搁笔的《日熄》和《坚硬如水》等小说,一如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影响大,而我也压根不是媒体上说的在世界上怎样和怎样。

我知道我仅是中国作家之一的小说家,仅是被翻译后书掉在地上会弹起一些灰的人。就这弹起灰的一点点的事,如果没有法国这个世界文学的购物场,没有陈丰女士一本本的推介和Sylvie Gentil一本一本地译,Picquier Poche出版社一本又一本地出,那些弹起灰的事,是连一丁点的可能都没有。
法国是许多世界作家和一些中国作家有可能走向世界的一道门。而对我自己言,陈丰、Sylvie Gentil、Brigitte Guilbau和Picquier Poche 出版社,使我走向这道门的路或者修路的人,而今天,Sylvie Gentil的走,不光是我前边的路上坍塌的一个大坑和一座桥,也是许多中国作家和整个中国文学走向法国、去往世界的路上塌陷的难以填补的一个黑汪汪的洞。这对她的家,丈夫、女儿和亲友,那种苦痛和永远的殇伤,也会如黑洞一样让他们永远的望着、又永远的望不尽和念不断。对他们,对我们,虚无、殇泪、愁念、忧思和想起来都在心底生出的人世的冰寒和文学的冷,大约都因为4月28日18:05她的走去而成为永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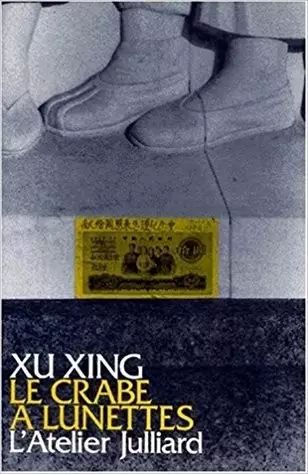
说起来,我和她认识是十几年前经由徐星介绍的。是2004年,陈丰把《受活》推介到法国后,有两个翻译家,都翻译了开头又觉得这部小说的语言不可译,也就都推辞搁下了。而那时,当我见了她,她却微微笑笑说:“如果确实没人译了我来译!”于是间,她把二年多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受活》的翻译上。其结果,《受活》在法国出版后,读者的意外和惊喜,让我和陈丰及出版社,都感到种了一棵枯桃树,却结了一树大苹果,连其它语言、国家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凡懂法语的,都用“完美”和“无可挑剔”来形容她对《受活》的译。从此后,我所有难译的小说,就觉得在翻译上无碍可行了,由她翻译就可以、也可能给别国他人的翻译提供借鉴了。
可现在,她却急急切切走掉了。
想起春节后,她在离开北京前,我们全家都到她的家里去,他们夫妇再到我家来,并约好四月她回到北京我们讨论《日熄》翻译的事;想起她生命的最后翻译出版的书是我的《耙耧天歌》和《发现小说》时;想起她要离开这个世界前,在翻译中止笔的小说还是我的作品时;想起4月17日,徐星告诉我她已肺癌晚期,他先一步到巴黎她的病床边上去,望我晚一步安顿、安顿赶过去,而今我和香港的翻译家Jessica Yeung(杨慧仪),七计划,八准备,终究还未及过去她就走掉了;望着她先生马丁在短信上告诉我的她已经“七天没有进食”、“九天没有进食”的话,虚无就像黑夜、黑洞一样围在我身边,情绪低落到觉得写作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活着也是一件无意义的事,而死亡和离去,又是那么可怕和不可逃避、又不能面对的事,人就空空呆呆,心如被黑沉沉的虚无挖走了样,只剩下一具躯壳窝在椅上和沙发上。

或者躯壳也已不在了,只还有看不见的魂灵在那一瞬间,像飞蛾一样茫然地飘飞又找不到可落下的枝丫和脚点,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想,她在生命的最后会对她的家人遗嘱一些什么呢?会对她酷爱到如吃饭、穿衣一样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遗嘱一些什么呢?就觉得,无论她在生命的最后说些什么话,遗嘱一些什么事,可能因为她一生所爱和翻译的是在世界上还处于边缘、落寞的中国文学,而法国巴黎并不会因为她的离去而感到惊讶和伤逝;而中国和文坛,会因为她是一个法国人,而觉得与己无关,并不把她的离去当作一个伟人、名人的离世样,但我却从昨天到现在,总觉得她面对这活着都已想到、且并不在意的尴尬和冷落,一定、一定在离世前的遗嘱中,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说下这样一句话——用无言遗嘱的方式对我们大家轻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