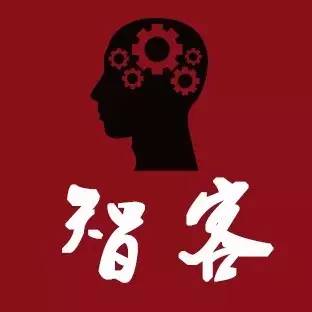《代议然否论》的另一个论述重点,就是分析当时中国是否有选举议员的条件,以及预测若径直举行选举,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在极力表彰代议制的密尔那里,“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响”。但章太炎指出: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如果举行选举,假设国会有700个议员的名额,那么置诸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将会是六十万人中选一人,在这样的比例之下,“数愈疏阔,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原因很简单,假设让“贤良”与“土豪”竞争,前者必不及后者富于资财,“土豪”可借财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让民众将选票投给自己。如此一来,“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膢腊齐民甚无谓也”。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将对民众造成更大的剥削,并在具备公开选举过程这一表面上程序正义的幌子之下,进一步剥夺了民众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条件,这也和中国政治传统中对豪强兼并的谴责,对均富平等的向往严重背道而驰。
此外,章太炎认为,如果用是否识字作为选举标准,当时中国的识字率并不高,那么大多数不通书面表达方式的民众将无缘选举,成为“无声的大众”。因此,章氏推测:“满洲政府歆羡金钱,其计必以纳税为权度。”这一判断,其实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若合符契。近代民主的出现,始于君主向贵族与新兴的资产者寻求金钱,于是后者向前者提出一系列条件,保障自己的权利。在这些讨价还价里,个人和集体对国家的要求,个人和集体对国家的权利,以及国家对其公民的义务皆一一确立。只是在近代中国,欲行此政,必须对中国地域广袤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此章太炎指出,中国“地有肥硗,获有多寡,不容以法令一切等画之耳”。具体言之,江浙一代农商发达,此外愈往西部,则经济水平愈落后,因此富裕之地纳税繁多,其他地区则依经济水平之贫瘠而递减。如果统一制定达到选举标准的纳税数目,那么将导致“选权凑集于江浙,而西北诸省或空国而无选权也”。如果抬高纳税数目的话,更会造成全国范围内只有有限的人数可以参加选举,那么民权云云,形同口号,甚至出现“代议本以伸民权也,而民权顾因之日蹙”之景象。章氏分析,当时娼妓伶优财产较为立宪政治鼓吹奔走的士人多,若制定高额的纳税标准,那么很可能后者无缘议会,前者却可在政治上粉墨登场。如此一来,政治将沦为借酒食嬉戏引人瞩目的闹剧。凡此种种,显示出代议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社会。他质问主张代议制者:“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耶?”
章太炎之所以反复提及中国国情的复杂,与他对知识的理解息息相关。他自言:
吾尝以为洞通欧语,不如求禹域之殊言;经行大地,不如省九州之风土;搜求外史,不如考迁、固之遗文。求之学术,所涉既广,必摦落无所就,孰若迫在区中,为能得其纤悉。
可见,在章太炎看来,作为中国人,首要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是最为重要的知识基础,也是一切政治行为的主要根据,后来他在教育领域也大力提倡“本国人有本国的常识”。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章太炎不像许多革命党人那样对未来信心满满,而是强调应“先综核后统一”:“诚欲统一者,不在悬拟一法,而在周知民俗,辅其自然”,否则“不先检方域之殊,习贯之异,而豫拟一法以为型模,浮文犷令,于以传电有余,强而遵之,则龌龊不适;不幸不遵,则号令不行”。设立制度与执行政策,都要建立在对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各地差异极大这一现实国情有充分体认的基础上,即“欲更新者,必察其故;欲统一者,必知其殊”。如果是靠一二“游学他国,讲肄科条,而于家邦庶政,什不能晓其二三”之人来主持政局,因袭一二外人之政来施于禹域,那么就是武断为政,是“新顽固党”。民初政局后来一系列闹剧式的行为,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章太炎此处的警告。这篇文章虽然写于民国初建,但他的思想见解,却是和《代议然否论》里提及的相关思想一脉相承,从中亦可理解章太炎为何反对在中国实行代议制度。
在西方启蒙运动时代,时人对于政治的理解,不是根据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而是视解决政治问题如同探索自然科学,后者的原理可以直接施之于前者,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差异可以泯除,整个人类生活将呈现一种普遍性,人类问题将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这一观点在19世纪欧洲受到历史主义的严重质疑。不过在晚清时期,许多主动接受新知的士人却依然深受影响。梁启超回忆自己在戊戌变法前后与夏曾佑等人聚谈西学的情形,他们觉得“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章太炎晚年在《自订年谱》中亦言:
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余每立异,谓技与政非一术,卓如辈本未涉此,而好援其术语以附政论,余以为科举新样耳。
在这样的知识风气下,加上救亡图存的强烈危机感,提倡改革的士人,很难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复杂性,更忽视了西洋新说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发展。即便认识到一二,也多强调用更大改革的决心与力度便可将其克服。极力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就宣称:
今吾国为世界大势潮流所迫,一切政俗不容不变,所有旧习惯,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不急起而改造之,以图一劳永逸之偷乐焉,而乃苟且偷闲,暂图目前之安睡不扰,以此为有秩序,殊不知真秩序不可得,旧习惯又势难保全,长此扰扰,不动不静,反真可谓不秩序矣。故吾一言以决之,苟非有文明国家责任政府之后,所谓秩序,必非真秩序也。
可见,在杨度眼里,当时的中国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章太炎亦然,详下文)。他心目中的“世界潮流”、“文明国家”,具体的现实形象就是当时国力强盛的欧美与日本。在此思虑之下,中国具体的国情、中国地域之间的差异,甚至中国社会自身运转的逻辑,不是被忽略不计,就是被看成有碍政治改革的“旧习惯”。
近代西方代议制度出现之初,主要的意义在于分摊赋税以及为地区争取利益,随着时间的推演,关于这一制度的争议也随之出现,如议员应完全关照地方利益,还是从国家整体出发决定政策,这在代议制发展史上长期争论不休。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议制下的议员,往往代表着某一资本势力的利益,许多看似充满神圣性的口号与政纲,不过是特殊利益集团意志的表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这一现象有极为辟透的分析。施密特则指出:代议制丧失其内在本质,政党沦为“社会的或者经济的权力集团相互对立着,思考着双方的利益和权力潜能,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和联合。一个最大效果在于呼吁人们关注眼前利益和激起热情的宣传机器争取着大众”。不过,由于前文所分析的时代政治心态,晚清趋新之士多视代议制度为振衰起微的良方,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后者在运作过程中对利益、权力、舆论、资本等因素的吸纳与操纵。在彼辈眼里:
代议政体兴,鉴于专制政体之害,务反其道而行之,必欲使其国民者,有直接间接参与政事之权,而惟恐一国之政治,为自私自利者之所把持,故特设一机关以广求舆论,则所谓议院者是也。既有议院,则国民之有政法思想者,如勇夫临战场,自喜有用武之余地。则安得不各整旗鼓,以思竞其技也。
作者似未想到,代议制同样会给“自私自利”之徒假公济私的机会,而能够在议会里“有用武之余地”者,更绝非具备“政法思想”即可,而是很可能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占据。
反观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里,他着重分析在不同的选举标准之下,不同阶层被选举为议员的几率。在他看来,靠上级政令强行整齐划一的选举,“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劳”,选出来的人很可能是豪强富户,他更观察到:“夫贼民者,非专官吏,乡土秀髦,权力绝尤,则害于民滋甚。”彼辈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这将会更不利于庇护细民。在这里,他已经认识到选举背后阶级、权力与利益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代议制度徒有其名,特别是对广土众民、经济发展形态差异极大的中国而言,以上因素将会体现得更加明显,这无疑是对现代政治极为深刻的洞察。犹有进者,章太炎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被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自功利说行,人思立宪”,时人提倡代议制之风盛行,与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中国资本市场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即“皙人又往往东走,矿冶阡陌之利,日被钞略,邦交之法,空言无施,政府且为其胥附,民遂束手无奈之何”,进而促使“富者愈与皙人相结”,在国内外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将导致“齐民乃愈以失所”,而在这一过程里,代议制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