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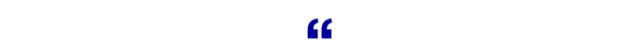
人不能因为害怕受伤,就用强大的姿态武装自己,把爱、软弱和不幸从生命中阉割掉。


爱德华•诺顿:
你好呀,最近北京雨多得不像是在北方。有天晚上我睡觉时被雷声惊醒,一道道白光闪在黑暗里,认真听了听,还有蛙声和蝉鸣,这里越来越不像北京了,恍惚回到了南方。在黑暗中,我听着这些声音,竟然觉得很安宁。
在很久之前,我睡觉是不敢关灯的,我恐惧黑暗中不知名的东西会慢慢地走到我的床边。可现在很奇怪,我竟然不怕了。黑暗中,我熟悉每个过道和门墙,准确地走向洗手间。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恐惧会消失呢?现在我知道,一个人只有正面恐惧,就会变得勇敢。
诺顿先生,这是个悖论。如果你极端恐惧某件事的发生,唯一能解决这种恐惧的办法,就是让这件事真的发生。然后你会发现,咦,恐惧和焦虑只是源自认知偏差,事实也不过如此——黑暗中什么都没有,于是我折回床上,蒙头大睡。
人长大,就是不断修正认知偏差的过程,然后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可是诺顿先生,我最近有点沮丧,因为接近真实必须跨越立场、偏见和自我,最重要的是跨越无聊。我很喜欢的导演希区柯克,他很了不起,是个跨越了无聊的人。他说过一句非常值得玩味的话,“戏剧就是人生,只不过砍掉了无聊的部分”。在他的作品里,只有强烈的冲突和意外的情节,没有什么情节与日常相似,每个结尾都出人意料。人们称他为恐怖大师,我却觉得他看到了生活的真实。
我曾经迷惑过,但是如果反向思考,把生活里每个重复的日子去掉,只剩下人生的枝干,你会发现,剩下的东西不多,爱、恨、生、死。如果必须再加点什么,那就是正义与不义。人们喜欢戏剧,因为我们都过着重复的日子。如果足够幸运,可以重复到死掉的那天。这多好呀。
人是很聪明的动物。诺顿先生,人人都希望自己幸福而美满,宁愿无聊,也不要不幸。正因为如此,人们喜欢在荧幕上看悲剧。或许再加点滑稽。诺顿先生,你愿意在电影院坐上三个小时,看着完美有爱的一家人吃饭聊天游玩打理庭院,展示幸福的日常吗?我相信没人愿意,人们渴望在戏剧里看到的悲剧,正是在生活里极力避免的。
我有天看到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求而不得,一种是得偿所愿,后者往往比前者更糟糕,那才是真正的悲剧。我认真想了想,这句话不对。诺顿先生,说这句话的人肯定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不愿意承认无聊其实是快乐的一部分,最重要的那部分。
为此我总是疑惑,为什么那些热爱艺术的家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颓废很痛苦,似乎有这样,才会具有艺术的深度,可是王小波早就说过了,只有别人的痛苦才是艺术的源泉。这话说得够机灵,拿自己的人生做艺术实验,是不智的,做个聪明而快活的人,比做艺术家更重要。
于是我理解了在戏剧里,必须发生点什么不幸,最普通的日子最惊险,最熟悉的人最出乎意料。可是在人生里,天啦,最好还是什么都别发生了。诺顿先生,因为真正的不幸从来都不是冲突,而是无声的崩溃,缓缓地坍塌在了心里。
诺顿先生,上次我说我推倒了心里一堵堵的墙。现在我做的是重新构建自己内心世界,我直面了恐惧,但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强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不在乎强大这件事了。如果推倒墙后,只是重新建立了一堵更坚固的墙,那推倒本身就没有意义。那个比别人强大的自我必须死去,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自我不如一捧尘土。
尤瑟纳尔说过一句话,这世界上最肮脏的,就是人的自尊心。这话和时下最流行的“做人最要紧是姿态好看”恰好相反。姿态好看是什么呢?这话说得狭隘,它指的是没什么比别人眼中“你的强大姿态”更重要,没什么比你的自尊心更重要。
可是诺顿先生,可是诺顿先生,人有血有肉,会哭泣,会难过,会害怕,所以才会勇敢,姿态算什么呢?这世界上比自尊心重要的东西太多了。如果在推倒一堵堵的墙后,还能对世界充满好奇,对苦难充满同情,对爱充满期待,这样的重建才有意义。人不能因为害怕受伤,就用强大的姿态武装自己,把爱、软弱和不幸从生命中阉割掉。如果人在不幸之中,还能看见别人,那就还有希望,还能体会别人的痛苦,那就还有温暖,人是不会停止爱的。于是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戏剧中,诺顿先生,都必须发生点什么,你说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