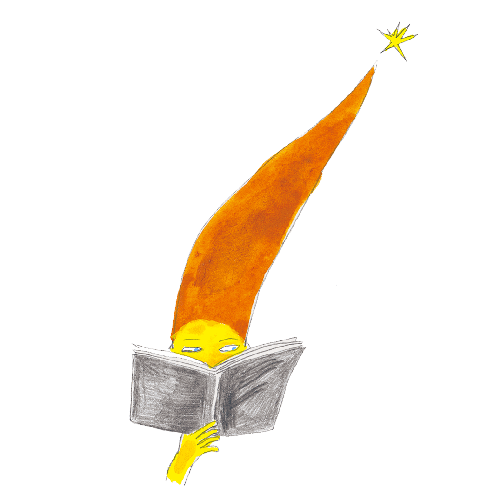
孩子们(比如6至12岁),他们除了呼呼睡觉,醒来时大声喊妈,然后吃呀、喝呀、跑呀、闹呀、哭呀、笑呀(一句话,就是“玩儿”)……他们还会干什么?
有人说:“他们会画画”。这倒是真的。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是事实,是我们每个大人都能观察到的。记得毕加索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能用很短的时间,就画得像一位大师;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这句话意味深长,说明“孩子画画”是了不起的一种天份。
我特别想说的是:“他们还会写诗”。孩子们会画画,也会写诗。
画画的能力和写诗的能力,是并存在孩子们的天性中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差别:对前者,大家都公认;对后者,明白的人还廖廖。
画家、诗人,我的好朋友熊亮,是真正明白孩子们“既会画又会诗”的人!他教他们画画,也教他们写诗。他凭什么发现孩子们“既会画又会诗”呢?凭他的一颗童心。童心让他变成了一个对世界万物充满好奇的人。当他想画出“好奇”的时候,他成了画家;而当他想说出“好奇”的时候,他成了诗人。
仿佛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孩子们会写诗”这个道理,熊亮特意编选了这本《孩子们的诗》,由“雅众文化”出版。
熊亮给我寄来了一册,写在扉页上的话令我感动:“树才老师:孩子们给我们的礼物”。
确实,
孩子们写的诗,是给所有大人的最好的“礼物”。这份礼物,是孩子们用心里话做成的,里面跳动着一颗颗活泼泼的童心。
这册《孩子们的诗》,从里到外都美。熊亮选了十几位孩子(6至12岁)的近百首诗。插画师刘霓贡献了插图(那些甩向四面八方的筒状长发辫,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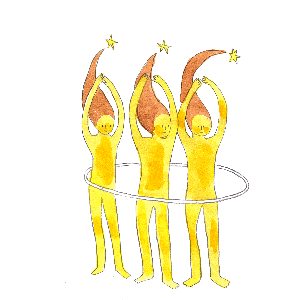
从只选了1首的杨子萱(6岁)到入选18首的李子轩(8岁),这些孩子的诗给了我莫大的阅读的愉悦。
通过这些诗,我读到了他们最细微的心思和最奇妙的言语:古往今来,不论中外,诗就是心灵和语言的相遇。我发现,孩子们的心是多么“灵”啊!我慨叹,“创造力”是所有这些孩子的特征,是他们的正常的语言行为,这种创造力特别适合于他们学习伟大的母语--汉语。通过习诗来学汉语,这是熊亮给孩子们创造的一个好机会。
我们来欣赏孩子们的诗吧。
杨子萱只有6岁,有一首诗《楼上的龙》入选,这是一首好诗:
这是小子萱做的一个恶梦吧!一边读,我不禁这么猜想。8行诗句,记述了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一件事情,有点恐怖!首先写恐怖的“声音”,
那是孩子的听觉,但抓得特别准
,地点是“楼上”,声音是“吐啊吐啊”吐出来的,让人想到嘴巴呕吐的痛苦,但这张嘴不是人嘴,而是“恶龙”的嘴,孩子想象是“恶龙吞了蓝蘑菇”(我现在就在大理,正是吃菌子的季节,有一种叫“见手青”的蘑菇,如果生吃,据说眼前会飞出好多“小人”呢),那就更恐怖了!但剧情马上发生了逆转,因为“每个人”都“茫然地对着我”,好像在问:“发生了什么吗?”孩子接下来写出了“每个人”的心里话:“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这是很戏剧化、也很生动的。面对这么一件恐怖的怪事,孩子自有一番认知:“我想/那可能就是属于我的那条龙病了”。
一首诗里包含着认知力。
孩子只有6岁,但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有认知的。6岁的孩子,对“惊恐地”“茫然地”这些词,可能只会说,还不会写。这首诗应该是孩子先“说”出,然后妈妈爸爸帮孩子“记”下来的。整首诗完全是孩子的口吻和语调。
6岁左右的孩子,对身边事物的观看是很敏锐的,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更是敏感,而每一天有多少事情在孩子们身上发生同时又被他们直接感觉到啊!这些事物,这些事情,如果孩子们能“说出”他们的“观看”和“感觉”,爸爸妈妈们只需把听到的“话语”记下来,它们就是现成的“诗句”啊。
池塘冻上了。
我趴着,眼睛贴在冰上往里看,
冰下黄黄的,好像加了一个黄滤镜,
还挤满了黄色红色的落叶,安静得像睡着了。
冰下有大大小小的泡泡,
大泡泡还有孔,莲蓬一样,
小泡泡就像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多的看不清。
冰下有鱼,有活的有死的,
活的很少动,不动时还以为是死的,
死的侧着身子,
一动不动。
诗,对大人们来说,也许是神秘之物,因为大人们误以为“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他们只是生活在“概念知识”的囚笼里
),但
对孩子们来说,真的是切近之物,他们抬眼所见、随口一说、即兴想象,只要有“话语”从嘴里说出来,诗句当即诞生,
因为他们生活在想象世界中,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一切都有形象、有色彩、有气味,灵心一动,就“看见”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们生活在类比的“隐喻语言”中。妈妈爸爸们要做的,就是同孩子对话,激发他们说出自己的感觉。这些感觉千奇百怪,但孩子有天生的语言能力,能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出这些感觉。
同样是6岁的王知微,有7首诗入选,也是很灵的一个小诗人,《脑海》一诗的最后一节,“说”得实在是妙:“一个记忆/想起来的时候是岛/想不起来的时候/是茫茫的海水”。7岁的小艾艾,那首《树》也入我心,我读了之后,就永远记住那棵树了,因为它居然有“一万零七百六十七”个小树精!小艾艾是随口一说吗?但这个数字又是多么具体、准确!接下来,诗向着哲学的方向发展:
它活着又死了/抛下了它的种子/种子又重生/再次变成自己/世界在变/我们在变/而它永远是“它”
一棵树,看似很平常
可你有没有想过
它的奇妙
你知道吗?
那里面有许多小树精
告诉你它的岁数
听,他们在嚷嚷
说的那个数字是:
一万零七百六十七!!!
它活着又死了
抛下了它的种子
种子又重生
再次变成自己
世界在变
我们在变而
它永远是“它”
早上是月亮休息的时间
晚上是太阳休息的时间
乌黑乌黑的房间
地上落着一束光
再见
每天 我睡觉的时候
我不在这个世界
在宇宙的另一边
孩子“说”出的,可是生生不灭的真理啊!一个人穷其一生,不就是为了明白这一真理吗?!你说是谁教会了他们?只能是孩子自己,是
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种来自本能的内在感知力。
这十几位“孩子诗人”中,最能写的,要数8岁的李子轩了,共有18首诗入选。完全是一个小大人!不光写了《怪人》、《梦》(“说不定/我们只是上帝的一个梦”)、《无题》(“烟是画笔/风是橡皮擦”)、《颠倒国》(“这里的薯条比石头还硬。纸巾比大地还厚”)、《讨厌的星期六》(因为“讨厌跆拳道”,最后连说三句“讨厌的星期六”),还写了《我心中的死亡》(纪念那只小乌龟),甚至写了《气》(“气无所不在/也不在任何地方/从台风的呜呜呜到沙子的沙沙沙”)……可见,8岁的孩子还是比6岁的孩子更能写!李子轩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了!生活中的一切发生,都被化为题材,从写景写物到写人写感觉,都有源源不断的“话语”涌出。还有,9岁的马达写了《我的心》,9岁的韩牛写了《太阳在屋里》,都写得很“牛”。
太阳在屋里
可那是一束光
点亮了昏暗的房间
我把它抓住
它变得格外清晰
如火球般地跳跃
直到
松开我的手
这个世界,屋子里漏出来的光是黑色的,路灯发出的光芒也是黑色的。事物投在地上的影子却是雪白的。
蜗牛的速度比光速还快。光却永远都到达不了它 要照射的地方。太阳就像一颗黑色的小芝麻。星 空就像是白色的布上洒了一瓶墨。这里夜如白 昼。白天却墨汁一样黑。葱郁的树木显得苍老。清澈的小溪像铁一样不透明,也不再流淌。
老人像新生儿一般。新生儿又显得那么憔悴。年 轻气壮的小伙子,虚弱无力。满头白发的老人却 精神饱满。
这里的薯条比石头还硬。纸巾比大地还厚。大象 似乎轻而易举就能踩扁,蚂蚁只要打个滚,你就 被压成肉酱。皇帝干的都是奴隶们的活,奴隶们吃的却是皇宫里的佳肴。
光明即时黑暗,黑暗即时光明。
开始时是结束,结束即时开始。
蹊跷蹊跷真是蹊跷,
不过那里的人觉得我们才蹊跷。
我的每个红细胞都在运送讨厌路拳道的想法 所以每个细胞都讨厌跆拳道
我的脑子里的深谷回荡着讨厌路拳道的声音 这种声音可以让一百个人变成聋子
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做“儿童诗歌教育”这桩大事。我要特别对熊亮表达感谢,因为我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始这项工作的。熊亮善画,能诗,心地善良,特别懂孩子,所以他的慧眼才能选出这些好诗。写这些好诗的孩子们,其实都是他的徒弟。按照中国的伟大传统,师傅是要把自己的“心得”和“技艺”直接传递给徒弟的。熊亮正是这么做的。孩子们的这些好诗,完全可以刷新我们对“童诗”的认知
——
真的,孩子们的语言竟然可以这么有个性,孩子们的想象竟然完全源自他们的生活,孩子们的认知竟然可以这么有智慧!
祝福这些“诗人孩子”!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成为诗。写诗,不仅是孩子们的一种天生能力,更是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天然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