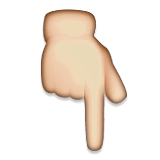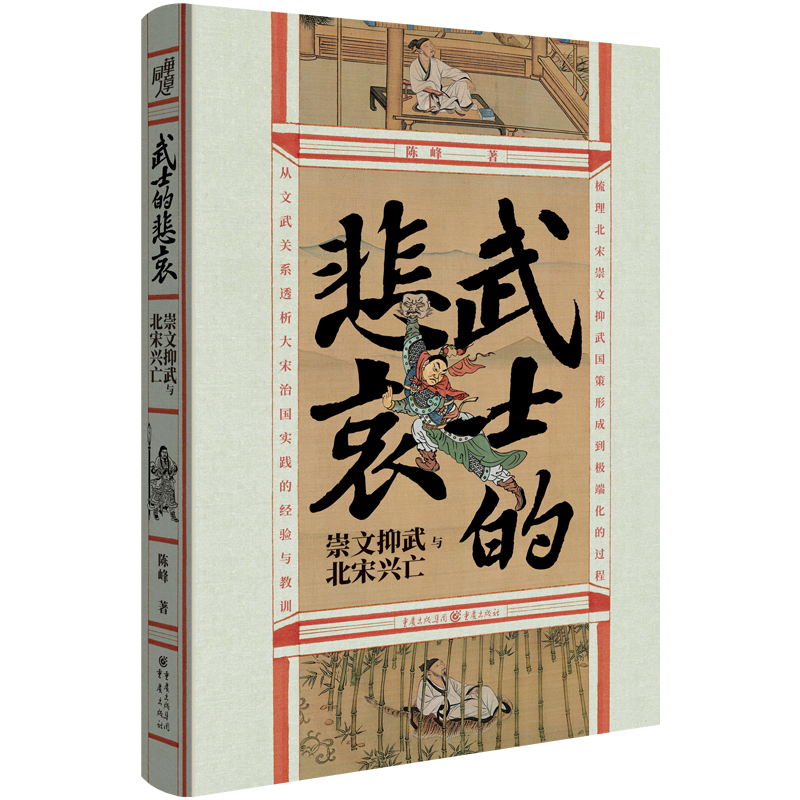最近看陈峰教授《武士的悲哀》一书,越来越看不懂北宋政府的行为逻辑。按道理说,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幽云十六州还在契丹人手里,宋朝应该继续为收复失地整军备战才是。
可宋朝立国没几年,就不可思议地
全面“弃武
从文”了!
汉朝立国时面对着匈奴的威胁,唐朝建国时突厥军队直接打到长安附近,要论政权初创时的险恶,宋朝并不算最差。
汉唐可没在强敌虎视眈眈时,主动搞什么“弃武从文”。
宋朝政府这方面还真做得不错。
五代十国飞扬跋扈的武将们,不过十数年的时间就纷纷灰头土脸,赵匡胤似乎喝了一场酒,就缴了武将们的兵权,唐末以来形成的“重武轻文”局面一扫而空。数十年后,汴京之围,无将可用,无兵可守,大宋的皇帝成了俘虏……
这种细思极恐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真宗登基之初,为了向天下表示朝廷的权威,曾通过下达诏令的形式对武备给予了一定的重视。随后,他又亲自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亲赴河北大名城坐镇指挥御辽战役,他还在做天子的第三个年头,下诏开设武举。
这一切似乎都给朝野传达了年轻天子有重整军备的志向,这给关注国家军政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一线希望,尤其是武举更对有意通过投军来实现个人抱负的人,不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
通过武科考试的办法为军队选拔武官的制度,最早出现于唐朝武则天时,以后该项制度逐渐湮没不闻,军官依旧从官员子弟,特别是将门之后以及军兵中录用。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文人“弃笔从戎”,加入了武臣的行列。
太祖、太宗年间,由于经历过战场洗礼的武将甚多,加之朝廷开始提倡崇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扩大武人升迁的途径。至第三代天子统御天下之日,面对边患日益加剧的局面,才感到军队人才奇缺,昏老庸懦者充斥营伍,于是想到了恢复武举的办法。
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中旬,真宗令有关机构讨论举办武举的事宜。次年二月一日,又由御史台向全国各地转运司下达公文,要求各路在五天之内将员外郎级别以下文臣中“有武勇才器堪任武职”者举荐上来,然后由朝廷安排这些人到边防前线做地方官。不久,再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及馆阁儒臣等熟悉典制的文官考定武举、武选人做官的资序旧制。
在咸平三年(1000年)四月间,河北路便推荐了三十名有武干之才的举人,真宗在宫中对他们的武艺进行了测试,将其中合格的十八人授以三班借职的低级军职。
然而,以上措施作用毕竟非常有限,有关的讨论及命令虽然风行一时,却很快没有了下文。因为
很多文臣对此提出了异议
,认为这些举措既不符合实际,又在时间上过于仓促,有失周密考虑。如吏部郎中、知泰州田锡就指出:昔日从朝臣中选出过多名有武勇之名的人,结果并无实效,而如今文官中尚武者既少,纵然有这样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愿转为武职,反不如从现有各级武臣中选用为便。至于录取标准,应以谋略为上,武功次之云云。
正像喜好议论时政的田锡所说的那样,文臣有文化知识,却不愿转入武官之列;武将们虽不乏勇气,然则不通文墨,缺乏用兵谋略,这种现象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军队各级指挥员素质的提高。但假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将优秀人才吸引到军旅中去,势必就要在朝野上下树立崇尚军功的观念,也势必要抬高将领在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说起来,这样的做法在昔日并不少见。
当时,大小军阀为了壮大个人势力,都拼命招兵买马,无不以能征善战者为时代英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方诸侯为了防止士卒逃亡,又开始推行刺字制度,即在士兵面部鬓角位置或者手臂上刺下所属队伍番号名称,如后梁太祖朱温对部下“皆文其面以记军号”。这样一来,士兵一旦逃亡,便很容易被识别、抓获。
刺字在五代时作为约束军兵的一种办法,可以说已含有某些歧视的成分。
然则在武风烈烈的岁月里,骁勇的武士常常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刺字倒未受到世人的过多议论,从军也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险途。如当时就有像前述焦继勋、辛仲甫等那样的弃文从武的文人学子,在军营中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然而,到宋朝建国后,经太祖后期,特别
是太宗一朝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宋朝的尚武风气迅速收敛
,不仅往昔“出将入相”的现象不再出现,而且将帅们还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从而受到文臣的压制。像深谙世情的大将曹彬,在街上与文官士大夫们相遇时,就主动为对方让路。
至于士兵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几乎可以与罪犯相提并论。按照当时司法制度规定,大部分重罪囚犯在发配到外地服刑前,必须在面颊上刺字,以防逃亡。
而这种刺字的形式竟与军人相同,正如后世小说《水浒传》中描写的林冲、杨志等人刺配的情景。与此同时,朝廷有时也将某些犯人刺为下等军人,如厢军中的牢城营士卒之类,所谓“牢城指挥,以待有罪配隶之人”。
如此一来,军兵在世人眼中便成了“行伍贱隶”
。宋朝人就曾这样说道:朝廷沿袭五代刺字旧习,使之成为常法,士卒竟无法与齐民相等。于是,在太祖后期,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开宝九年(976年)初,各地奉命向朝廷推荐了四百七十八名举人,其名目为“孝弟力田”及“文武才干”等,其中仅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北)一地就推荐了二百七十名之多。太祖对此感到奇怪,就将这些举人召入宫中询问,结果发现他们都大不如意。举人们眼见天子流露出失望的表情,又不愿放弃入仕的机会,遂纷纷声称自己可以操练兵器。太祖听罢,便下令让他们演练骑射。
然而,情况却依旧令人失望,表演者不是坠落马蹄之下,就是将箭镞不知射到何处。看到眼前可笑的场面,太祖生气地对众人说:你们只能到军营当兵。举人们一听,都不觉号哭起来,一再请求天子开恩,免去自己兵籍之苦。太祖最后下令将他们遣散,对地方官追究了滥举之罪。
太宗朝以后,武人地位日渐下降,更受到文臣的明显轻视
。
真宗登基初,就有朝士向天子上言:当今主将仅有一夫之勇,在边防上少有功勋。
正是在开国以来天子及朝臣们的精心筹划与治理之下,
大宋的军官日渐变得谨小慎微及恭顺谦和起来
,其头面人物如傅潜、王超及次一级的王荣之流,已成为当时武将的集中代表。
这样一大批将领虽早已被证明有庸懦无能的痼疾,但因为易于驾驭,没有非分的志向,所以仍继续身居高位。直到他们损兵失地、国人皆曰可杀之时,才被暂时解除职务,却终究不至于有性命之虞,日后则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还有一些开国功臣的子弟,如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王审琦之子王承衍等,依凭父辈功勋而轻取显赫官爵,手握节钺,却同样贪图享乐,怯于作战。咸平二年(999年)天子亲征期间,石保吉任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和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州市)方面统军大帅,受命迎敌。但他却有意缓师而行,致使延误了战机。
这些贵胄子弟纵然在战场上有失职行为,也同样不会受到什么惩处。相比之下,
那些不识时务、舍身沙场的将官,或难以升迁,或受到排挤
,遂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武臣的悲哀,并且是真正的武士的不幸。
太宗朝抗辽名将杨业不幸战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遗业,继续投身保卫北疆的战场。在杨业的诸子中又以杨延昭最为著名,他同样以卓越的战绩而成为真宗朝名将。杨延昭本名延朗,自幼受家庭习武之风影响。稍长之后,他便随父亲出征代北各地,以勇武冠于三军。父亲遇难后,他被朝廷提拔为崇仪副使,开始在河北前线与内地担任军职。
咸平二年(999年)秋,在抗击契丹大军南犯期间,由于河北主帅傅潜等人拥兵自守,致使辽军长驱深入,众多边镇失守。就在当时前线一片残破的局面下,唯有杨延昭与少数几个将领敢于顽强抗击,给辽军以重创。
咸平四年(1001年)冬,杨延昭又与杨嗣、李继宣等勇将在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北)大败南犯的辽军,再以战功升任团练使衔。一时,杨延昭与另一将领杨嗣名扬北疆,被世人称为“二杨”。
朝廷毕竟还是需要戍边将领
,所以真宗对宰臣们说:二杨都出外守边,以忠勇效命朝廷,朝中嫉妒二人者甚多,朕尽力保护,才能使他们获得如此功绩。天子一席谈,正反映了当时庸懦武官遭人蔑视,而功勋卓著的将领又受朝官嫉妒的事实。
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军职,官衔则迁至防御使。从此,他驻守于城镇之中,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地方,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对于处理案牍吏事,杨延昭既无兴趣,也不精于此道,日久天长,遂为手下奸吏蒙骗,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他因此受到过真宗的训诫。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杨延昭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七岁。这样一位名将,在仕途上至死不过是防御使官衔,离授以节钺尚差两道鸿沟,默默无闻地病故于平静的家中。这对于那些慷慨骁勇的武士来说,实在是壮志难酬,如同一场悲剧。
景德三年(1006年)年底,大将高琼身染重病。据史书记载,真宗为了表示对忠心耿耿担任多年禁军大帅的安慰,曾打算亲临其家探视,然而却遭到了宰相的劝阻。史籍没有提到这位宰相的姓名,但通过其他文献的记录,不难知道当时的宰臣只有一名,即王旦。
王旦为什么要阻止天子幸临高府
,其原因不得而知,最有可能也最接近史实的解释便是:高琼乃一介武夫,皇上大可不必屈尊探望。也许是真宗被宰相的话语说动了,便中止了这次行动。于是,高琼在期待中死去,时年七十二岁。
值得一提的是,咸平时,故相吕端病死前,真宗曾亲临吕府慰问。景德初期,宰相李沆和毕士安亡故前后,真宗也亲自去两家探视,朝臣们并无人劝阻皇帝,反而视此举为天子贤明慈爱的一种表现。以后,王旦自己病重之际,真宗又亲至其家抚慰,并一次赏赐给五千两白银。
但对武人而言,在文官们看来,皇帝这样做便过分了
。
本文选自《武士的悲哀》一书,选编文章有所删节,详情看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