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上映前后,演员咏梅忙碌起来,接连几天都排满了工作,只能在间隙接受采访。但这种状态在她这里或许并不常见,曾经有位合作伙伴说:“她就算不停止工作的时候,也不怎么工作。”
在咏梅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角色不多,但有不少却让人难忘。她不是很在乎自己是不是女一号,但很看重剧本和故事。某种程度上,《出走的决心》和咏梅此前的作品很不一样,这是一部“大女主”的电影,以视频博主“50岁阿姨自驾游”苏敏为原型,讲述了女主人公李红在50岁的年纪,如何离开禁锢自己的家庭,勇敢上路的故事。
“我在等待一个有力量的角色。”咏梅说。因此,当她看到媒体对苏敏的报道之后,很自然地就被打动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和导演、编剧几乎是同时看到苏敏的故事,都觉得可以拍成一部作品,它绝对是为女性发声的。”
2019年,咏梅凭借电影《地久天长》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华人柏林影后,大众知名度越来越高,她却没有因此加快接戏的频率。那一年,咏梅和出版品牌“理想国”一起发起了与阅读有关的“咏读计划”,以声音的形式和读者见面,定期和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
也是差不多从这个时候,咏梅开始系统地阅读女性主义方面的著作,她发现自己有很多粉丝是年轻的女孩,她希望可以从理论层面给予她们真正的支持。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咏梅自己在接其他工作的时候,也会更加考量它是否可以表达女性的处境。
咏梅少年时代生活在呼和浩特,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了懵懂的女性意识。“想要出走”成为她心中的小火苗。1992年,咏梅大学毕业,想要南下去深圳工作,这在当时多少是个有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却得到了母亲的支持,让她证明给自己看看。
咏梅的父母很早离婚,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家庭。年少的咏梅也不理解母亲,直到有一天她看到母亲头上的白发,才意识到母亲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和渴望。
《出走的决心》上映后,咏梅和苏敏做了一期节目,咏梅问苏敏,如果将“自己、女儿、母亲和妻子”几个角色做一个排名,她会怎么选。苏敏说:“以前我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但是现在我想把自己排在第一位。”
当苏敏问咏梅如何排序的时候,她说:“我其实特别不喜欢排序,我可以去调和不同的角色的关系,但是我还是会捍卫自我。”
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女演员奖之后,咏梅的工作邀约多了起来,其中少不了拍摄杂志封面,她总是会和摄影组强调:“不要把我的皱纹P(S)掉。”咏梅说:“我现在也在‘出走’,比如对抗所谓的‘容貌焦虑’,和束缚自己的东西抗争是一辈子的事情。”
《出走的决心》前期团队几乎全部是女性,咏梅在其中工作感受到了一种女性彼此的理解,和充分的沟通。这部电影由于男主角李红的丈夫是一个过于反面的角色,一开始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来出演,直到姜武接下这份工作,电影才顺利进行。咏梅觉得,在当下讨论男女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搞对立,她希望可以有一个有效的平台,大家可以进行充分的对话和讨论。
2024年9月25日,咏梅凭借《出走的决心》获得金丝路最佳女演员奖,她在微博上感谢了全体主创:“祝贺导演尹丽川、编剧阿美,我们共同的荣誉。感谢全体主创,特别感谢姜武老师,没有他的贡献,李红的塑造就不可能成立。”
 电影《出走的决心》中的一场“家宴”,成为女主角李红(左一背影,咏梅饰)出走的导火索。(资料图 / 图)
电影《出走的决心》中的一场“家宴”,成为女主角李红(左一背影,咏梅饰)出走的导火索。(资料图 / 图)
截至目前,这部电影上映一个月,意外地收获了1.21亿元票房,豆瓣评分8.9,成为该网站2024年华语年度剧情片评分第一的作品。
借着《出走的决心》这部新作,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咏梅,以下是她的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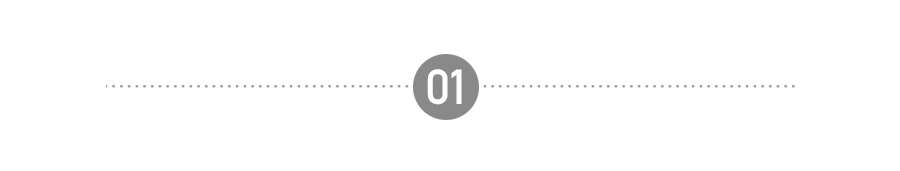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一个有力量的人物”
我一直想演一个有力量的人物,苏敏的行动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力量。
我跟导演、编剧在之前就有过约定,要一起弄一个有力量的、有劲儿的故事。
后来,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了媒体报道苏敏的文章,都觉得这是一个为女性发声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值得被讲述,尤其是苏敏最后出走的行动,太有力量感了,令人震撼。
确实很少有像她这样能走出去的(女性),苏敏是一个特例。我们看到过千千万万个“出走前的苏敏”——那种懦弱、麻木的日常,才是大部分普通女性的状况。现在终于看到有一个很勇敢地去挑战的人,为了自己能选择这样一个未知的前途,真的了不起。
导演一直在说苏敏行为是很“摇滚”的,有一种打破和冲破的劲儿。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必须讲清楚这个人物为什么要出走、为什么要上路,以及是如何上路的。这样一串下来,就能挖出这个人物的本质,展现人物背后历史性、根源性的东西。
苏敏是非常传统典型的女性。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没有哪个女性能完完全全不受这种影响的。但是她骨子里有很倔强的一部分,这也是和我本人性格最为一致的地方。苏敏的这些特质,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多少都会感同身受。
在塑造李红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刻意追求贴合苏敏的人物原型。因为这部电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所以表演上没有要求要在外形或者什么方面去模仿她。之前我和导演也没有和苏敏有过直接的交流,只是在后期宣传的时候才有接触。比起形象上是否相似,我更注重的是角色的内心。
很多观众反馈都说留意到片中李红的笑容,我觉得这就是她性格乐观积极的部分。李红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所以一定要有那样的笑容。她心里面一直有一团火苗,对外部世界是有向往的,然后才有了行动。
李红是在一家人都在为各自的进步庆祝的时刻选择离开的,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她内心长期积累的结果。李红一生都为了家庭付出,他们的欢庆时刻却不需要自己,那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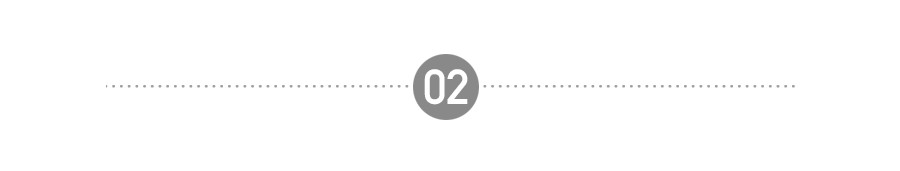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母亲的头发白了
电影的名字叫《出走的决心》,我觉得“出走”更多指向的是精神层面的出口。女性千百年来一直都生活在传统的规训里面,承担着最大的牺牲。
我们之前也聊起《平原上的娜拉》里的刘小样。她也曾经出走过,但后来又回家去了。因为她的婆婆有心脏病,家里没有女人能够搭把手,她觉得不能完全为了自己,必须回去照顾家庭,这是她的责任。
前两天,我们和张越老师在一起做节目,她讲起刘小样的近况。小样现在很开心,在村庄里守着一片土地,依然喜欢读书。但她现在的心境改变了,一边种地,一边在院子里种花,每到丰收的时候就有无尽的喜悦。我觉得她找到了出走的道路,也找到了精神的出口。
当女性成为母亲后,会天然地要去面对母职的矛盾。抛开社会结构的问题不谈,即使从纯生物的角度来说,母亲就是要养育她的孩子,自己没得吃也要给孩子吃,这是天性,是人性中的必然。
但是它的复杂和无解之处在于,生育和养育都给女性巨大的压力,尤其是现代女性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峻,我身边不少母亲或多或少,类似片中的李红,都有些抑郁症的情况。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应该给这种压迫性的东西一个出口,母亲们需要被看见,需要被理解,也需要去觉醒。大家都说要先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全面的牺牲是很残酷的,也不应该去鼓励。
中国的养育关系中,我们对母职的要求很高,很难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苏敏其实也是在履行了母职之后才离开家上路的。我和我的母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关系,我也曾经觉得她必须得为我牺牲,对她有很多的要求,等到我成长了,她也老了,我才理解母亲也应该是她自己,她为我牺牲了太多,却没能获得什么回报。
我开始理解母亲,是我突然发现她的头发白了,那一刻我非常触动,突然想到她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看到那些白发,我很心痛,想到我之前对她的种种要求,甚至还曾干涉过她,逼她做一些决定,我就会很自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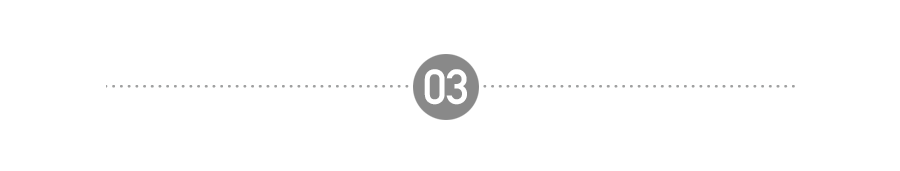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阅读让我建立女性意识
我在呼和浩特长大,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自然也会觉得不够自由,我当时就很想走出去。
应该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些朦胧的性别意识,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就是有一种骨子里的倔强。
其实我现在也经常有“出走”的冲动,比如面对所谓的容貌焦虑,外在的环境和舆论会让人整天苦闷焦虑,但我不要被这个东西左右,一定要冲破它。我觉得跟束缚自己的东西去抗争,这是一辈子的事。
做了“咏读计划”后,我的女性意识慢慢变得更加强烈。可能也和我的很多粉丝是女孩子有关系,她们觉得我很独立,也会经常和我聊天,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力量。所以我想要更多地在意识上给她们一些支持,也会开始系统地阅读一些相关的理论书籍,因为阅读可以打开一个人,进入你的心灵,赋予你更强的感知力。
“咏读”之前,我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去阅读,虽然没有什么针对性,但将近十几年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说实话,以前也不太接触女性主义,读是读过,但是没有那么大量地去读。做了“咏读”之后,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运动,基本是在阅读,女性主义方面的著作就成了我必读的一类。
我学习女性主义是从头开始的,东西方的都看,像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上野千鹤子等,国内学者比如李银河、戴锦华等人的著作,我都一一读过,也分享过我的阅读心得。
这些年大量阅读了女性主义著作之后,我自己在挑选角色或者在一些具体的工作当中,会自觉地承担一些更能表达女性的角色,希望能更充分地展现女性的处境。
《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前期的主创基本是女性,我在这样一个团队里,能够感到女性之间的沟通是更容易的,我们可以互相抵达,也能够惺惺相惜,大家的目标也很一致,就是去为女性发声。
要说愿望,我还特别希望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平台,不是要搞什么性别对立,而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理性地讨论问题。在首映的现场,也有男性观众很不理解,会有一些发言。他们会让我觉得有些可怜,但如果想要让他们明白这样的电影,或者女性的处境,更不能简单地对立,骂来骂去有什么意思呢?
还是应该把问题放到公共空间里面,可以从社会结构中、从文化系统中,大家在一起理性地去讨论,现在也有很多进步的男性,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空间,去进行充分有机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