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梓新
我已经忘了自己是为何想开始尝试英文写作的了。2020年春天英国的疫情刚起来时,我停留在伦敦,想着也可以找一下当地的老师提高英文写作水平。我先自己写了些儿时潮州的故事,在一个找家教的平台上找了一位UCL文学本科毕业的英国女生Chris,一小时25英镑,想让她帮我看看语言怎么样,是否符合母语者的阅读习惯。
Chris看上去有些病态,面色略显灰暗,手臂上有纹身,或者伤痕,像是一个被文学折磨过的敏感灵魂。虽然我们算是校友,但是她对UCL的经历几乎闭口不提。她只提及自己来自伦敦当地有名的中学女校Francis Holland,但在那里遇到过欺凌。她的父母似乎离异,她和父亲住在一起,也似乎挺需要这偶然缘分带来的外快。我们的见面一般都在咖啡馆,疫情之中这些咖啡馆凋敝而冷清,在伦敦时不时吹起的大风中垂头丧气,一起喝咖啡的人也需要彼此有足够的信任。我的英文创意写作就在这样的环境起步,也忘了十年前自己是如何用类似雅思作文的语言完成国际公共政策硕士的论文和考试的。
一对一的辅导其实没有进行多少次。我总觉得她带着一些秘密,也开始觉得她虽然能提供一些语言上的建议,但似乎对我所写的中国故事背景一无所知,让我觉得解释费力。我当时以为我需要清楚地交代一些历史背景,才能让英文读者有兴趣读我的故事。有一次,Chris发消息说,她手摔伤了,去了医院,当周不能来。我让她好好养伤,后来疫情就严重了,慢慢课就中断了。然后我就回国近两年。
去年二月底,我回到伦敦已经半年了,经历了"阳"、流感之后对自己的未来方向仍然头脑不清。我报名了一个在英格兰中部山里的写作课,火车坐了近四个小时去和一群陌生人度过一周。毫无疑问,我是其中的少数派:非白人、男性、外国人,甚至曾经的记者身份也是。有人以为我是流亡者。我大概是文化上,以及家庭生活的流亡者。
那个时候我们还停留在口头读自己作品的阶段。课上即兴完成的段落,经过老师短暂点拨的习作,其他学员理解的眼神,被挑出来嘉许的句子,似乎提供了可以继续前进的信号。一个非母语者在这样的松散工作坊总是容易被宽容的。一群一周后此生不会再见面的人也没有必要太苛刻面对彼此。
英国有着喜欢写作的一些灵魂,他们通常是已经衣食无忧的银发族,徜徉在文学世界里的年轻女生,从事戏剧、影像等相关艺术领域想跨界的人士,以及一些有着各种常规工作的男生想业余写作,比如厨师、广告人,或者高校工作者。
在三明治,我发现我们的写作者也开始呈现这样的趋势。在创作媒介这么多元的情况下,文学仍然是一种吸引人的选择。而和我在英国经历的短期工作坊不一样的是,很多写作者都选择了长年累月和三明治一起写作,并结成了生命中的联系,有的甚至成为夫妻,或者事业合伙人。而且,环境还有些不同。
在中文世界的写作,被理解的成本比在英文世界大得多。
现代中文白话文的创作,本身也不过百年历史,还遭遇过几次断层。人们甚至认为写作是一种特权,或者一种不再合时宜的旧日理想。
我在中文世界的写作,因为有过媒体这样一个行业,让我先尝试了正式发表的感觉。回头想起来,媒体和发表的文学,都是非私人的写作,但媒体又比文学快速。我确实对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较早地祛魅,却一直对自己是否在"写作"这件事迟疑。
虽然,我在2009年出版了新闻专业书《灾难如何报道》,2011年又写了一本粗浅的政治入门书籍《民主是个技术活儿》,但我一直在寻求一种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个探索过程,就是三明治的建立过程。
从2011年3月23日开始,到今天已经13年了。
这个探索的命题,是写作如何成为个体的力量来源,如何成为内心和世界连接的通道,成为一种非功利的日常生活方式,一项持续不断打磨的艺术?
三明治写作朋友珍妮说:语境就像楚门的世界,不离开它,你感觉不到它的边界。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通过跳出有了定式可依却发觉使不上力的中文写作,来到英文写作的语境,才接触到对写作的新认识。
在UEA,我是一个非母语者,一个英美文学滋养欠缺的人(我从小也没读过多少翻译文学),一个纯粹的学生。我离开了中文世界里这些年带来的一个似乎有所建树却仍然模糊不清的写作者身份,所谓的年资也一下子消失。UEA是一个无龄感的校园,我的同学有本科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有六七十岁的长者,他们都平等地相互点评,也不会以各自成长的年代来标签彼此。混杂在其中,我唯一的特色是一个有娃需要抚养的男人。可是这学期新认识的津巴布韦女同学,她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放给在家乡的老公和保姆带着,自己跑到英国来学小说。
现在我来到一个自己的文本要被别人仔细研读的学习阶段。每次要打开老师和同学给我的作品点评文档之前,我要先呼出几口气,这个时候还能感觉到自己脖子后面的肌肉发紧。我在期待或者害怕什么呢?是那些即使检查了很多遍也无法根绝的语法小问题,还是他们不能理解我里面提到的中国叙事背景?又或者是写作是不是合乎所谓非虚构和虚构应有的体例?
课上,同学们呈长方型状围坐,居中的老师发出邀请,让大家点评某位同学的作品。大家都尽量克制而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过于冒犯,又不想让自己的发言没有价值。
"这个故事的叙述节奏太快了","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Time passing的概念,有多重place和identity,但是人物有点太多了,读者容易混淆。" 同学对我的作品有过这些评价。
我拼命地用笔记下意见的要点。想到了录音,但是有点不好意思,害怕没有提前申请他们的许可,就像在国外的讲座,很少有人拿出手机来拍照一样。这些举动都是让人觉得自己很东亚的时刻。
还没下课,一些同学已经通过邮件把他们的点评发到我邮箱了。然后后面的一周里,我会陆续收到十几封点评的邮件我一般不会立即打开。我需要一些心理建设。
打开文档之后,情绪却很快趋于稳定,担心也开始释然。问题其实和自己想象的差不多,对同学喜欢的片段会感到惊喜,他们喜欢的点往往比问题所在更难以预测。但是我发现了,真正的写作并不需要太多解释和背景介绍,即使在非虚构中也是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题材,都需要往人性和日常的方向去写。
文学不在于提供一个完整的叙事,它提供一种情绪的唤起,一种共情的连接。
要达到连接他人,需要先连接自己的内心。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却也是写了多年媒体型“非虚构”的我最陌生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自诩自己生活得像一个个“选题”,因为身上代表了很多媒体可能感兴趣的选题点。就像我现在所进行的"教育游牧"实践,最近也被某媒体报道了。我作为受访者,提供了他们选题的一个样本。但是我发现这并不是我内心所追求的。
内心是我们的秘密花园,这个花园很少对人开放,因为年久失修,连其中的小径自己也经常迷路。但是它隐秘的风景似乎和别的花园有很强的连接力,很容易建立共振。只要这些风景没有经过修饰,伪装,越真实越好。
我发现在文学的角度,和媒体完全相反,越小的切口,越纠结的情绪,越日常的生活,反而是最好的文学题材。它不需要去代表某种群体现象,也不需要分析总结,只需要把作为一个“人”的各种反应和心理呈现出来,便至少是一篇好文章了。所以,
并不需要追求在生活中有什么大事,每个人都可以是作家
。
在三明治写作的上万名朋友,他们都是这样默默地做着。“短故事”的写作者解剖出自己的某个生活片段,丝毫不考虑自己是否迎合了大众关注的热点,只是让这些片段在切口下开始流动,哪怕有时切口便是伤口。
流动是有意义的。情感的流动是人类的需求,甚至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我们的漆黑的电影院里,在安静的剧院里,都在和陌生的演员和观众流动情感。情感的释放是一种结束和全新的开始,也是微小的个人主体感存在的证明。
我们通过写作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微小和敏感,这就是我们最清晰和真实的存在感
。
而持续不断在“每日书”写作的朋友,更加进一步把写作确定为一种
个人可把控的生活日常
。这种方式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先锋的。每天能够写好300字,一个月已经近万字。这哪怕对于一个职业作家来说,仍然是不小的成就。前些天来课堂和我们交流的英国作家Miranda France无意中也提到这一点。
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我有些惊讶,这本叫做《The Writing School》的小说,取材于和我开头所说的那个山中一周的写作项目。Miranda是其中某一期的导师,她把整个课程中的环境和心理描写得特别真实,当然学员的名字和故事进行了小说化的处理。在她带领学员进行Life Writing的时候,她自己也回溯了家庭往事,完成了她一直想写的,在她15岁那年,哥哥自杀的故事。她也在一种引导的过程中,将自己引导到一种和解。
我忽然发现,正是这种
写作者社群之中的平等
,特别是所谓导师和写作者之间的平等,是三明治能够长期生存的根本原因。作为创始人,我没有打造出任何个人权威,很多三明治的读者甚至不知道我。我自己是学习者,也是探索者。而这比太多用个人IP去打造的平台更加平权,更加开放。
三明治是属于对自己内心真诚的写作者的平台
。
在三明治13周年的时刻,我似乎找到了对它的清晰的定义,
三明治是一个以写作为外在形式的内心探索平台
。这些探索,是关于人自身的探索,最终会带领你去很多方向,文学、影像、戏剧、游牧、行动、创业、思想,都可以。这些也都在三明治发生。因而,写作可以是某种社会风潮的发端,也可以是个人转变的青萍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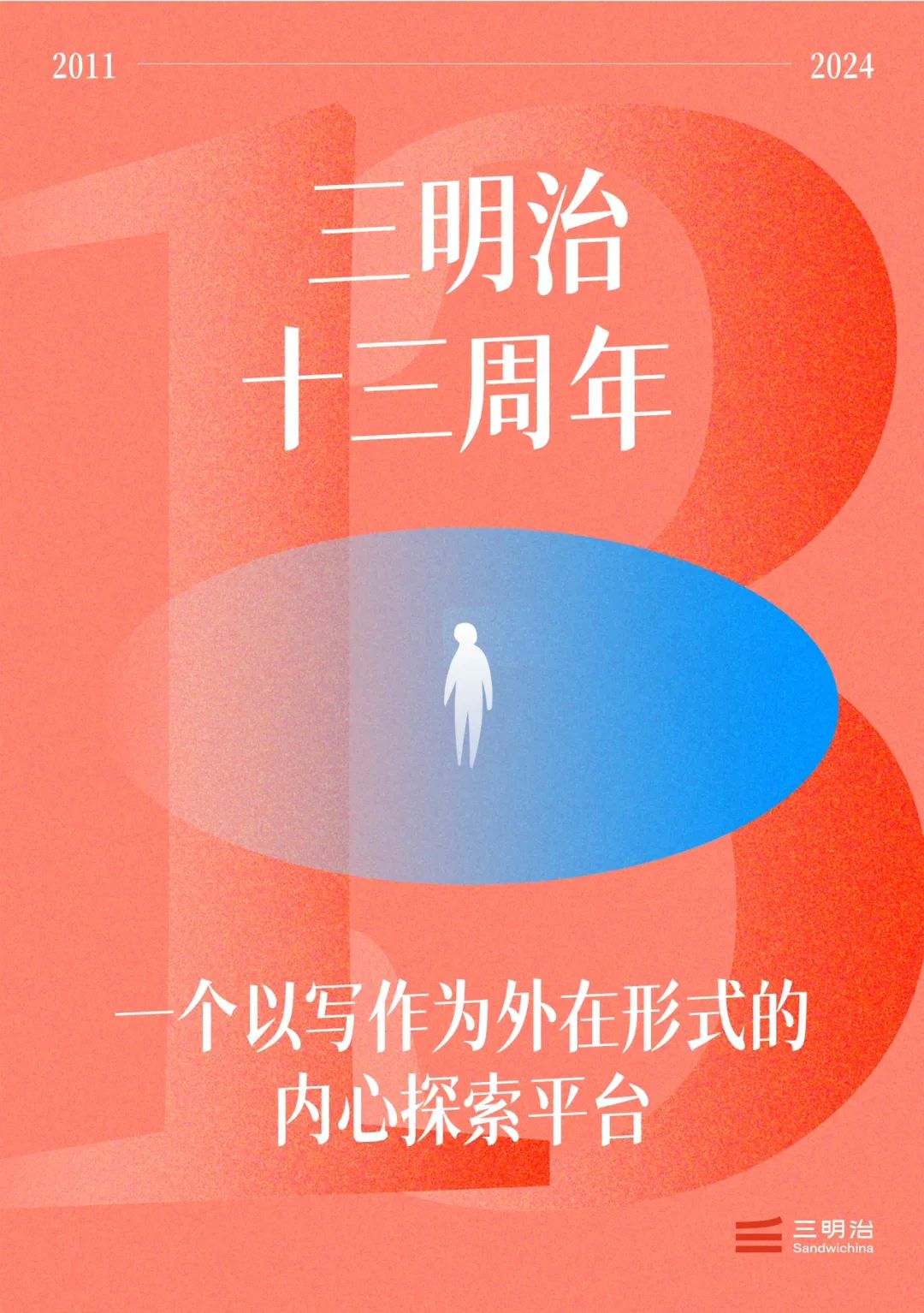
之前我觉得,学英文创意写作就像在陌生的池塘游泳。现在我觉得它不是池塘了,而是一条河流。它是流动的,它也有波浪,它有岸底莫测的水文,也有水面上欢快的春景,它肯定也通向某个汇流的远处。现在,我作为来自另外一个文化半球的游泳者,正在熟悉它的水质——时态、句法、词语选择、文化内涵共同构成的英文语感。
而对于今天的中文语感,我们在从小熟悉的水温里,是否也失去了知觉、敏锐和弹性?我们如何拨开营销的、网红的、功利的写作,重新塑造中文真诚的质感?这也是我想和大家一直探讨的问题。
这个月底,我会回一次上海。想和三明治的写作者朋友,对三明治感兴趣的朋友线下见面聊天。目前一共计划了两场活动。分别是:
3.31日(周日下午)16:30-18:00
我将和《收获》杂志编辑吴越聊聊“跨语言写作的感受,以及如何从内心写作”。
4.13日(周六晚上)19:30-21:30
我将和播客“不合时宜”主播王磬聊聊“离散写作和全球成长”。
扫描下面二维码目前可以分别报名两场活动。
我们上海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