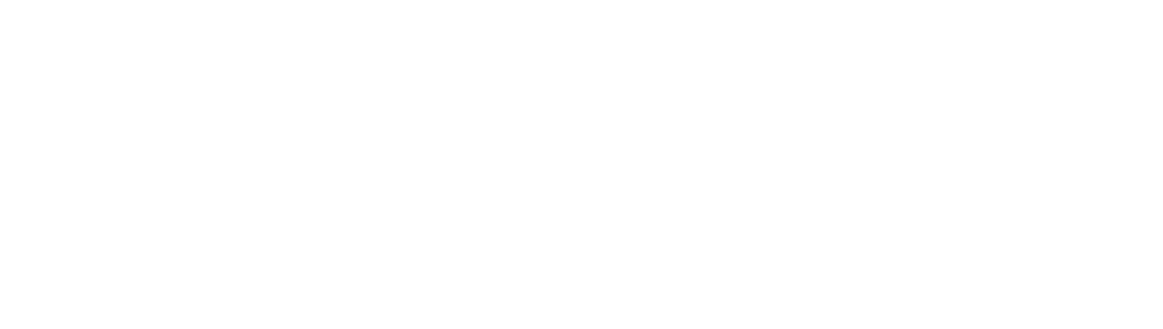
伴随着两部重磅作品的问世——《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帕布罗•拉雷恩在去年冬天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帕布罗钟爱历史题材电影,而这一次,他直接将镜头对准的却是传记电影。
《追捕聂鲁达》取自一位加入了智利共产党,讲述了一位当过国会议员的诗人政治失势的而被迫逃亡的经历。
所以整部电影并未以教化的口吻去讲述,而是带有游戏和连载小说的特征
。

警探布鲁楚诺
对聂鲁达的追捕行动更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聂鲁达的形象看起来很符合以往电影中经典的负面角色——
贪吃,贪图享乐
,
自恋,野蛮等等。
也正式因为这样,他的个人影响并未因自己秘密地下的工作性质而削弱。

而另一边,警探
布鲁楚诺则更像拉雷恩其它作品中的小人物
,无情,纠缠不休,往往成为压迫势力服务的工具。
这两股势力针锋相对,一方求生力量,另一方死亡势力
。
这种对立使得导演能找到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来传达出自己的讽刺意图,并赋予电影一种迷人的辩证风格。
《追捕聂鲁达》给传记类影片加入了一种荒诞手法,与镜头前如同孩童嬉闹般的欢乐相比,电影素材本身的真实性变次要了。
在转入地下工作之前,聂鲁达就表现出他对于乔装打扮的癖好。

在电影开场后的镜头中,我们就看到他在一个化装舞会上扮成“阿拉伯的劳伦斯”示人;不久之后,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他为了逃避警察追捕而化妆成一个老妓女的样子;在影片最后,则更为大胆地化身为阿道克船长。这一对埃尔热作品人物的提及并非偶然,因为电影所遵循的线路很明显:在还原主人公高雅而充满魅力的形象同时,也企图塑造出一个滑稽人物,确保可以展现出聂鲁达的多面性:高贵与粗俗,政治家与冒险家,诗人与浪子。
这种对立统一还以一种比较隐蔽而少见的空间呼应方式表现出来:在电影的第一组镜头中,聂鲁达在和一群包围着他的议员激烈辩论,而辩论场合竟是拉莫内达宫中的豪华卫生间,里面配有雅致的小便池和盥洗池。

而同样的空间场景不久后在电影中又重现,而这一次则是在聂鲁达为避开警方大搜捕而躲进的一家妓院沙龙里。
于是,电影一上来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带有布努埃尔风格的“沙龙政治”,这一空间既是概念上的同时也是具体的,而聂鲁达则以一种令人惊叹的轻盈姿态,从一间房穿梭到另一间。
这种如同滑稽剧的手法很受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称赞。
不过,这种荒诞手法的运用,不仅仅表现在乔装情节与夸张色彩上,还表现在对地位的颠覆中。
在这种情形下,这种颠覆本身也构成了电影的风格之一。

在这场大型追捕游戏当中,电影始终被一个主要问题所萦绕:追捕者与被追捕者,谁才是游戏的主导者?
在现实中,聂鲁达总是领先一步,但布鲁楚诺却是这一故事的叙述者,他的内心独白同时要不停地跳回到对手的行动和对话上去。
换句话说,讲述历史的人正是被历史所超越的人。
“我从一张白纸中走出来,来寻找我的黑墨”,电影开场几分钟后,这位警探的身影出现在大银幕上,伴随着这句抒发内心的旁白。
由此,电影独立于它的主题之外,构成了一部人物建构的专论。

布鲁楚诺在故事讲述中占据着主导权,但确是一个没有内核的人物,需要聂鲁达这个太阳来给他提供故事灵感的光热。
布鲁楚诺和聂鲁达两人互为对方的噩梦,但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追捕,不如说是两个人的互相磁化,双方以一种近乎心灵感应的方式来猜测对方的意图
。
两人最后的对决,也并非西部片中常见的雪中决斗,而采用的是塞吉奥•考布西式
的结局方式,一方被塑造出自己的另一方所吞没。
这种游戏般的相干性也有它的局限,尤其是当导演的拍摄风格对影片的视觉结构加以影响时,画面看起来像镀了层薄膜:刺眼的逆光效果令人怀疑其四周布景是不是都安装了灯光,此外还有复古的透明感,伴随着空间跳跃的切分式剪辑,有时看起来奇妙无穷,有时却让观众不明所以。

电影还少不了一些如埃皮纳勒版画一样的画面:工农群众们仰着冻僵的脸,听聂鲁达那娓娓动人的演讲。
对于拉雷恩来说,这很有可能是一种证明自己没有走进“出版一部传奇故事”误区的方式。
而在这些有教化动机的画面当中,还穿插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小细节:他的妻子德里亚跟聂鲁达建议“换个声音”,用读诗的语调去读政治宣传册,用政治动员的语调去读诗,在这种即兴的演讲练习中,他似乎也找到了新的灵感。

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些电影的内在逻辑,这逻辑存在于电影节奏和演讲腔调的频繁切换中。
同时,观众可能也更希望这种政治与诗歌之间的对换方式也能影响一下电影本身,因为它虽然有着出色的叙事结构,但是表现手法却略显单一。
导演拉雷恩的才华无可否认,但是不足之处也相当明显。
或许他也应该去“换个声音”,来打破自己可能有些推崇过度的信条。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