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作家):
关于儿童文学,首先想到的是这一文学类型的读者界定问题。以前称比儿童文学高阶一点的,叫“少儿文艺”;现在又从台湾传过来一种桥梁书的概念,特指为解决儿童只爱看绘本认字太少的问题,专门出版的一类有插图但文字比例大大增加的读本。这一类书籍的目标读者,通常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们。
那么,此处讨论的儿童文学到底包括哪些形式的书籍,又究竟分别面向哪些人群?
甚至连“儿童”同样都是不够明确的范畴。国家规定未满14岁的都可过六一儿童节,也就是说,14岁以下的孩子都被视作儿童,更狭义一点的分法,则特指6岁到14岁之间的孩子。1岁以下的称为婴儿,1到6岁则是幼儿。
自英美舶来的儿童心理学里,从出生至十七八岁都属于儿童,并可根据心理发展特点划分为:乳儿期(出生至1岁)、 婴儿期(1至3岁)、学前期或幼儿期(3至6岁)、学龄初期(6至12岁)、学龄中期或少年期(12至15岁)、学龄晚期或青年期(15至18岁)。这也无怪乎有儿科医学教授认为,“我国儿童的年龄应该推后4年,由0岁—14岁推后到18岁”
。
这一呼吁的直接影响就是18岁的人看病应该挂儿科。在美国,儿科的面向人群甚至包括21岁以下的人。
与这一心理学划分相对应的儿童文学学科划分里,也将目标读者划分成五个年龄阶段:婴儿期(1-3岁),幼儿期(3-6岁),童年期(6-12岁),少年期(12-15岁),少年后期(15-18岁)。
而读者界定一旦清晰,我们将要讨论哪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文学,就变成相对复杂的、一篇文章根本讨论不完的事。倘若抛开目标受众不谈,儿童文学最权威的定义到底又是什么呢?
百科词典里,“儿童文学”本身是一个多义词条。除去《儿童文学》这本团中央和中国作协共同创办的杂志和若干童书丛书外,儿童文学的基本定义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对象,又分为婴儿文学、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体裁有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曲艺、儿童戏剧、儿童影视和儿童科学文艺等。偏于文学,适合3至17岁阅读,老少均可品味。
3至17岁,比上文界定的“1至18”少了整整四年。
但更让我注意的,是“老少均可品味”这六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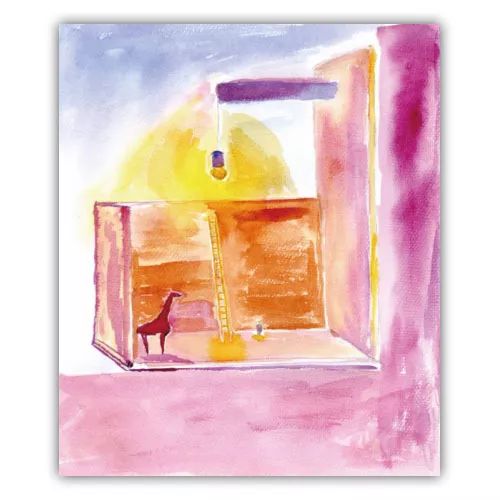
《盒子里的小马》 文珍 绘
就我自己而言,长大以后依旧会读的儿时读物还有哪些?前几天我刚重看了《洋葱头历险记》和《假话王国历险记》,都是意大利作家贾尼•罗大里的经典著作,任溶溶翻译的。再看仍觉津津有味。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痴迷任式翻译,他自己的童话我也喜欢,最出名的,当然就是曾被拍成动画片的《没头脑与不高兴》,这篇据说在咖啡馆里半个小时写就的小故事,整整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儿童。
家里书架尚属于儿童文学范畴的,还有好几个版本但同样都是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全集、吴承恩的《西游记》、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弗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鲁迅的《朝花夕拾》、詹姆斯•巴里的《永无岛》(书柜里另一个版本译作《彼得•潘》,还有一本叫《小飞侠》,此外也有英文版的
Peter Pan
)、宫泽贤治的《鹿舞起源》(收入著名的《银河铁道之夜》和《风三四郎》)、叶圣陶和严文井的童话故事集,以及宫西达也和其他绘本作家的若干儿童绘本等等。
这些大多是我小时候就看过,长大后依然不能忘记的书。
很奇怪的,曾经那么喜欢的郑渊洁童话,长大以后却一本都没有留下,也没有专门买来纪念。完全属于童年的同步读物,长大以后却不愿重读,可能因为那个反抗学校教育体制的叛逆年代早已经过去了。
就我个人而言,儿时读物里还包括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一本叫做《科学世界漫游》还是《科学导读》的科普类读物(现在再也找不到了),袁珂的《中国神话故事》。《堂·吉诃德》《动物庄园》和《骑鹅旅行记》如果也算,那就还包括金庸、古龙、张爱玲、陈丹燕、琼瑶、亦舒。
这些少年时代找到就囫囵吞下的读物,同样也参与建构了我十八岁之前的部分人生观。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儿童时代的读物,也不过是《山海经》《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他那个时候还要更可怜一点,市面上根本没什么专门的规定给小孩子看的书,除了《幼学琼林》《弟子规》《三字经》和《千字文》。
孩提时代遇到的书,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一生造成影响?
同样以自己举例,《小王子》里的玫瑰花,《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小豆豆和巴学园的校长,都会变成我生活中随时可能提到的人物;《海的女儿》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还不是那富有牺牲美感的爱,而是提供了一种关于蓝的想象:比矢车菊还蓝的海的深处到底有多蓝?堂·吉诃德的风车和卡夫卡的城堡所形容的困境有云泥之别;而谈话间形容一个让人不安的东西在盯着你,大家都知道哈哈大笑地说:老大哥在看着你!这当然得归功于从小就读过的《动物庄园》;在城市遭遇大拥堵时,也很可能会冷不丁想起舒克和贝塔的那艘可折叠、缩小、隐形的五角飞船来。
小飞侠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我们的集体修辞学。我们整整一代八〇后,都被外部强行诊断得了“彼得·潘综合症”——其实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得了——
具体症状是固执顽强地不肯长大,幼稚成瘾,一直到30多岁,心里面依然住了一个逃避尘世的小孩
。哪怕为人父母了也没用——很可能会和自家小孩抢玩具玩,一起看动画片。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会在但丁开始漫游的年纪,写《初夏童话四则》的原因。年纪大了,受挫折变多,知道世界的更多暗面,但与此同时,心底那个一直开窗睡觉暗自期望被小飞侠带走的小孩却一直没有死——就像叮铃铃一样,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孩子还相信小仙女的存在,那么她就会依然顽强地活着。
但这些偶一为之的童话故事,其实也不完全是为真正的小孩子们写的——比之定义要求的“通俗易懂,活泼生动”,这些故事的推进也许仍然太缓慢了一点。它们更像是为十八岁以上的,那些不大甘心自己被赶出儿童阵营的大人写的。
坦率地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儿童文学更难写的题材了。那是一类在人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黄金年代遇到,可能对人发生最长久影响的书籍;面对的又是值得为之付出一切都不为过的最纯净的心灵!好的儿童文学,譬如时至今日仍然盘踞在我书柜里的那些,也同时要求创作者有比一盎司黄金还要纯粹珍贵的童心。国内那么多市面上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在“钱多人傻速来”的创作方针指导下攒出来的所谓童书,残忍,世故,充满了成人世界的丛林法则和低级趣味,或故作天真,丝毫不尊重儿童世界的逻辑和美学,那些不叫儿童文学,只能叫冒充儿童文学侥幸混入学校的商品和赝品。
也许应该修改儿童文学的立法:从六岁到一百岁都可以读的书,才配叫儿童文学。
如果有人能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守卫麦田那样竭尽全力捍卫这片土地,甘愿耗尽全部心神去写作真正可以传世的儿童文学,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后辈读者们的幸运,更是所有大人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