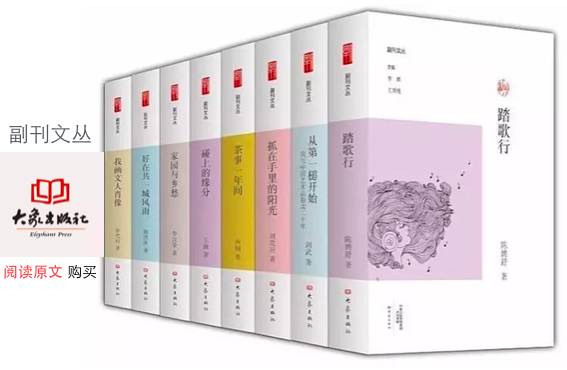《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说不完的欲望与诗
文|韩浩月
是简简单单地看一次电影,还是在电影里活过或爱过一次?想想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你就能轻易找到答案。
好的电影不敢一次看太多,就像找到对的人,一次只能爱一个。但春天与樱桃树的关系不是这样——春天浩荡,樱桃树有许多。观影人谁敢把电影比作樱桃树,谁又敢把自己比作春天。

文字的好处是可以过滤掉那些让你昏沉的情爱体验。
在晚春下午阳光里读影评人阿郎的影评集《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有种舒适的倦怠感。书中收录的那些情爱电影大约一半看过,一半没看过。文字的好处是可以过滤掉那些让你昏沉的情爱体验,给你一个通达透彻的答案。对于懒惰者来说,绕过过程知晓答案,是件省心的事,如同浪子绕过爱情直达床畔。
阿郎写作这本书所花费的时间长达八年。八年看这么些电影写这么些文字,不算多。所以他的文章给人以一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感觉。一静一动,以静制动,他是沉舟,电影如千帆。读过本书,情感再粘稠的人,也会产生点“片叶不沾身”的跃出感。

《巴黎野玫瑰》电影海报。

《年轻的亚当》电影海报。
阿郎的文字口头禅是“喜欢极了”,这四个字常常在阅读过程中被捕捉到。比如他在评论《巴黎野玫瑰》时写到,“喜欢极了贝蒂出现时的场景,镜头缓缓摇升,全景,阳光明媚……”,在评论《年轻的亚当》时写到,“喜欢极了影片开头,水波潋滟,一湖如碧,一只高贵的天鹅骄傲地游弋……”
在我所了解的语意当中,阿郎的“喜欢极了”并非单纯是字面层面的“极致的喜欢”。这四个字还包含有诸多微妙的表达,比如欣赏、震撼、享受、愉悦、动心、神驰……但当这些包含了嗅觉、触觉、味觉等在内的敏感气息,被归于“喜欢极了”这种朴素的、口语化的表达之后,让读者也产生了心旌摇曳的感觉。
如果在职业上做一个比喻,阿郎不像是一位影评人,而像一位放映员。他抚摸着并不存在的放映机,用语言勾勒画面,为读者“放映”那些让他在深夜里觉得百花缭乱的故事。他要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尽量用速写的方式描绘出那些色香味俱全的场景——在电影审美方面,阿郎对画面与场景的关注似乎要多于台词。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艾曼纽起床,那是一个华丽而凌乱的房间,化妆镜和巨大的床铺遥遥相对,化妆镜左手是寂寞的沙发,在餐桌边垂头丧气;餐桌上的残羹冷炙暗示昨夜曾经的狂乱,可以想见,我们的主人公怎样在桌前和人举杯,并怎样在那个夸张的大床上,度过了昨夜。”这是阿郎在《艾曼纽》中的一段场景描写,这不是对画面的复原与再现,而是灌注了个人格调与情感之后的重新创作。这也不是对电影的一种解读,而是用小说家的口吻和侦探家的心理,带读者进入电影、参与电影。

阿郎在他的影评文字中,融入了许多诗的语言。
“她的睡裙不敬业地散落开来,耀眼的肌肤在午后的阳光下生机勃勃”,“回忆有时候太过孱弱,抵御不了短小精悍的真相光临”,“食物、爱欲、子弹以及那天早上的阳光”……阿郎在他的影评文字中,融入了许多诗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稀释于他的全部文字当中,与他描述的那些电影画面相得益彰。几十部情爱电影被凝结为两个关键词“欲望与诗”,诗成为阿郎解剖故事人物欲望世界的手术刀,而诗也恰恰调和了电影作品那些指向纷乱的价值观,让那些已经位列电影长廊中的艺术形象,拥有了永不褪色的外衣。
作为本书作者,阿郎拥有冷静的眼光和安静的笔触,但却能够敏感地发现电影里角色内心深处的热烈。因此阿郎的身份既是作者又是媒体,作为作者,他从第一观影现场带来丰富感受,作为媒体,他对扑面而来的影像洪水进行深切加工,捧给读者最有价值的内容,这大约也是影评人存在的价值所在。《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作为一名影评人所交出的答卷,里面写满了所有影迷都感同身受的爱。

-END-
六根者谁?
李辉 叶匡政 绿茶
韩浩月
潘采夫 武云溥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微信号:
liugenren
长按二维码关注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