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社科报 洞见
原题:今天的中国怎么处理思想问题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任剑涛
◤人们心中都在探问:中华民族未来会走向哪里?
有人提倡回到中国古典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历程远未终结,还需要谦虚地谋求深度现代转型进路。我们怎么去解答这样的问题,以便敞开中华民族发展的广阔天地?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思想,而且这个民族只能在思想中升华,绝对不可能在物化中升华。
中国GDP总量的迅速做大,驱使人们形成物化思维:以为一个GDP数据足以表明中华民族的崛起,以为在物质中民族已经升华。对一个民族来讲,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展开思想的旅程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原因在于,人只能在生存的基础上才可能思想。凌厉的思想旅程和原创的思想锋芒,不可能由一个饥肠辘辘的民族展现出来。 但问题在于,物质丰裕了,思想并不自动跟随。思想的贫困极有可能与物质的丰裕突兀相伴。为此,需要另辟话题,审视思想对民族发展的独特价值。
在现代世界,伟大的思想精英登顶世界巅峰,仍由欧美思想家领衔。科学精英群体自不待言,人文理念的新诠毋庸赘述,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新人耳目。

须知,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伟大的创造。英国人经过近五百年的坚韧努力,创制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的现代范本。美国人承接了这一现代范式,并加以再创造,以实用主义为思想导向、以大众民主整合国家力量、以流行文化扩展国家影响,创造了当代思想的独特景观。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讲,一个落后的民族,也可以演奏思想的第一小提琴。注意,他所指的落后民族,就是德国。19世纪的德国在物质世界、社会政治发展方面,是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来自法国的征服、囿于君主专制,让德国的现代转变异常困难。德国古典哲学家登上德国历史舞台的时候,德国人正处在殖民统治的悲壮情景中,一个思想家要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仅要面对专制国王的压力,而且要面对法军驻扎者的压力。思想之难,可想而知。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并没有畏缩,而是在民族的悲壮处境中,展开自由的哲学旅程,成为欧美思想界的第一小提琴手。德国古典哲学,让落后民族发现了表达自己民族思想的独特方式,让民族更为深沉,使思想更臻成熟。尽管这是不得已采取的思想表达形式,但确实发挥了促使民族深沉思考、不至肤浅抱怨的巨大作用。
今天,中华民族反省自己民族的健全发展,思索自己对人类应担的使命,亟需广泛而深沉的哲学思索。就国家状态而言,中国绝对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国家悲剧处境。他们着力筹划的,是如何用哲学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挽德国于狂澜既倒之际;我们已经挣脱民族的生存危机,但谋划民族的健全发展,更需要如履薄冰的审慎。任何浮浅乐观之论,都会误导中华民族。
我们民族今天已经有些乐不可支的感觉。这种状态,与德国人在内外压力之下做出的深沉哲学解答,正相反对。难道超越生存危机的民族,就勿需在德国思考方式中得到启发?未必。今天的中华民族,对自己担负的发展责任,承担的人类使命,必须进行高度理性的筹划,才有望真正承担起民族对自身的责任、对人类的义务。

一个民族必须具有思想活力,它才具有思想穿透力;也必须具有思想穿透力,才能够透悟民族的众生,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实际遭遇到了怎样的思想难题。区分思想与激情、思想与学术、活的思想与死的思想,以求真精神解答真实问题,才能给民族前行提供足够精神动力。
一切真正活的思想,一定是活在当下的思想。当下的国人,要能够承接得住历史厚重的思想遗产,同时穿透现实世界的迷雾,直抵现象世界的根柢,才能以活泼的思想呈现活性的发展。一切历史上的活泼思想,深藏在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它靠活在当下的人来承接,并续写它的历史辉煌。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有无比辉煌的思想创造,如果没有活在当下的人承接这种活的思想,并且发扬光大的话,活的传统思想就变成毫无活力的历史陈迹,变成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里的遗存”。对于它,人们尽可观赏,但它已经是“死的东西”。
只有当一个民族当下活着的成员能够承接得住自己古代先贤的思想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它的思想活力才足以引导当下活动者,继承历史、切近当下、不惧困境、重现辉煌。活的思想是引导民族前行的灯塔。
在民族的思想演进上,时间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时间刻度,可以指向过去、面对当下、指向未来。但千万不要遗忘,一维时间的连接点,一定是当下。如果民族的当下主体成员承担不了延续历史思想的责任,而仅仅以一种好古的态度,以放大镜观赏思想遗产,对民族当下状态视若未睹,且以清高姿态冷对现实,以为历史上的伟大观念足以指引未来,不费吹灰之力续写伟大民族的思想世界史,那无疑是一种幻想。
活着的思想一定活在当下。它不是既定历史的完成状态,也不是只能在未来发出夺目光彩,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勾连历史和未来的活的思考情形,呈现一个民族伟大思想的当下而即时的活力。一切以中华民族古典时期的辉煌思想来描述我们民族的光明未来之举,都只是对民族成员未来忐忑的一种宽慰。这甚至是我们民族思想能力不足的表现。
回想我们这个民族,自明朝厉行海禁,对外封闭;对内警惕异端,压制思想,造成全民族创制能力的严重衰变,无力在思想上再造辉煌。结局首先是明被清征服,其次是更为专制的政治统治,进一步造成民族创造力的明显萎缩,以至于站在现代转型的门槛边,完全缺乏心力领先世人,甚至缺乏心力予以承接。“落后挨打”之命,就此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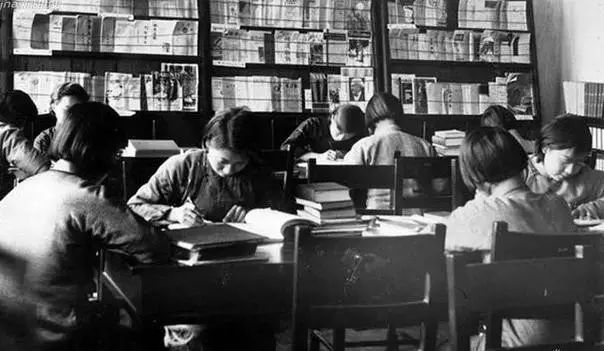
整个清代思想封闭,民国思想界倒是非常活跃。古今中西理念的碰撞,呈现了民国思想繁荣的局面。但民国的思想远不值得表彰。“国粉”、“清粉”不解的是,晚清也好,民国也好,即使是富有穿透力的思想家们,思想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救亡。他们完全没有心力在救亡之外,为民族、为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李泽厚概观这一时代特征而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恐怕不太准确。因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来说,几无启蒙所可表达。他们紧紧围绕着民族群体的生存权,国家建构的自决权,也就是救亡这个唯一主题,来展开紧张思考。即便借助启蒙话语,也不过是为了解决国家如何不被列强所灭的难题。
中国真正的启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时,中国一方面要解决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聚集古今中外思想资源,聚精会神地求解民族未来、当下处境和人类担当这类问题。80年代,国人以活的思想展现了一个活力中国,关于国家和人类的宏大话语初登思想舞台。

当下中国思想界,令人极为遗憾地出现“两个丧失”。
其一,丧失了创制宏大话语的热情和能力。
1990年后,学术界认定宏大话语等于空虚、玄妙、无用、幻想。学者们最擅长的活,就是所谓文本解读:拿三五本书写一本书,三五十本书注解一本书,以此赢得人们“好有学问”的赞叹。这是我们民族思想能力退化的表现。深度转型的中国,需要宏大话语的创制。将近三十年前,中国走到了现代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将以什么样现代的国家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如果国人在思想上回答不了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宏大话题,民族的未来也就休提,遑论所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其二,丧失了深沉思想的冲动与热情。
1990年以后,中国学界的精力大致放在学问的扎实程度和细微功夫上,这当然不能说不好,但以拒斥思想为前提条件,就令人担忧了。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问题,并不是学界自责和被人自责的大而不当。而是同时呈现出可怕的双失状态:大而不实,小而不精。大的不实,是指学术界建构宏大话语的时候,搭建不起像样的思想体系。学术界提供不出一个让民族升华的价值观念,帮助解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促使民族登顶世界思想巅峰。小而不精,是指埋首书斋、深耕字里行间的学术功夫,并没有精致到令人诚服的地步。学术界并没有因为提倡学术,而真正贡献让人感觉赏心悦目的学术精品。
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讲,需要避免从思想者变成思想警察。对思想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思想者畏惧思想市场,摇身一变,成为思想警察。这一身份变化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演变成:理解思想的思想者变成监督思想的警察,动辄认定这种思想有什么危险,那种思想有涉嫌政治犯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阻止人们展开思想的历程,扼杀民族思想活力,终至思想禁锢,头脑简单,全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成为缺乏基本思想能力的弱智民族。
思想者之乐,乐在思想的过程,乐在直达事务的本质,乐在穿透一个事务表现的满心喜悦。一个思想者,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社会意图、政治目标。但这样的思想者却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力,理论创制能力,以及挣脱当下束缚展望民族与认可未来的宏大视野。
学术思想家应当具有高度的共同体意识,促成大家都信守的共同体规则,只要不借助权力压制思想,学术思想界足以按照共同体的规则,为民族走强做出突出贡献。这是当代中国迈过发展门槛所亟需的。
思想如何使一个民族升华的命题,涉及思想家的国家担当与人类责任。也许人们会认为,专业知识分子不足以思考承担这一使命,尤其是那些科学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他们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业,常常为专业所蔽,缺少公共关怀,即便是心忧天下,也不知怎样恰当表达自己的满腔热情。因此,唯有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够有效担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

此说有误。对今天中国的深度改革与持续发展来讲,专业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容小觑、非常紧要。科学家饶毅写过一篇文章,解释“中国为什么需要‘科学知识分子’”非常之棒。对今日中国而言,对精确知识的追求远未达到应有高度,社会公众甚至排斥科学知识。弥漫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迷信,证明中国的现代品质急需提高。这都需要专业知识分子以其精神的专业知识,指点社会公众,促使中国社会提升科学技术的认知水平,促进中国社会增强现代基因。
每个民族有思考能力的成员,需要把道义的责任放到自己的肩上,富有穿透力地展示不同意见,促使公众和当权者理性决断。在今天,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需要全民族成员具有底线的思想能力,理性、开放、对话、选择,俾使全民族具备现代思想素质。
中华民族必须以自己民族成员的思想判断力,而不是学术知识的积累能力,直面当下处境,为民族未来理性谋划,为民族克服现实困难展开合作,为民族的人类担当进行共谋。就此而言,思想者越多,越能够让我们民族迈过现代化门槛,打破以物质实力提升判断民族是否崛起的思想迷思,以民族的现代综合素质提升,自主且顽强地推动可持续发展,进入承担人类使命,尽到一个伟大民族对人类应尽的责任
。
(感谢“爱思想”支持,文中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原载于社科报总1531期。)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
shehuikexuebao
欢迎转载原创文章。如转载,请注明:本文首发于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
shehuikexuebao。

长按识别二维码
立即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