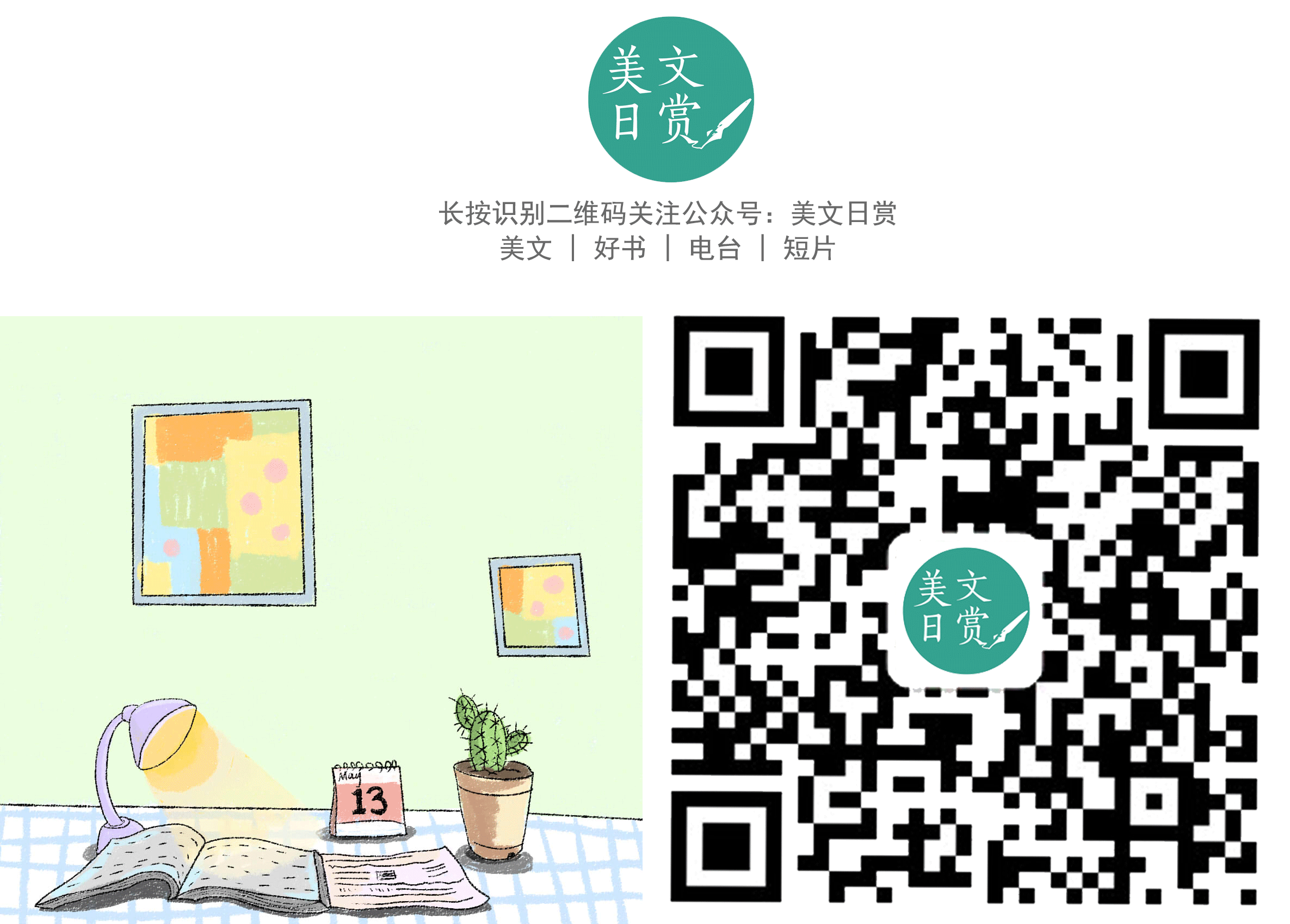文 Jame
那天和朋友聊天,他说,我们好像总是被集体绑架着。不同的是,以前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被别人修剪掉了。而到后来,我们就甘于做一个平庸的从众者了。
我想了想,好像有点道理喔。
小时候,每个学期总有那么几次,校领导会来听课。班主任总会特别紧张,提前就开始准备——备课、动员甚至是排练:
老师会在前一节课把流程走一遍,把上课的内容给我们讲一遍,但要我们保持书本整洁不能有太多笔记。并且叮嘱我们在提问环节积极举手、记牢答案。在公众课上回答到问题的同学是有甜头的,可能是老师奖励的一个本子。
为了公众课不出岔子,老师有一次甚至让班上比较调皮的郭某,在公众课时去她的办公室座位坐着。
但后来的公众课,郭某信誓旦旦地跟老师承诺了绝对不会给她添乱,老师心一软,就让郭某留着了。得到老师垂青的郭某,在公众课时候表现积极,在提问环节把手举得老高。老师自然就把这个机会交给郭某了。
万万没想到,郭某站起来之后,答了前一半,突然语塞、脸红,支支吾吾地憋出一句:“老师,我忘记答案了。”当时,全班哄笑。我猜,老师应该很是尴尬。
在那节课之后的班会课,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了,老师给在公众课上“表现积极的同学”颁发奖励。心灰意冷的郭某大抵也知道自己没戏,瘫坐在位置上。
但没想到老师还是念到他名字了:“郭XX。”
郭某立刻从位置上弹了起来,想要上讲台拿他的奖励。料想不到,老师说:“你是不是存心给我添乱的?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记不住?你怎么那么没有集体荣誉感?”她严肃的语气,不容置疑。班上的同学甚至不敢笑。
平时野得很的郭某,当时只是耷拉着脑袋,小声喃喃自语,不知道说的啥。
后来,我们升了一个年级,换了班主任,但是上公众课的套路还是一模一样,“你怎么那么没有集体荣誉感?”这句话也萦绕在我身边许久许久。
小学的时候,我扫地没扫干净,班级被扣分了,老师批评我“没有集体荣誉感”;高中那会,我早上迟到了,老师也说我“影响全班人”;现在上了大学,不去班级活动、不和舍友打游戏, 也让人觉得我不合群。
久而久之,我也真的觉得“没有集体荣誉感”是一项很严肃的批评,它像是对一个人道德和人格的否定。没有集体荣誉感的人是自私的。
印象中,唯一一次“老师被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感动了”,是高三那会儿。我们全班为了响应学校的号召,参加拔河比赛,还拿了名次。结果我们全班男生被麻绳磨破了手掌,腰酸背痛了好几天。
那会儿的晚自习,不少人是双手贴满胶布,在一摞摞的试卷上歪歪扭扭地奋笔疾书。可是大家都没在抱怨,反倒是积极地讨论下场比赛的战略。
在所有人都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的年纪,我们总有一种说不清缘由的强烈的集体意识。我们愿意为了“班级的荣誉”,在那些我们当时和现在都觉得很傻缺的广播体操比赛、队列比赛上面喊到喉咙嘶哑。
而且,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落单的人总是可怜的。于是我尽可能地融入一个集体当中,尽力表现、站住脚跟。
到了大学,尽管有些人像我这样游离在班级外,但其实也是因为选择多了,我们把情感寄托了在另一个集体里,可能是宿舍、社团或是学生组织。
大一在学生组织当干事的时候,大家都是热情满满。身边不少人,可以开会开到临晨、做策划书熬夜通宵,还有人可以为了活动“出人力”,翘课去做些布场、看守物资之类的琐屑的事儿。
有一次,我在的学生组织举办了一场全校性的活动。所有干事部长都在转发活动链接到朋友圈,唯独我没转。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活动没啥吸引力。
结果第二天见到部长,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没转?”
我一阵尴尬,摸着后脑勺说:“啊,忘了。”当即掏出手机转发链接。
那时候,我们在枯燥而糟糕的活动里呆了一整个下午,却因为有朋友陪着聊天,倒觉得时间过得挺快。归属感或许就是这样慢慢地建立起来了。
每一个我呆过的集体,大家在散伙的时候,总是会哭得稀里哗啦、喝得一塌糊涂。可是第二天酒醒了,各赴前程,找到新的可以依托的集体之后,彼此的联系又渐渐淡去了。
最后发现,大家重新聚在一起只能聊当初一起当初做的傻事儿。
突然想起有人说过:“你以为你在合群,其实你在堕落。”
张戎的《鸿》里,抗战后国民党统治下的锦州城弥漫着恐怖的氛围。有抱负的军官们终究慢慢被国民党内部腐败的氛围同化,终日留恋花天酒地。
其中一位潜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下共产党员,“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必须强迫自己每日酗酒、赌博。
但最可怕的是,当我们从“被修剪”到自愿从众之后,我们可能会恍然发现:原来我们对集体的屈服,得益的可能只是极少数的人。
在我高一那年,回了一趟小学,发现那个批评郭某的班主任的办公桌已经搬到主任办公室了。我看了看那间办公室,另外几个主任全是四十好几的模样,独独班主任才三十多。
我唏嘘不已,但还是想着和老师唠嗑唠嗑家常,老师第一句话却是:“哦,我记得你,但是一下子想不起名字了。”
我很想相信她的话,可惜做不到。
大一那年,学校的某个学生组织拿了全国性比赛的冠军。我的朋友圈被这个组织的朋友刷了屏。
然而同样是这个团队的Black却没转,那晚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像我当初的部长那样问他:“你为什么不转?”
他很是激动,说:又不关我事,参加比赛的其实就那几个人。荣誉、奖项或者加分什么的全部没我份。
咪蒙说她当初开公司的时候,对她的员工描绘了一幅宏大的愿景:“我想做出最牛逼的影视作品,改变国产影视业。我开公司绝对不是为了赚钱,赚钱太低端了。”
结果一群员工死心塌地地跟着她干活,最后她的公司面临财政危机,她只能哭着辞退了一批人。
我也发现,当我慢慢长大,集体利益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冲突似乎越来越频繁。
当初我在所公司实习,那是一间氛围很好、坐落在CBD的公司,工作也挺有趣的。最初几天在这上班,我每天出入在这也都打满了鸡血。
可是这份热情并不能持续超过半个月。我发现每天我的实习补贴压根儿不够我的交通和伙食;我的工作是按量分配,报酬却不会以绩效发放;甚至,我经常还要加班得比大部分人还要晚。
我感到,我的回报远小于我制造的价值。后来我实在熬不下去,在实习期满了的那一天我也就离开那间公司了。
“你怎么那么没有集体荣誉感”,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句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是一种违背自愿原则的奉献主义。
虽然说,集体的利益的确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但,我一直不喜欢无私乃至牺牲性的奉献精神。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接下来的生活里,也一定常常会遇到个人价值实现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时刻吧。如果有人选择了前者,能不能不要再谴责他呢。
——摘自《不管怎样,这就是20岁的我们》

《不管怎样,这就是20岁的我们》是WhatYouNeed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收集了WhatYouNeed的部分编辑在大学期间关注度较高的作品。和市面上流行的励志小说不同,这本书并不是告诉你要怎样做,而是作为同样的人,讲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经验,迷茫。让你思考,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