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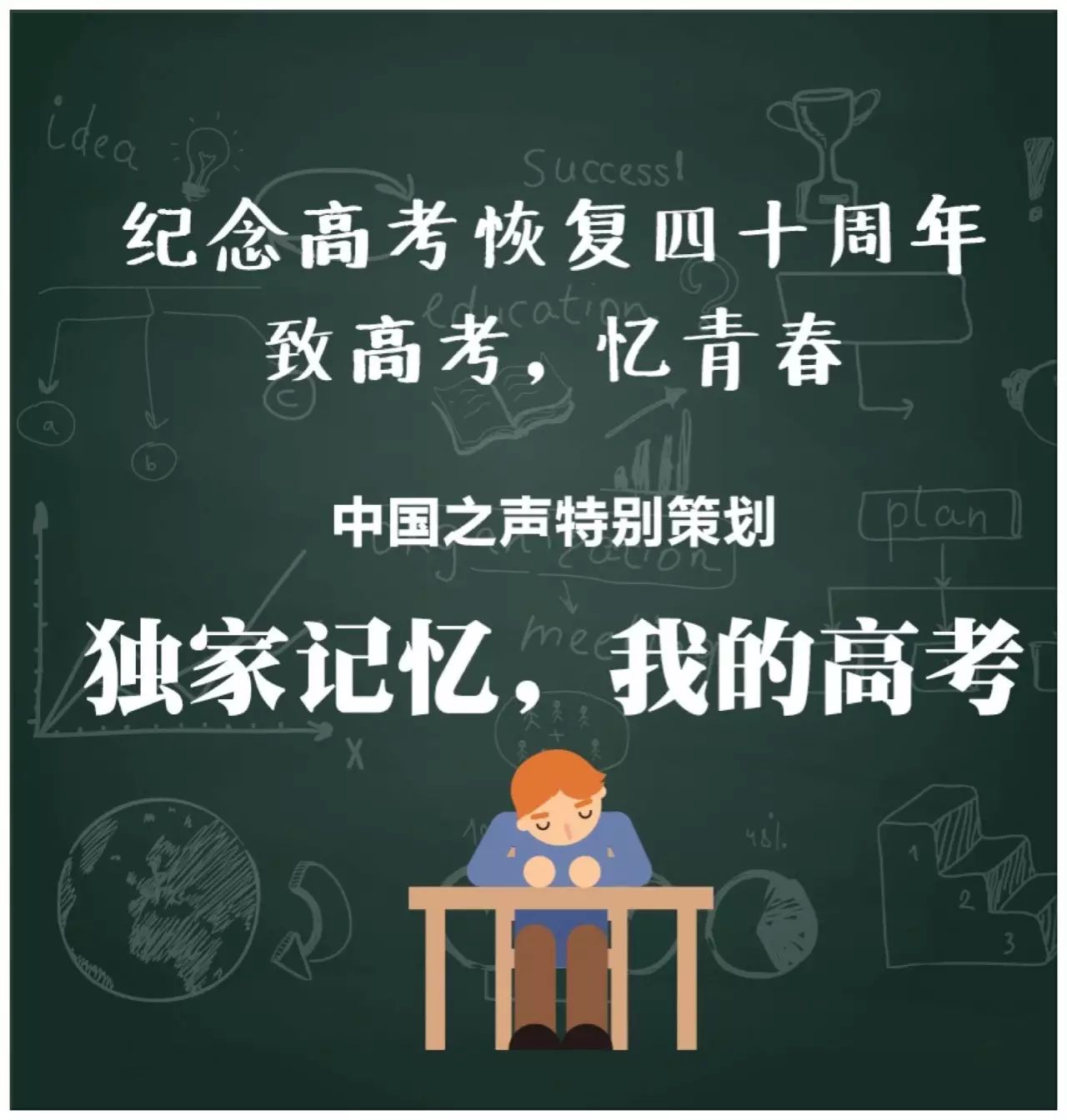
一恍,高考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这40年里发生了太多悲欢离合的高考故事,这些故事都被封存在了那属于青春的记忆里。
那时候,高考时间定在每年的7月7日-9日。正是北半球最热的季节。天气火热加上考生焦虑,影响发挥,确实不够人性化。巧合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七七事变”无人不知,影响深远。同学们进入考场,谁也不知道我们的“七七事变”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命运转折。
1984年7月9日下午,骄阳似火。

我和大家一起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如释重负。那个年代,考上学校跳出农门的确让人羡慕,考不上自己叹口气也就罢了。
走出考场,一眼就看到母亲推着自行车在门口等我,车把上蹲了一只黄猫,眼睛十分明澈地盯着神态各异的考生看。我问母亲为什么带一只猫,她说准备送人。这让我觉得母亲并不是刻意来关心儿子的高考,更像是因为要送猫,捎带来看看参加考试的儿子。
母亲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关于高考,母亲从不给我施加压力。但我知道她的期待,于是我说,今年题不难,我觉得没问题。
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才告诉我,她曾经找村里的“神人”算过,说我今年考不上,准备补习吧。这种既不科学又不吉利的预言她当然不敢告诉我,反而搞得她自己紧张了一个多月,端的是自寻烦恼。那“神人”是个目不识丁的老巫婆,经常胡言乱语吓唬人。后来听说她老伴走在路上好好的,身边的墙忽然就倒了,他就被砸死了。母亲有些不解地说,她怎么就没算出来呢?
这倒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母亲关心高考是真,送猫是捎带。可见,面对高考,哪个年代的家长都无法淡定。
7月10日,标准答案发下来。天忽然阴了,大雨如注。同学们三三俩俩地挤在教室里估算分数,不少人的脸色便也阴沉下来。
我很想冒充哲人说一句:高考面前无淡定,从来如此。

考场外的书包(图文无关)
谨以此致考生家长。
1984年,我以全县中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一举考到了位于北京的国际政治学院。我的身份从此变了,我成了非农户。1980年代,大学生还被认为是天之骄子。考上大学对我而言是个了不起的大成就,意味着我的命运被改变了。
直到现在,每每同学聚会都会拿这个第一名说事儿,说我是全县的文科状元。我当然自己知道这个状元几斤几两。当时,我们县里有三所高中,各有一个文科班,除了县中,其他两个中学师资生源都不行,考上本科的基本没有。故此,县里的文科状元只能出自我们班这几十号人。可能是运气好,那一年的考题比较对路,我就成了第一。不好意思的是,读了两年文科,我在班上从未当过第一。
报到时间临近了。母亲为我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土色的毕叽夹克,毛蓝色的直筒裤,足下是一双崭新的蓝色网鞋。母亲是村里最好的裁缝,村子里绝大多数人过年、结婚穿的中山装、西装基本上都出自她的手艺。后来电视剧《渴望》开播,母亲无师自通,学会了做慧芳服,于是,全村流行。大二的时候,一位家在京城的同学对我说,你入学的时候很中国。我不认为他是在揶揄我,权当是在夸我母亲的手艺。
因为要去三十公里在外的忻Y县(现在改叫忻Y州市了)坐火车,父亲破例使用了一回特权,把他工厂里的大卡车调来送我。那时候,父亲是县里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工资不足60元,卡车是全厂唯一的机动车,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就这样,我双手扶着栏杆,一身新装昂首站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里,任卡车行驶带来的风吹乱我的头发,神气十足,感觉就像检阅士兵的将军。
我有理由神气。我是父亲以及母亲两大家族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村里近30年来第一个考入北京的大学生。爷爷得知这个喜讯,按照封建科举制度的规则算了一笔账,认为至少也相当于中了举人。到了火车站,出示入学通知书半价买票。行李照例是要托运的,学校提前寄来的标签上印有“国政”二字。列车员十分好奇,问“国政”是什么意思?搞清楚之后不无羡慕地说,还是个国际人才。

不过,入学之后不久,学校就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1998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合并组建成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火车一夜,咣当咣当。我这只来自黄土高原某一眼井里的青蛙,游到了北京这个满眼全新的大海里。不需要河伯告诉我这里的水有多深。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跳出井台的。
后来,听了宁德厚先生的讲座,我明白了,改变命运的不是一次成功的高考,不是读大学的经历,不是一纸大学文凭,而是时代。
中央乐团的音乐家宁德厚先生曾多次应邀来我校办讲座,一段一段地讲贝多芬的《田园》、讲《命运》,有时会带来自己的同伴,组成一个小型的乐队为我们演奏世界名曲。整个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有一阵,我们的校园里甚至以听交响乐为时尚。而在1980年代中期,港台音乐才是真正的流行音乐。可惜的是,依我的出身和经历,仍然不大可能对交响乐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记得他讲“梆梆梆梆”,那是命运在敲门。
父亲曾经对我说,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还像过去那样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村里有十个指标也轮不到你。
我信。关于文革,父辈们有太多的记忆不堪回首。
1988年,大学毕业。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夏日,我把所有的行李打包在七个大小不一的纸箱里托运回家。其中,大部分是书。那是一次情绪黯然的归途,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此刻当然也是各奔东西。我知道,时代又向前走了四年时间,我的行囊中不过多了校长李子明签发的毕业证,还有学校发的派遣证,充其量算是没有被时代甩下列车。入学时的神气活现早已消耗殆尽,倒是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战战兢兢。
参加工作以后,有一次陪省外来的客人去五台山路过家乡,我对客人说,你看公路上开蹦蹦车的那些人,如果当年考不上大学,说不定其中的哪一位就是我。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五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