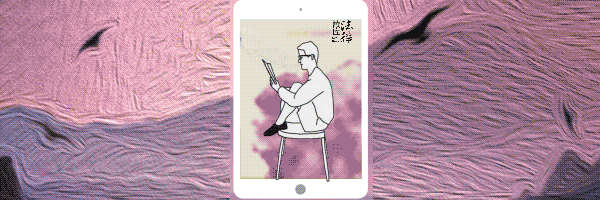
公众号平台改变了推送规则,每次阅读后,请给我的文章点一下
“在看”
。
这样,每次更新推送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订阅列表里。
作者:金懿(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以前司法考试界总流传着一则笑话,说是一些学法律的博士参加了三四次法考都考不过,但一法盲老太太粗粗学了下法律知识去考就一次性通过。有人问个中秘诀,老太太说她只是根据普通人的常识和良知蒙的答案。
当然这只是一则笑话,因为只靠常识和良知显然通不过法考。但这则笑话说明的一个道理却发人深省,
那就是普通人的常识和良知通常是符合法律解释的结果的。
法律先贤们提出过一种观点,就是人世间存在着超越制定法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所有人类世界善良、公平、正义原则的集合,如果人类的制定法违背了自然法,那么“恶法非法”,这样的法律即使制定出来也是无效的。当然,这样的认识只是类似于乌托邦一样的美好理想,现实中,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秩序,只要制定法的产生是符合法定程序的,制定法的内容不根本违背上位阶法,就必须承认
“恶法非法”
,违法者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当然,为了避免法理层面的"恶法非法",现代国家立法者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反复推敲、论证,尽量使制定法符合自然法、符合普通人的常识和良知。
但是,只要是成文法都不可避免会有一定模糊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总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即使从法理上说,有着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目的解释、系统解释、主观解释、客观解释等等解释方法,依据这些方法也难以保证法律解释结果的一致性,分歧总是会存在。张明楷教授曾提出过在法律圈深得人心的一句话,大意是人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应该心怀满满善良之心,使目光不断往返于法条和社会生活之间,从而得出正确的法律解释结果。张明楷教授其实阐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应当尽量使制定法符合自然法,司法者、执法者在解读、适用、执行制定法的时候,也应当尽量使法律被解读、适用、执行的结果符合普通人的常识和良知。
“司法为民”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的一项司法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适用、执行法律的时候应当考虑“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长期以来,一些司法人员对该原则其实并不理解,有些认为这仅是一句大而空的口号,有些甚至认为这是不讲法律讲人情、不讲法律讲政治的表现。
其实,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司法为民”、“三个效果的统一”实际上和那句张明楷教授的"心怀善良正义,使目光不断往返社会生活和法条之间,以寻找法律的正确解读"说法虽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
“司法为民”、“三个效果的统一”,其实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在解读、适用、执行法律的时候,
不能单单从法理方面进行思考来理解法律,而应当时刻提醒自己,法律解读的结果应当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一般认知,符合社会正常人的良知和常识。
当我们得出一个法律解读结果时,社会上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认同,或者当我们运用证据规则认定了一些案件事实,社会上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认同,那一定不是老百姓不懂法,而一定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解读、证据推导和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出了错。
司法人员当然应该掌握法理,更应该精通法理,但必须时刻切记再高深的法理或是再完善的证据推导,都不可能是违背大部分人的常识和良知的。
如果两者相悖了,那么改的绝不应该是大部分老百姓的常识和良知,改的应该是我们的法学理论,或者改的是我们解读法律、证据推导的方法和路径。为什么一些热点案件的处理结果被媒体报道后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轩然大波,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原因恐怕就是司法结果违背了大部分老百姓的常识、违背了社会一般人的良知。
本文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所以也没有引注他人的研究成果。以下将提到一些作者在日常工作学习时遇到的有分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并没有形成通说结论,作者的思考也许存在谬误之处,故问题的提出仅供读者探讨。
刑法上的
“轮奸”
是强奸罪的加重情节,二人以上轮奸的,应当直接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
笔者曾道听途说了这么个案件,被害人某丙(女性)与某甲、某乙(均为男性)共同吃烧烤,后在吃烧烤过程中丙喝醉。后当晚甲、乙二人带醉酒的丙去某宾馆过夜,当时开了两间房间,甲丙一间、乙一间。甲在房间中趁被害人丙严重醉酒无法反抗之机违背丙的意志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从监控录像上看,期间乙多次到甲的房间敲门、扒门、并贴耳在门上听门内声音。在乙反复多次敲门后,甲打开了房门,丙浑身赤裸裹着被子从房间内踉跄逃出(监控中看到途中丙的被子曾掉落在地上过),乙在目睹上述情况后仍将丙推入自己的房间,甲在看到乙把丙推入乙的房间时并未阻止,之后甲就关上自己的房门睡觉了,乙在其房间中又强行与丙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后,通过相关证据已能确认甲、乙分别在违背丙的意愿情况下强行与丙发生性关系的事实,二人均已构成强奸罪。某检察机关认为甲、乙的行为不但构成强奸罪,还具有轮奸妇女的加重情节,向某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甲、乙不具有轮奸情节,理由主要有三:一是没有证据证明甲、乙事前具有轮奸丙的通谋,二是没有证据证明甲当时在打开房门后在过道中曾教唆、指使、授意乙继续奸淫丙,三是没有证据证明甲乙互相知道对方奸淫了丙,因此认为本案强奸的证据充分、轮奸的证据不充分,故而未判处二人轮奸情节,只按照强奸罪的基本条款进行了判处(案例一)。
关于轮奸,笔者还曾看到某司法考试机构辅导用书中写到"甲将丙女打昏后实施了奸淫行为,随后让没有参加前行为的乙强奸了昏迷的丙女,无论乙是否知道甲已经强奸丙女,乙对甲之前的强奸行为都不负责任,乙仅承担普通强奸的责任,但甲应对乙的强奸行为承担共同正犯的责任,对甲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对乙不适用轮奸的法定刑" (案例二)。
笔者明白,之所以上述问题会引起分歧,主要是学理上对于"轮奸的共同故意是否必须产生于第一次奸淫行为之前还是也可以产生于第二次奸淫行为之前"、"轮奸的共同故意是否必须表现为犯意有互相交流还是只需要互相明知奸淫行为且互相不阻止即可"、"承继的共犯中,后加入者是否一概对之前他人的行为不用负责"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导致。抛开上述学理分歧不谈,笔者认为就上述所举的两个涉及是否轮奸的案例,马路上找一些不懂法的老百姓来谈论应该都会得出甲乙肯定具有轮奸的加重情节,在这两个举例中如认为甲乙不构成轮奸,明显违背了普通人的常识与良知。因为对于妇女丙来说,无论甲乙是事前共谋还是事中共谋、无论甲乙之间是否在宾馆走廊里交流过"我完事了,你继续吧"这句话还是双方对于彼此奸淫丙的事情心照不宣各自进行,对于妇女丙受到的奸淫伤害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甲乙轮流奸淫妇女的恶性也没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还要人为限定轮奸的故意必须发生于第一次奸淫之前、轮奸的故意必须互相有明确的犯意交流这些限制呢?这样解读法律不是明显违反老百姓的常识和良知吗?
可能有些思路清奇的观点会提出,甲又没有授意乙继续奸淫丙,因此让甲承担丙被乙奸淫的结果从而构成轮奸不是对甲很冤枉吗?甲构成轮奸他冤枉吗?
笔者认为大部分老百姓显然不会觉得他冤枉。符合良知和常识的解读思路应该是怎样的?因为甲乙共同主动在深夜把醉酒的丙带到宾馆,甲乙二人的先行行为本来就使得甲负有法律上照顾好丙的义务,此外,因为甲不但没照顾好丙反而强奸了丙,甲的犯罪行为使丙落入了更不利的境地(深夜醉酒还赤身裸体)这就更加创设了甲应保护丙不再遭受他人继续侵害的义务,甲明知乙想要继续奸淫丙,在有双重作为义务的前提下,有义务阻止而不阻止,甚至默认或纵容乙继续奸淫丙,因此甲的不作为行为构成了乙强奸罪的共犯。对于乙而言,虽然乙事中加入前甲奸淫丙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的既遂,乙的确不应该对甲已经既遂的强奸结果承担责任
。但由于乙尚未开始奸淫,轮奸的加重情节尚未发生,乙明知自己继续实施奸淫会导致妇女被他人轮流奸淫的后果,
仍一意孤行,那么乙就应该对由于自己行为导致的轮奸加重情节承担责任。
至于案例一中某法院的第三点理由,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甲乙互相知道对方奸淫了丙,笔者认为这样的证据推导事实同样也是明显违背一般人的认知的。因为刑法中的明知包括"确实知道"和"应当知道",作为一个正常成年人,乙都在门口猴急的敲门、扒门、偷听了好久,之后也看到了丙赤身裸体只裹着一条被子逃出房间的情况,难道乙不应当知道甲很可能奸淫过了丙?甲在自己实施奸淫的时候,乙反复过来敲门,甲心中一定很恼怒吧,后甲自己完事了看到乙猴急地把赤身裸体的丙推入乙的房间且也不报警不呼救的时候,难道甲会认为乙是要去好心的安慰丙而不是继续奸淫丙吗?这样通过证据推导出甲乙不明知对方奸淫了丙的事实到底是属于"合理怀疑"的范畴还是属于违背良知和常识的证据推导?
至于案例二中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编写者之所以会得出乙明知甲强奸了丙,事中加入还不构成轮奸的结论,恐怕是因为编写者认为根据承继共犯理论,后加入者对于之前他人既已实施的行为一概不负责任,所以推导出乙无法构成轮奸。但真的是这样的吗?笔者来举另一个例子,恐怕读者就明白了。某甲想要用毒药毒杀丙,根据毒药用量两包毒药才能毒死丙,而一包毒药只能产生轻伤的后果。甲已经对丙下了一包毒药,但因为客观原因甲无法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故甲事中告知了朋友乙实情,甲请乙帮忙对丙下另一包毒药以毒死丙,后乙照办,丙成果被甲乙二人毒死(案例三)。如果认为承继的共犯中,后加入者对之前他人行为概不负责,那么案例三中的乙要么只能对一包毒药致他人轻伤负责,要么只能对丙死亡的半条命负责,总之没有办法对丙死亡的一条命负责。但这样的法律解读应该是会被不懂法的老百姓笑掉大牙的,如果司法实践中果真如此操作,那么引起轩然大波的负面效应该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所以笔者认为,承继的共犯中后加入者对之前他人既已实施的行为不负责是有限定的,应该是后加入者不对之前他人既已实施的加重结果负责,而对于基本犯的事实是必须要负责的。比如某甲实施暴力对某丙进行抢劫,造成了丙的重伤结果。这时甲的朋友乙正巧路过现场,乙事中加入协助甲从已经重伤的丙处劫取财物的,乙作为承继的共犯不对丙重伤结果负责,乙不具有抢劫致人重伤的加重情节(案例四)。又比如某甲对某丙实施非法拘禁,而法律规定非法拘禁一般要达到24个小时才构成犯罪,甲已经拘禁丙12个小时,事中邀请乙过来协助继续共同拘禁了丙剩下的12个小时(案例五)。该案例中就必须认为,尽管乙是事中加入的,但乙必须要对甲已经拘禁丙12个小时的事实同样负责,此处的逻辑是与案例三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问题。刑法规定非法拘禁他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根据刑法的规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是结果加重犯,而且是十分严重的结果加重犯,需要直接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笔者了解到了两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案例,认为可提出供探讨:
某乙因为误入某传销组织,想要离开不被许可,而被某甲等人非法拘禁于一小区楼的402室出租房内。乙当晚借上卫生间之机欲通过爬窗户至窗户外排雨管的方法逃离传销组织,但因爬窗不慎从四楼坠落而致颅脑损伤死亡。甲后被某法院判处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案例六)。某乙因为欠某甲债务,为追索债务,甲采用非法拘禁的方式向乙索债。期间,乙逃跑后被甲发现后抓回,甲因气愤用正好放在屋内的棒球棍敲击了乙的腹部一下。后甲看乙被打后确实很疼,怕把事情闹大而在将乙捆绑后放置在轿车后排并驾车前往表哥的小诊所想要给乙治疗,车辆正常行驶过程中,不料遭遇了疲劳驾驶的某丙的追尾撞击,后乙当场在车内因车祸事故死亡。经法医鉴定,乙腹部被棒球棍击打造成脾脏破裂构成重伤,乙因车祸导致颅脑严重损伤而直接致死。经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丙因具有疲劳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在交通事故中负全责,甲没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故不负交通事故责任。后甲被某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非法拘禁罪(致人死亡)两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例七)。
这两个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案例,前一个是互联网上搜寻到的真实判例,对于该判决结果笔者比较认同;后一个是某省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中虚构的案例及答案,对于该认定结果笔者实难认同,并且十分希望该案例仅是一个虚构的案例,否则某甲真的有点冤。
案例六中,甲的辩护人曾提出甲等人虽然非法限制了乙的人身自由,但乙爬窗逃跑时其人身自由已脱离了甲的非法拘禁行为的控制力,乙死亡是因为介入了其爬窗坠楼的这一行为,因果关系已被中断,故乙的死亡与甲非法拘禁没有因果关系,故甲不应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某法院审理后未采纳该辩护意见,依旧认定了甲构成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判处了甲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学理上一般认为是非法拘禁的行为直接地、过失地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采用非法拘禁范围外的其他暴力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根据法律规定应直接认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常见的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情况,包括非法拘禁因捆绑过紧而过失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长期非法拘禁过程中因疏忽忘记给被害人食物而使被害人饥饿死亡等。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与其他的犯罪行为致人死亡一样,一般都要求该犯罪行为直接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如某甲强奸了妇女某乙,后乙抑郁非常竟跳楼自杀身亡(案例八),在该案例中就不得认定甲存在强奸妇女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因为强奸致被害人死亡应理解为强奸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包括妇女被强奸后因抑郁跳楼死亡的情况,但案例八可考虑强奸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加重情节。如此说来,为何笔者赞同案例六的判决结果呢?因为案例六中,
一是
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虽然介入了被害人乙爬窗逃跑的这一情况,但考虑到甲等人将乙非法拘禁于四层楼的位置,乙为了逃跑高概率可能会选择翻窗逃跑的方法,被害人翻窗逃跑在一般社会认知上并不属于异常介入因素,因此不能中断非法拘禁行为与坠楼死亡后果的因果关系,两者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或者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甲将乙非法拘禁于四层楼位置的行为,社会大部分人会认为就已经创设了乙可能在翻窗逃跑中坠楼死亡的具体风险,最后乙因爬窗逃跑坠楼死亡,该死亡结果可归责于甲的非法拘禁行为。
二是
甲将乙非法拘禁在四层楼的位置,应当预见到乙可能会采取翻窗逃跑的方法,所以甲具有刑法上的预见可能性,因此其主观上存在过失,可对致人死亡的后果担责。故案例六中,虽然介入了被害人逃跑的这一情节,但也可认为属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加重情形。而在案例八中,即便牵强的认为甲奸淫妇女乙后,有预见妇女自杀的可能性,但在现今相对古代性开放的社会一般认知来看,妇女被奸淫后会主动选择自杀应属于极小概率事件,从相当因果关系来说,妇女自杀这一被害人自身的异常行为足以阻断甲奸淫行为和乙死亡的因果关系,因为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不能认定甲强奸致妇女死亡的加重结果。或者从客观规则理论来看,社会一般人的认知并不会认为甲强奸乙可以引起乙自杀的具体风险,故乙自杀的后果不能归责于甲的奸淫行为。
在笔者看来,案例七实质上和案例八的情况是类似的,或者说是更加不能认定为致人死亡的情况。案例七不能认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是
甲显然无法预料到正常行驶中会遭遇因他人疲劳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导致的车祸追尾事故。因为在社会大部分人的常识来看,正常驾驶车辆因他人的违法行为造成追尾严重交通事故是一项极小概率事件,社会中有很多人正常驾驶车辆一辈子都不曾遭遇他人违法追尾的严重事故,甲又怎能事先预料到送医救治过程中就那么巧被他人违法追尾而致乙死亡呢?这种概率其实和甲把乙非法拘禁过程中发生地震,乙被地震震死一样几乎是无法预见的,即便车祸的几率比地震大一些,但也不足以构成甲有预见可能性的理由。
二是
由于在社会大部分人的常识来看,正常驾驶车辆因他人的违法行为造成追尾严重交通事故是一项极小概率事件,是一种相当异常的情况,故足以中断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后果的因果关系。或者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社会一般认知并不会认为将被害人非法拘禁于车内正常行驶,会引起被害人因被他人疲劳驾驶追尾导致颅脑损伤的具体风险,故乙死亡的后果不得归责于甲的非法拘禁行为。
遗憾的是,案例七的参考答案认为,乙死亡系由于甲的非法拘禁行为加上他人的违法疲劳驾驶追尾两个原因共同造成的,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况,且乙客观上死于甲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因此甲属于非法拘禁他人死亡的情况。笔者认为,参考答案是误把刑法上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当成了"原因"。杀人犯的母亲把杀人犯生下来,是创造了杀人犯杀人的"条件",但显然不可能成为被害人被杀人犯杀死的"原因"。幸运的是,该案例应该只是个杜撰的模拟案例,希望实务中不存在如此倒霉的被错误起诉为十年以上加重情节的真实的甲。
诈骗和盗窃均属于刑法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类犯罪,二者都属于侵犯财产占有型的犯罪,前者属于被害人主动型犯罪,后者属于被害人被动型犯罪。刑法中很多罪名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很多罪名都可以存在想象竞合的情况,比如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就可能出现想象竞合——行为人完全可能虚构了一个来自于自身的恶害,后把恶害向被害人发出,被害人接受虚假恶害后被欺骗而陷入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而产生恐惧,进而向行为人交付财物导致经济损失的情况,这既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从一重罪论处一般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但由于诈骗罪和盗窃罪中,前者是被害人主动型的犯罪,后者是被害人被动型的犯罪,如果说有一天出现了被害人既主动地被侵害、又被动地被侵害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将会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所以诈骗罪和盗窃罪永远也不会出现想象竞合的情况,他们就是冰与火的关系——永不相容。虽然从法理上两罪名是这种关系,但实践中两罪名却经常产生让人"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