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TITUTE|批评·家
|
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
文|
黄清怡
/
责编|yy

本文主要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俄罗斯的先锋派电影,在欧洲的社会思潮和先锋艺术运动的语境中,梳理电影创作者对于蒙太奇手法和电影媒介的探索和实验,并考察创作者关于电影蒙太奇的理想和观念,最后借助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视角,反思电影和蒙太奇的可能性
。
本期推送的内容为论文的第一章第一节,
论述苏俄社会与文化的总体历史面貌,逐步对焦至俄罗斯先锋电影的发展状况。开篇第一节,
作者尝试借用蒙太奇理念将庞杂历史有线索地书写成“电影式”的历史景象,在意图明确而非泛泛的论述中,“先抛出一个俄国罗斯先锋派电影超越于个别图像的整体意象,再仔细地去拆解、分析它的样貌”。
近两百年间,彼得大帝改革加剧了知识阶层与平民的隔阂;拿破仑战争激发起民族热情与大国意识,那些被鼓励前往“崇高体面”的专制德国的俄国青年最终成为俄国独裁体制的拥趸。夹杂在社会诸矛盾中的知识阶层受到浪漫主义学说及其哲学体系的影响,他们强调“特定人群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使命”,希冀用一套完整体系疏通积弊,解决眼前社会的多重问题。
1870、80
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随即与浪漫主义学说嫁接成一种“集体性超越个别性”的独特信念。鲍里斯·格罗伊斯尝试将俄国先锋派的基本精神概括为“要求艺术从表现世界转为改变世界”,电影领域的实验自然并不例外。如何理解这一总括?
此篇论文的作者提出,我们在俄国先锋派电影实验中看到的是“一种新世界观的可能性,这种新的世界观也在根本上为‘何谓改变世界’做出了一种解释,简言之,改变寓于表现和解释,‘表现’与‘改变’、‘解释’与‘改变’,并不是相对的,甚至不是一前一后的两个阶段,而是作为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互相交织在一起”。

尼古拉·切尔卡索夫、谢尔盖·爱森斯坦和爱德华·蒂斯在《伊凡雷帝》片场
|1945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与蒙太奇理论|2020

第一章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
第一节 苏俄文化概略
开篇讲苏俄文化, 并不是为了给出一个“背景”,好像要论俄罗斯电影,必须先了解它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然后再去理解它的形式和内容为何如此——“电影”所鼓励的方式恰恰相反,这种作品有自己的时间性,指向一种直接的综合感觉。而作为艺术手法的蒙太奇,首先就是要打破叙事的连续性模式,以达到更加真切的体验。因此这里的苏俄文化概略,其实是借用了蒙太奇的理念,期望可以用“电影式”的历史,先抛出一个俄国罗斯先锋派电影超越于个别图像的整体意象,后文再仔细地去拆解、分析它的样貌。
首先,这一节把论题中的国家称为“苏俄”,因为这里讲的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俄罗斯帝国,而是从俄罗斯帝国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剧变。正当这场剧变,俄罗斯先锋派电影实验激烈地展开着,而这些艺术实验,正是与俄国革命同处于一个积蓄了近百年力量的文化势头中。
十八世纪起的俄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受过教育的阶层与“愚暗”的人民之间有着巨大的分裂,这起因于改革心切的彼得大帝选派青年前往西欧学习艺术与技术的做法,而这些艺术与技术,是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产物。回国后,那些带着欧洲现代思想和技术的人,就承担起了建构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但是,这读了许多德国书、法国书的一小撮人,面对的是甚至不知道本国语言如何书写的广大人民,他们所懂得的道理,难以顺利地加于人民身上,便不得不使用强权,逐渐地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1]
十九世纪早期的拿破仑战争则让俄国有了民族意识和大国意识,引发了激烈的爱国热忱,随之而来的是全民参与一个共同理想的感觉,一些理想主义的青年开始感到自己与国家之间有着切身的关联。[2]

[1]
以赛亚·伯林详细描述了这种社会割裂的成因:“彼得变革心切,选派青年前往西方世界,待其习成西方语言,以及发源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各种新艺术与新技术,即召回国,任为新社会秩序的领袖。这样,他往他的封建国土上强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又因求功孔急,用事遂无情而强横。如此,他造成一个小小的新人阶级,这些新人都是半个俄国人、半个外国人——即使出身为俄人,也是在海外受教育;不久,这些人化作数目极少、以管理为职掌、以官僚为结构的寡头政治,站在人民头上,不复分享人民仍然属于中世纪的文化,而且终至与人民两相断绝,无可挽回。”(
[英]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怀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第142页。)
[2]
体制上,社会割裂的情况没有改变,但是俄国人的国家自我意识改变了:“拿破仑入侵,将俄国带进欧洲,情势不变。几乎一夜之间,俄国发觉自己是欧洲核心强权,意识到自己是锐不可当的力量,支配全局并且为欧洲人所接受。……在俄国观念史上,战胜拿破仑、进军巴黎,与彼得改革是同等攸关重大的要事。经此二事,俄国知觉到她的民族统一,意识到自己是欧洲大国,而且已获承认为欧洲大国,不再是中国长城外面一群生口众多、久遭鄙视、沉陷在中古黑暗里、半带热心而笨拙模仿外国范例的乌合蛮人。此外,长期的拿破仑战争引发重大而持久的爱国热忱,全民参与一个共同理想,阶级平等的感觉随之增加,一群比
较理想主义的青年于是开始感到自己与国家有新的连属相系之处。”(
[英]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怀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第143页。)

《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
谢尔盖·爱森斯坦|
1925


而西欧涌动着的社会变革暗潮,则对俄国人的感受和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俄国政府已不愿臣民前往充满革命和动乱的法国学习,而鼓励青年前往安分地保持着专制制度的德国,以便得到公民守则方面的训练。[3]不料德国人本身已受法国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在观念上甚至比法国人更加狂热,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的青年。[4]
夹于死气不化的政府和饱受压迫的农民之间的俄国知识阶层,在这当口热切地带回了德国的浪漫主义和体系哲学,强调特定的人群具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使命。[6]他们知道俄国社会的问题很多、很重,并相信有一种体系能对所有互相关联着的问题给予根本上的解决,因此所有的道德和教育都应从这个体系出发,而在这体系中,为了唯一的真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使命。这样的文化氛围是适宜马克思主义生长的土壤,当马克思的思想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传入俄国,它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在二十世纪初的剧烈震荡中势头高涨,延续着俄罗斯文化阶层对于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达到了自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的古典时代以来的一个巅峰。俄国的经典先锋派艺术无法单单用一个公式去概括,但如果要把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出现的各种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艺术实验统称为“先锋派”,并为它加上一些描述,那么可以说,它要求艺术“从表现世界转为改变世界”。[7]俄罗斯的先锋派电影制作者,也散发着前文所说的那种浪漫信念,无论是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还是爱森斯坦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他们都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以靠近这个理想为目的,进行着自己独特的工作和使命。当然,这时的先锋派艺术,包括文学和绘画等等,都透露出了一些新哲学的影子,比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等等。而在电影领域,似乎更明显地流动着二十世纪的思想与生存方式。在俄罗斯的先锋派电影实验中,我们看到一种新世界观的可能性,这种新的世界观也在根本上为“何谓改变世界”做出了一种解释,简言之,改变寓于表现和解释,“表现”与“改变”、“解释”与“改变”,并不是相对的,甚至不是一前一后的两个阶段,而是作为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样说恐怕过于简略或抽象了,但在电影及超出“电影”的蒙太奇中,我们却可以无比具体、无比切身地领会到这点。

[3]当局眼中法国和德国所代表的政治性格参见伯林的描述:“法国,尤其一八三〇年以后,被视为革命已成长期痼疾,终岁苦于剧变、流血、暴力、混乱之国。两相对比,德国在一个非常高尚体面的专制制度脚下雌伏平治。因此,俄国政府鼓励青年前往德国大学,学取公民守则方面的完善训练;当局认为,他们学成之后,会成为俄国独裁体制更忠实的仆人。”([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怀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第144页。)
[4]这种狂热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独裁的俄国政府来说实在是危险的:“是时也,德国本身内部,亲法情绪安涛汹涌。经过启蒙的德国人信起观念来——法国启蒙运动的观念——竟比法国人本身犹更强烈且狂热,俄国这班遵命前往德国的年轻安纳卡西斯们于是染上危险的观念,习染之深剧,他们若在路易·菲利普当政最初那几个逍遥年头里求学巴黎,也会远远不及。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实难逆料自己命定如此阴沟翻船。”([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怀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第144-145页。)
[5]“毫无疑问,浪漫主义的学说对俄国这种普遍的态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那些浪漫主义学说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统治者欧洲文学和报章杂志,在德国尤为盛行,强调特殊的人群——如德国人或工业家或诗人——具有独特的历史使命。”([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124页。)
[6]在这种信念中,集体性超越了个别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也有一些例外)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是为关注个别的或个人的目的,比如说为自己追求知识、艺术创作、追求幸福或个人自由而放弃对这种理论体系的求索,则被看成是主观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人的责任的不道德行为。”([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125页。)
[7]“从表现世界转为改变世界”是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表述:“在俄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经典先锋派艺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无法单单用一个公式去涵盖;但是把它的基本精神定义为要求艺术从表现世界转为改变世界,也不能说是过度简化。”这一表述暗合了马克思口中“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这两种思想的特征。

《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
谢尔盖·爱森斯坦|
1925


▶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2020年硕士毕业论文《俄罗斯先锋派电影与蒙太奇理论》
论文指导|
周诗岩
未完待续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1
第一章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5
第一节 苏俄文化概略/5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7
第三节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的发展/11
第二章 蒙太奇理想/14
第一节 对于形式的探索/14
(一)蒙太奇作为新闻形式/14
(二)蒙太奇作为艺术形式/17
(三)形式的意义/20
第二节 电影与社会/22
(一)何为真实: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22
(二)何为现实:爱森斯坦的“一切为了人”/24
(三)艺术的界限/25
第三节 电影的可能性/27
(一)传播的视角:维尔托夫与电影眼睛/27
(二)感知的视角:爱森斯坦与声画蒙太奇/29
(三)联结与结构/30
第三章 再论蒙太奇/33
第一节 集体性与解放/33
第二节 经验与现实/35
第三节 美学与政治/37
结语/41
参考文献/42
致谢/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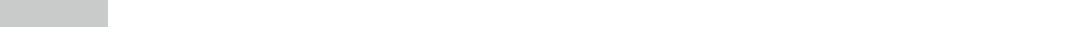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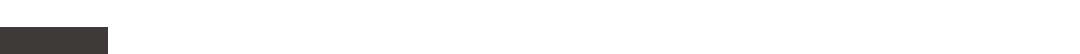
苏联电影的诞生
本文作者什克洛夫斯基,作为苏联电影从萌芽到初绽的实际参与和见证者,切实记录下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如何从零开始,凭借真挚、天真与勇敢,将生命的热情诉诸新型的电影事业: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列昂尼多夫...在暴风骤雨的革命前线,这些青年人伴着苏联电影崭露头角,传递着革命的热血,也传达着春天的微笑。那是闪烁着奇迹光芒的年代,也是脚踏实地、幸福奔走的日子,他们所有人——普多夫金、演员鲍·里凡诺夫、摄影师阿·戈洛夫尼亚、美工师乌特金、导演米·道拉尔——坐在桌子周围,为电影争论,把自己想的东西直接告诉对方,只说最重要的东西;努力让自己的艺术修养符合这个时代。然后来到街上,迎接那个时代的、还非常寂静的、楼房层数不多的莫斯科。
那是一段天真的岁月。但却是各种伟大发明频出的年代。我们都在等待着,第二天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
苏联电影诞生的时代——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我们这群人仿佛是他们所需要的那批人。我们仿佛和他们同一个时代,而同时又像是一群未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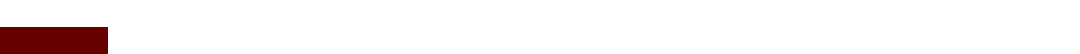
▶
合集
|
2017/18 - 2021/23
院外
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
BAU学社
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
星丛共通体
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