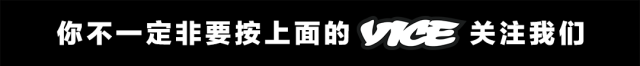
作为一个年轻的傻小子,我恐怕只能接受在电影和小说的虚拟世界里审视生死和善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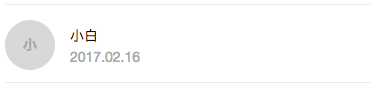
我爸妈从上大学前就教育我,“你好好学法律,将来能从政或者当个律师多棒。” 就这样,我误打误撞地学了法学专业。不过几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决定远离这一行。
大四前,我和身边几个哥们被老师分派去了湖北某地的司法机关进行毕业实习,我去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那段时间课不多,我基本都在看演出、喝酒或者打游戏,突然被拽到部级司法机关上班,有点懵逼 —— 何况前一年我刚刚因为酒后闹事进了派出所。
第一天去法院报到,流程就是安检、登记、熟悉工作。法院有两栋气派的大楼,还有花园、车队和体育场,法官下班后喜欢打打羽毛球。我去了刑事审判第一庭,办公室跟正常公司差不多,大家趴在电脑前各干各的活,但是没有
Wi-Fi,电脑也不能用外部设备。大家等级明确,每个部门都有门禁。
 Photo by author
Photo by author
开始的工作是每天给庭长送文件,报纸文件要按他的喜好顺序排好。因为是年底,还要写一整年的每周党员作风建设会议记录,包括每个法官的发言和感想总结 —— 这个就比较头疼,因为他们没开过几次会。
好玩儿点的工作是整理卷宗,高院的卷宗比大部分国产电影有看头,故事够狠够劲,没有漏洞百出的剧情和无聊透顶的恋爱故事。内容大多是涉及贪污、毒品、杀人、强奸的事儿,其中贪污和毒品案件占了一大半。有
“大老虎” 贪污案的机密文件,也有个别的邪教、间谍和颠覆国家的案件。毒品案件最精彩,当地的本土 “绝命毒师”
敢想敢干,个个都是亡命之徒,而他们绝大多数的下场都是死路一条。
当时整理的一个案子让我印象很深:黄某、丁某和胡某哥仨靠倒卖毒品谋生,但老黄立志要当大毒枭,“没有毒源,永远都是中间商,我要
‘升级’ 成顶级毒贩。”
于是他们在家小区的楼顶盖了100平米的空中实验室,还安装了电梯运货。邻居夸他们安电梯是热心做好事,给邻里提供方便;可能老黄想做像巴勃罗·埃斯科巴一样的被人民热爱的毒枭吧。
 老黄在小区楼顶的实验室。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老黄在小区楼顶的实验室。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三个人每天在实验室里戴着防毒面具研究制冰毒,一开始从感冒药中提炼,但这个方法太笨,他们就升级从广东进合法甲基原料,实验提取含甲基苯丙胺液体,凝固后得到冰毒。他们花费成本50万元,不断实验,最后终于成功,提炼出了纯度30%的冰毒,一共100多公斤。第一批卖出了1000千多万,三个人暴富之后先买豪华公寓,再买奔驰宝马,老黄还特爱给自己的爱车改色。
 警方展示查获的实验设备 。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警方展示查获的实验设备 。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但是老黄没有像老白或巴勃罗一样成为传奇
——
没到一年,他们挣得钱还没花完,就被逮了。查获过程很简单,他们家附近有个武警基地,武警下班时闻到异味去看了一眼,发现了他们的工作室。后来被特警包围的时候,哥仨正在里面跟小弟打麻将,麻将桌旁还有枪和400公斤含冰毒的液体半成品。老黄和他兄弟最后被判了死刑,不久前刚刚被处决。
像老黄一样的
“毒师” 不止一个,冰毒相对制作简单、成本低,很多法外之徒想借此发财。制冰毒的教程可以在网络上花几千元买到,制作一颗 “麻果”
的成本仅几元,售价则是约50元。也有高端的产品,当地曾有几个大学教授前赴后继在实验室带着学生制毒,研发的 “浴盐”(类苯丙胺物)销往欧美。
但进一步参与到案件执行中后,我再也没法轻松地转述这些故事了。
第一次具体的执行工作,是陪法官出差去山区里的县城给杀人犯宣判死刑。法官平时的样子木讷不起眼,到了小县城也变样成了领导,包里装着厚厚的几沓钞票。县法院领导给我们接风,住在当地最好的酒店。
第二天我们去看守所宣判死刑。几道大门进去,我们在狱警的陪同下见到了死囚,在一间几平米的审讯室里,宣读了死刑判决书。犯人是患乙肝的养猪工人,老婆长期出轨,他想离婚但老婆一家人不同意并再三侮辱他,他一怒之下砍死了老婆,然后自杀未遂只砍伤了的脖子,只能向警方自首。判决书不长,宣读完后,法官、狱警点上烟和犯人聊了两句,问了下他的遗愿。他说一心求死,但放心不下自己失去父母的小女儿,希望有机构照顾她。法官点点头,十几分钟的宣判就结束了。
我第一次见到的死囚不是预想中戾气逼人的罪犯脸,他年龄不大却异常苍老,有点像我常去买烟的小卖部的老头。身上裹着蓝色的囚服,手脚都链着黑色镣铐,一动就会哗啦啦地响。他自杀时砍伤了声带,所以没费力多说什么申辩的话,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 但我知道他不是没有求生欲,他上诉过,结果是还是死刑。
我当时很想跟他说对不起,因为第一次见面,就带来了他的死讯做为见面礼。但我是做在本职工作,他人命在身,死刑的判决经过了二审和复核,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种纠结的愧疚,让我出门时差点吐在看守所高墙边。法官安慰我说:“来这儿宣判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要尊重人权生命,体现法律的人道”,可我并没有感觉好一点。
我说不准这个犯人是不是该死。很多人坚信杀人偿命,死刑存废饱受争议,他的故事也不会博得什么同情;但作为杀死这名犯人的众多参与者之一,我的感受只有愧疚和恐惧 —— 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这种剥夺生命的行为和权力。
第二天回去上班,法官没再提起这件事儿,这次出差可能也只是算他繁忙案头工作中的小插曲。我慢慢也记不清死囚的样貌和声音,只记得他身上的蓝色囚服和脚镣摩擦地面的哗啦声。如果他尚在人世,希望他也别记起我。
之后一个月,所有人都在为我们承办的全国毒品工作会议忙碌,准备接待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法院领导,我负责为领导们联系专车和酒店。开了三天会后,领导们说毒品犯罪形势恶化,要从严审判。
干完这个活儿,就是假期,实习工作结束了。放假前,
我和一起分配到司法机关实习的几个朋友聊天,在高院民事审判庭的哥们说他目睹身边的法官被设计送进了监狱,在检察院的哥们经手了本校大一女生组织同学卖淫的案件……大家一致觉得,上个班要遇到这么多烂事儿,简直是每天和自己的良心作对,本来还以为我们早都生活在文明社会了呢。最终,我和他们一样,毕业后没有一人从事法律行业。
实习结束后没多久,我发现自己得了情感障碍,一部分的病因正是这段压抑的经历。作为一个年轻的傻小子,我能接受在电影和小说的虚拟世界里审视生死和善恶;但合法地杀死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是我参与过最操蛋的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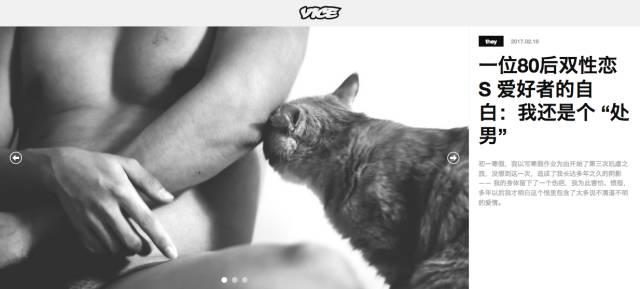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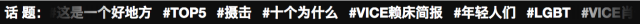

点击 阅读原文 回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