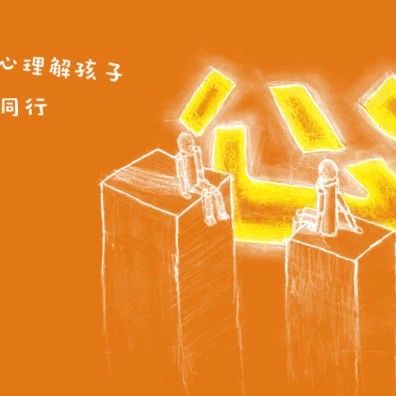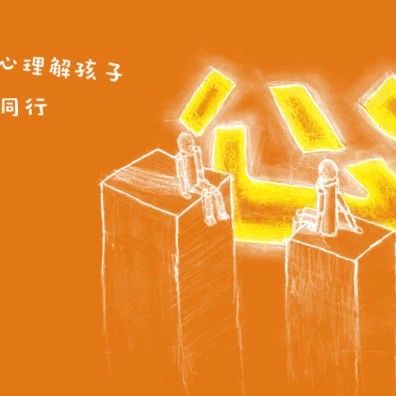正文

美国学者Gilligan在《不同的语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的发展》中写道一段访谈内容:
有一位大学女生在被问到「如果要妳说道德对妳而言有什么意思,妳会怎么说? 」回答道:
在我想到道德这个字的时候,我想到责任/义务。
我通常会把它想成是在个人欲求和社会事务、社会考虑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妳个人的需要与另外一个人的需要或者人们的需要的对立。
道德是妳如何决定(解决)这些冲突的整个领域。一位道德人是个在许多时候与他人平起平坐的人。一位真正有道德感的人总是会平等的对待另一个人……
在一个社会互动的情境里若有一个人把别人弄得鸡犬不宁,那么这就是道德上错误。若每个人都变成更好,那就是道德上正确了。
但当问到她是否能想到一个真正道德的人时,她回答:
嗯, 我现在能想到的是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因为他很明显的助人到牺牲自己性命的地步。义务和牺牲超越了平等的理想,在她的思想中设定了一个基础的矛盾。
我想到平常搭乘台北大众运输工具的经验,走进地铁或公交车车厢,你会看到特别标示着不同颜色的「博爱座」,而经常站着的旅客人数高过空无一人使用的博爱座数量。
设置博爱座利益良善,但一个真正良序,有道德的社会,就算车厢内没有特别标示博爱座,民众也会自动让座,这才合乎道德人的表现。
相反地,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种「道德的被害妄想症」。好似一旦坐了博爱座,就得接受道德谴责。
这真是一个吊诡的问题,博爱座要礼让老弱妇孺使用,英文也加上 “priority”(优先)字样,即当遇到老弱妇孺等有需要的乘客,当让他们优先使用。但到了台湾,「优先」顿时成了「必须」,而且这个必须彷佛是康德口中严谨的道德律令。
试问台湾民众真的因为「热爱」礼让博爱座而显得道德特别高尚吗?
与此同时我们在马路上,还是经常见到驾驶(包括公交车司机)跟行人抢道(尤其是右转车碰上直行行人)。
若我们回到Gilligan的访谈中,以访谈对象的道德标准来看待道德妄想症,我们应该要问:「社会是否因为礼让博爱座而让每个人变得更好?」
乍看之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实际上,若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礼让」的意义,不是积极的认为「我们礼让是对的」,而是消极的认为「不礼让我怕被人投以责怪的眼光」。
那么礼让本身第一个就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陷入害怕指责的消极恐惧。
进而,道德人难道就是一位完美如儒家所言的「圣人」?难道行道德非得达到史怀哲义务和牺牲超越平等理想的高度?
这里又点出一般民众容易犯的一个逻辑错误,当我们在教育当中透过某些典范来做为表达某些抽象概念与道德观的实际范例,那并不意味着典范之外的就是不对的,只有与典范相符合的才是对的。
人的本质有善性与欲望,以及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做选择的理性,以及最终下决定的意志。过去我们接触典范,经常因为对典范的片面书写而使典范失去人性,使得某些读者忘了典范人物和我们一样都是人。
史怀哲亦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著名人道摄影师尤金‧史密斯就曾在拍摄史怀哲时,因为捕捉到他平常不完美的一面,而被要求必须拿掉那些照片。
然而究竟是谁意图创造一个完美的假象?是史怀哲,还是「背负」道德使命的杂志社,抑或两者皆是?

当我们在思考生活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压力所造成的焦虑等影响生活的负面能量。
我们必须要回头去探索这样一个行动的准则,到底我的选择是「正面、积极的判断」,还是「负面、消极的放弃」?
前者清楚自己要什么,后者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并透过消去法将选择抛给他人。
在此情况下,被害妄想症将如影随行的让人无法真正拥有一个有质量的生活。
这也许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上了驾驶座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不需要让座,并且因为握有方向盘而有了自己拥有权力与决定权的假像。
实际上,这些驾驶还是活在一个道德被害妄想症的社会,故拥有权力的片刻他没有思考如何正当的运用权力,而是堕落于权力,以权力为发泄压力的借口。
若我们要去除妄想,我们必须试着接触与了解这个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
让座理当出于自愿,因为行道德乃是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对的。
而不是表面上认为那是对的,实际上我们只是因为害怕惩罚与责任,进而采取自虐方式享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快感。
◎ 高浩容
哲学、教育双博士生,台湾哲学谘商学会监事,著有《心灵驯兽师》等十多部出版品。现居上海,专职咨询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