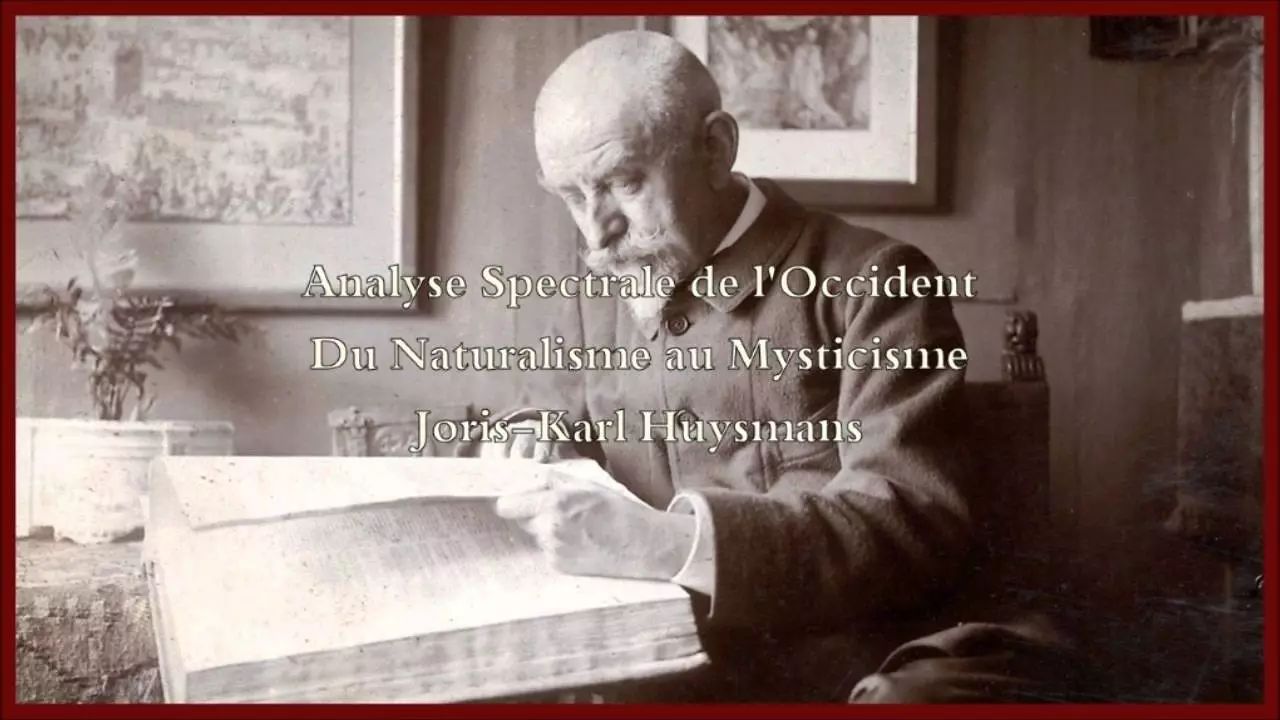
我从来不像左拉一样为一本书制定计划。我知道怎么开头和结尾——这就够了。
1880年,与德加《舞蹈课》和马奈个展同一时期,一本闪光的文学随笔集《巴黎速写》(Croquis Parisiens)出版了,并在当时的文学和艺术圈引起涟漪。在这本随兴而发的小册子里,记录了当时活力四射的巴黎社会万象。一系列精细逼真、浓墨重彩的写实文学手笔,勾画了女神游乐厅、马戏团的宏大场面与街头游走女人、栗子摊贩的众生相,在角落与片断中重建了一座晦暗又闪亮的“光之城”。
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影响了王尔德的法国小说家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名气不仅没有左拉大,在国内更是鲜少闻之,其原因,可能跟作者的独特经历和题材相关。
于斯曼1848年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Godfried Huysmans是荷兰人,一个版画家。他的母亲Malvina Badin Huysmans曾是一个校长。Huysmans的父亲在他八岁时去世了。他的母亲迅速再婚,继父是一个书籍装订厂的厂主,但是
于斯曼
跟他的继父关系并不好。

巴黎小酒馆
获得了大学预科文凭,于斯曼后来进入法国内政部当公务员,这份枯燥的工作一做32年,但是他有着另外的身份和圈子。1874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诗合集,《香料糖果盒》(Le drageoir aux épices),开始用Joris-Karl Huysmans这个名字,这本散文诗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他的丰富词藻和行文风格初步闪现。
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于斯曼作品一部接一部,1876年描写年轻妓女的小说《马尔特,一个女孩的故事》(Marthe,Histoire d'une fille),其中自然的描写手法引起了左拉的注意,并与之交好,3年后的小说《瓦塔尔姐妹》(Les Soeurs Vatard)明确献给左拉,通过在书籍装订厂姐妹的故事,写出了于斯曼巴黎生活的点滴回忆。1881年出版了另外一本关于失败婚姻的小说,影射作者一辈子未婚没有子嗣的生活。1882年的《顺水漂流》(À vau-l’eau)是早期的创作高峰,围绕一个被压制的文员如何获得体面的膳食。
于斯曼让人联想到“关税员”画家亨利·卢梭,他默默地写,不停地写,打入了自然主义的圈子,然后终于以小说《逆天》( À rebours,1884)一举成名,又从此与自然主义流派渐行渐远。
今天看来,《逆天》充满闪光点,被很多文坛后辈奉为写作圣经。只是这部关于审美家的小说,让作者跟左拉意见相左,成为颓废文学的代表。他作品中语言灵活多变,内涵丰富,细节描写令人叹为观止,以物质形象体现精神世界,并带有反讽色彩。最为突出的,是在光鲜亮丽之下的悲观色彩,作品的哲学观让人联想到叔本华。
在《逆天》中,于斯曼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德泽森特收藏的两幅以莎乐美为主题的法国画家莫罗(Gustave Moreau)的杰作。虽然他没有在书中写出这两幅画的名字,但根据描写我们可以知道一幅是《莎乐美在希律王前舞蹈》,一幅是《显形》,画的是施洗者约翰被砍下的头闪闪发光,在莎乐美面前升起。对前面一幅画中的莎乐美于斯曼有如下的描写:“当她开始那淫荡的舞蹈,并将要挑逗起年老的希律王沉睡的情欲的时候,她的脸上带着沉思、严肃、几乎是虔敬的表情。她的乳房在颤动,在她摇摆着的项链的轻触之下,玫瑰红色的乳头挺立竖起;在她肉体的湿润肌肤上,一簇一簇的钻石闪闪发光;她的手镯、腰带、戒指射出火星般的光芒;在她缀着珍珠、绣着银线、嵌着黄金的长袍上,穿着一件由金匠镂刻而成的紧身胸衣,它的每个网孔就是一颗宝石,上面似乎有盘绕着的火蛇在燃烧,就像长着色彩鲜艳、光彩夺目的翅膀的昆虫在爬过那粉红色的肌肤。”于斯曼的这段文字,就如同一道视觉的盛宴。

法国画家莫罗画笔下的莎乐美
于斯曼可以说是对颓废主义这种艺术和生活态度,进行了最细致深入的研究。左拉说于斯曼试图“用一部书竭尽一个题材”。在对颓废这种生活和艺术态度的描写上,于斯曼确实在一本书里就登峰造极,后来的英、法唯美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能就他书中的某一方面加以发挥,但总体来说没有能超过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