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
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出了大家对理想伴侣的期待:
一辈子太长,得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
这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实现却很难。
首先,得有两个有趣的人;其次,这两个有趣的人得恰好看对了眼;再次,他们最好还要活得足够长,才能达到“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的境界。
在民国众多伉俪中,能抵达这一境界的夫妻并不多。很多世人推崇的神仙眷属,大多只能做到“有情”,要想达到“有趣”,还得多一点幽默感,多一份俏皮劲儿。
携手走过百年风雨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就是这么一对堪称凤毛麟角的夫妻。他们俩年龄加起来超过两百岁时,仍能举“杯”齐眉,两“老”无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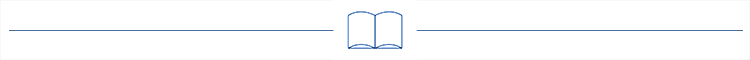

1998年12月21日,国际教育基金会举行百对恩爱夫妻会,年近百岁的周有光、张允和是最年长的一对。
岁月没有消磨掉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和对彼此的爱意,他们越活越有味,越爱越深沉,一个是新潮老头,一个是白发才女,真正做到了“有趣到老”。

(年轻时的周有光与张允和)
张允和是谁?鼎鼎大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她在张家排行第二,被称为“最后的闺秀”,张家人则亲昵地称之为“小二毛”。
张家四姐妹中,就数她最活泼、最爽朗,从小就深得父亲张武龄的钟爱,每次出门,都喜欢捎带着她,“小二毛,来!”父亲出谜语,制对联,她总是第一个抢着作答,人送外号“快嘴李翠莲”。
小小年纪,她就一肚子的主意,父母让她当四妹充和的老师,她就耍起了“小老师”的威风,给四妹改了个名字叫“王觉悟”,意思是要妹妹做个懂民主、懂科学的新人。
孰料妹妹反问她:“你既是明白道理的人,为何要改我的姓?我姓张,不姓王。”她被妹妹问住了,气得拿剪刀去拆书包上绣的“王觉悟”三个字,“觉”的繁体字足足有二十个笔画,拆得她满头大汗。这起小闹剧,日后反成了姐妹间的温馨回忆。
张家姐妹从小就跟着父母听昆曲,耳濡目染,慢慢都学着在家演戏。
姐妹们爱演《三娘教子》《探亲相骂》《小上坟》《小放牛》之类的戏,大姐元和、三妹兆和演主角,我们二毛允和呢,则是永远的配角,为主角们插科打诨、开锣喝道。
她还专爱演丑角,鼻子上点一块白豆腐,勾上几笔黑线条,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琴童、小书童,非常符合她活泼灵动的性子。
很多人演配角都会为自己抱不平,允和则高兴地回忆说:“我认为配角很重要,现在不是有配角奖吗?我的童年如有配角奖,我可以受之无愧。”后来,她在学校里、曲社里都爱演配角、凑热闹。
在三妹兆和和沈从文的婚姻中,允和可以说是一个“最佳配角”了。
沈从文苦苦追求张兆和而不得,索性追到了她九如巷的家里来,兆和不想见他,是允和劝她说,他是老师,你是学生,做老师的到学生家里来,总要接待一下吧,你就对他说,我家里有很多弟弟妹妹,欢迎来玩。兆和听了她的劝告,沈从文才有机会进了张家的门。
后来又是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开明的张家父母一口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允和非常开心,连忙跑到电报局去给未来的三妹夫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允”字,既是应允的意思,又包含了她的名字,一语双关,可见张二姐的机智。沈从文对这位二姐非常感激,到晚年时还戏谑地称她为“媒婆”。

尽管允和在曲会上演了一辈子的配角,但对周有光来说,她却是始终不变的女主角。
周有光先学经济,后攻语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四朝元老”,周有光给人最大的感觉是处变不惊。他一百一十岁时,别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是“不要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其实除了淡然处世外,活得生机盎然可能也是周有光的长寿秘诀。
他年轻时就喜游历、谈锋健,爱好十分广泛。小时跟着老师学拉小提琴,很有音乐天赋。老师让他每天练四个小时,他却说,学琴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为了成为演奏名家,于是照旧按自己习惯的时间练。
十年动乱时,他被下放到宁夏,和教育学家林汉达一起看守高粱地,仍然能够谈笑风生,好像是在对着一万株高粱演讲。
八十五岁那年,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的小书房,看报、写文章,那间书房仅仅只有九平方米,他却安之若素,还饶有兴致地撰写了一篇《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的快乐自寻。
房间阴境,更显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
九十多岁时,他头顶上的头发都掉光了,他却笑着说是还没有长出来,依然像年轻时一样,随身带着几块洁白的大手帕,时不时拿出来擦擦脸。

说起来,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结缘,还要归功于几块大手帕呢。
晚年周有光回忆起他和张允和的恋爱,用“流水式”的恋爱来形容这段关系。两个人的相识相恋,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
张允和和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两人由此相识。两家都是望族,但周家已经没落,一度连周有光念大学时的学费都交不起,所以允和常笑称自己戏曲看多了,有“落难公子后花园”的情结,不仅没有嫌弃周家家道中落,反而认定了周有光是个“落难公子”,想去搭救他一把。
张家有十个兄弟姐妹,周家的年轻人也很多,两家人常常聚在一起玩。在九如巷的小型曲会上,张家姐妹唱戏,年轻的周有光会给她们拍曲,没想到,这一拍,竟然就持续了一辈子。
可能是因为性情相近,周有光和张允和做了很多年的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在上海教书的他给还在杭州读书的她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很普通,没有一句有关情爱的话。
允和收到信后,还是很紧张,和比她年龄大的同学商量后,才敢回信。暑假两人再见面时,已经没有以前相处时的自然,可能爱情的萌芽都始于这种不自然吧。
很多年以后,允和回忆起和周有光挑明心迹的那一幕,清晰得宛如昨日。
那是1928年的一个星期天,他们一起从吴淞中国公学的大铁门走出来,一直走到了吴淞江边的防浪石堤上,两人没有手挽手,而是保持着一尺左右的距离。
在温柔的防浪石堤上,他掏出一块洁白的大手帕,细心地垫在石头上,让她坐了下来。可能是太紧张,她的手直出汗,他又取出一块小手帕,塞在两只手之间。她心想:手帕真多!
隔着一块手帕,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回想起这一刻,暮年的她动情地写道: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从那以后,她和他无论欢乐幸福,还是风雨突变,都没有松开过彼此的手。

他们恋爱期间,发生了两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一个周末,周有光和张允和相约在灵隐寺见面,那时候的寺庙,常常成为书生小姐谈恋爱的地方,《西厢记》的故事就发生在寺庙。
两人肩并着肩一起上山,始终不敢手挽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尾随在他们身后,他们走他也走,他们停他也停。这对情侣心想,这个和尚也太不识相了,于是索性坐在树下休息。岂料老和尚也坐了下来,还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
原来允和鼻子很高,轮廓分明,所以被老和尚误认为是个外国人,这才好奇地一路跟着来瞧瞧。
周有光不动声色,笑着回答:“来了三年了。”
老和尚说:“难怪中国话讲得这么好。”
热恋中的人难免要安排各种娱乐节目,有一次,喜欢西洋音乐的周有光特意请还在念书的张允和去听音乐会,地点是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把躺椅,躺着听,很贵,得两个银圆一张票。
当天演奏的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没想到,在雄浑激越的音乐声中,张允和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这位张二小姐,打小喜欢的就是昆曲之类的中国古典音乐,对西洋音乐实在是欣赏不了。
周围的人难免投来诧异的眼光,周有光心里也有点打鼓,但还是淡定地听完了音乐会,其间任允和在躺椅上酣睡,并没有叫醒她。
换成其他人,也许会埋怨爱侣不懂欣赏,周有光却完全不以为忤,反把这当成了一件趣事,可见再合拍的情侣,也需要有一颗懂得包容的心,关系方能长久。

相识十年、恋爱五年后,两个人准备结婚,定下日期后,允和的姑奶奶出面阻止,认为喜期定在月末不吉利,是阴历的尽头日子。于是改为4月30日摆酒,结果发现是阳历的尽头日子,再改已来不及了,只好如期举行。允和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婚礼很简单又很新潮,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后来成为张家大姐夫的顾传玠吹笛伴奏,还有一位白俄小姑娘弹奏钢琴,称得上是中西合璧。
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第一个结婚的,起初张家人并不看好这段姻缘。照顾允和的保姆拿着这一对新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称,这对夫妻都活不过三十五岁,连三妹兆和都说:“二姐嫁给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尽管如此,开明的张家还是没有阻拦他们的结合,还给了新婚夫妇两千银圆的嫁妆。他们用这笔钱出国留学,并乘坐当时最豪华的游轮“伊丽莎白皇后号”遍游美、英、法、意大利、埃及等地。
结婚前,周有光有些忧虑地给允和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表明了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年老相伴的周有光和张允和)
他们果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两人共同生活了近七十年,允和活了九十三岁,创造了白首不相离的奇迹。
七十年的婚姻岁月,就像婚前一样,仍然是流水式的相守相依,其间不乏风风雨雨,抗战时他们经历了丧女之痛,特殊年代又受到打击,他们却用天性中的乐观和热情,将每一天都过得生机盎然。

这对恩爱终生的夫妻身上的共同点很多,其中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乐观和活力。
晚年的周有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张允和的乐观人生》,在他眼里,这位夫人既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又是充满朝气的现代新女性。
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后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在干孙女曾蔷的眼里,这位张奶奶的性格恰如宋词,既婉约,又豪放,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坚贞不屈的一面。
“文革”期间,红卫兵来抄他们的家,可在张允和看来,这些红卫兵只不过是天真的孩子,这个时候化身为十分严厉的导演。她自己呢,平时在戏台上扮惯了小丑,在这非常时刻,也就当是在演戏陪孩子们玩儿吧。
回顾这场风波,她一点怨气也没有,说:“我的孙子在我面前耍猴,我生不生气呢?当然不。”
都说人生如戏,人啊,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种游戏的精神,这样才能出乎其外,不至于陷入痛苦无法自拔。
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当时多半在劫难逃。当时有人戏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有光随口对出下联:“秦皇汉武毛泽东”。一下子捅了马蜂窝,被打成了反革命,下放到宁夏平罗。
在平罗,他染上了青光眼病,病情危急,张允和则带着孙女在北京借贷过日,并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每月给周有光寄药,共寄了四年零四个月。

回忆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周有光记住的居然都是些趣事。
且看他笔下的“大雁粪雨”:“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的头上。”尽管有大草帽顶着,他身上仍沾了不少粪便,可在他看来,大雁粪便准确地落到人群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所以笑称自己运气太好了,遇到了幸福的及时雨。
他被发配到宁夏农场,和林汉达先生一起看守高粱地,这里荒芜,两个老头儿躺在高粱地里,仰望长空,畅谈起了语文的大众化,林汉达问他“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地回答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就是凭着这种他们夫妇所说的“阿Q精神”,他们总算熬过了劫难。

回到北京的周有光,推出了一系列语言学的著作,工作到八十五岁才退休,仍然笔耕不辍。有记者问他:你一生百岁,有点什么经验可以留给后人?他回答说: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终身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一台夏普打字机,是周有光的宝贝,早在1988年,他就学会了打字。
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感染了张允和,八十六岁那年,为了重新编印张家的家庭刊物《水》,这位张二小姐决定学习打字。她的老师,自然就是被沈从文称为“周百科”的周有光。

(晚年的周有光和张允和)
张允和是合肥人,普通话不标准,“半精(京)半肥(合肥)”,老是拼错字,这时候,只需要一句“帮帮忙”,周有光就会应声过来,帮她校正。
可以说,允和打出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丈夫的爱意和耐心,所以她最先会打的就是“亲爱的”三个字。正是用这台打字机,张允和创作了《最后的闺秀》等作品,八十八岁时出版了处女作。
如果说打字方面是“妇敲夫审”,那么唱起昆曲来,则是“妇唱夫随”了。张允和晚年与俞平伯等人一起成立了昆曲研习社,周有光常常陪同她去参加曲社活动。允和七十岁生日时,周有光送了她一套《汤显祖全集》,老太太心里甜滋滋的:“他真是懂我的心思。”
夫妻俩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张允和是“诗化的人”,富于传统文化韵味,周有光则是“科学的人”,条理明晰,滔滔善辩。性格不同,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以音乐为例,他跟着她去听昆曲,她则跟着她一起听西洋音乐。
他们的婚姻生活是雅致和雅趣的结合,夫妻俩经常不定期地请一些“亲爱的”来参加“一壶酒、一碟菜”的“蝴蝶会”,还在酒席上行“新水令”。他们在朋友的帮助下,用五线谱等记下了评弹的词和曲,使无论哪国的音乐家拿起乐谱就可以演唱。
“快乐极了”“得意得不得了”成了晚年张允和的口头语。他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四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个“举杯齐眉”,既是为了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后辈们都笑他们“两老无猜”。
常有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周有光夫妇的想法截然不同,周老先生曾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的理论是,人过八十,年龄应重新算起,九十二岁时,还自称“十二岁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