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好,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没有对标的时代。
很糟,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没有对标的时代。
中国服装业此刻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间,游移不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总是能很快找到“对标物”。
曾经,在温州、晋江等地区,服装巨头们重复着一轮又一轮简单却有效的动作:以一线的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国际品牌为对标物,借鉴其设计,通过明星代言、赛事赞助和大众媒体广告轰炸,先在二三线城市攻城拔寨扩张渠道,再来反攻一线城市。
在吴晓波老师看来,这样的商业脉络,集成了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所谓的后发优势,是指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成熟品牌的各个方面,然后利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最强大的制造能力实现弯道超车。
而后发劣势在于,过度依赖会导致企业创新停滞和制度僵化。即便在跑步的时候猛冲到了第一名,但前方没有对标物了,此时就会产生对未知的恐惧,不知所措,失误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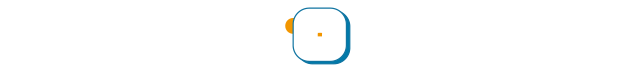
“没有对标的时代”
2008年,中国服装业已拥有全球最大也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当时欧洲服装企业的高管到浙江一带考察,已经看不懂中国工厂拥有的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了,感叹“他们哪来这么钱”。
这是中国服装行业首次在制造领域进入“没有对标的时代”。
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引发的运动热潮使得行业急剧扩张,各大公司纷纷上市。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增速戛然而止,渠道的“大跃进”和销售的大批发模式,使得生产过剩,整个行业陷入到“去库存”的低谷中,中国六大运动服饰品牌关闭5000家。
当生产端没有对标的时候,行业第一次出现极为陌生的萧条现象。安踏的丁世忠感叹道:“闭着眼睛也能挣钱的时代结束了。”
本质而言,那是一个重视生产力和渠道的时代。很多服装企业像是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采取的是一种“选品”商业模式,依赖于供应商的设计做选择,没有自己的设计和生产,更别提“品牌精神”。当国际大牌开始渗入到二三线城市后,这些企业就被挤压得异常难受了。
有的企业在这场萧条中收缩规模,有的从此一蹶不振,有的则永远退出了市场,但也有企业找到了新的“对标物”:学习耐克、阿迪达斯搞营销、做品牌(Branding),他们通过渠道重构、国际并购、加强自主生产等手段,走出了危机。

配合消费升级的趋势,2018年之后,中国头部服装企业找到了品牌密码,开始塑造品牌形象,也抢占了国际品牌大量的市场份额。在营收方面,它们甚至一度超过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子公司。至少在中国这个熟悉的市场,服装企业似乎正进入第二个“没有对标的时代”。
然而到了2023年,高库存、慢周转速度的魔咒再一次降临,中国服装业又很快第二次来到了陌生山谷,行业的周期似乎难以穿越。
这一年,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访问安踏总部,创始人丁世忠问他:“历史上有没有能让我们对标的发展阶段?”
钱院长停顿片刻,说“没有可以直接对标的对象。中国企业如今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更像是一百年前美国企业所面临过的。”
彼时的美国,诞生了洛克菲勒、JP摩根、福特汽车、可口可乐、宝洁等一批优秀企业,它们穿越了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石油危机、次贷危机等大周期,成为现代企业的范本。
那么,当前方充满未知的恐惧,中国服装企业想要穿越周期,到底该怎么办?吴晓波老师在年终秀中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放弃对标,勇于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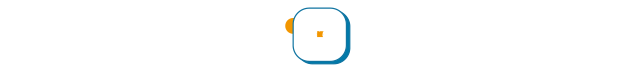
放弃对标
放弃对标,当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却是一些服装头部企业不得不跨出的第一步。
安踏品牌CEO徐阳曾在内部开过一个脑洞:“有两家公司,A公司年收入400亿元,年均增长9%。B公司年收入700亿元,年均增长7%。请问A公司超过B公司需要多少年?”
答案是31年。所以,当用别人擅长的方式去追赶别人时,去赶超那一串数字会变得异常艰难。用徐阳的话说,“一门心思盯着销售的时候,反而会把雪球越滚越小”。
放弃对标的企业往往有三种选择。
◎ 其一,换一条赛道奔跑。像比音勒芬创始人谢秉政,尽管在服装行业赶了个晚集,但他没有选择赛道拥挤的男装,而是换了一条叫高尔夫球服的新赛道。
◎ 其二,故意慢下来,另辟蹊径。当前面的企业跑得太快,往往会遗漏一些市场。过去二十年来,许多服装、电商等企业并没有和一二线的对手竞争,反而进入了被忽略的庞大的下沉市场。
◎ 其三,换一辆自行车跑。在同一条赛道,并没有规定必须用跑的形式,有时候,新工具和新模式往往会带来颠覆式的效果。当把对手甩得足够远时,就很容易克服对前方未知的恐惧。

徐阳曾问同事:“想比一个跑马拉松2小时36分的人快,该如何做到?”答案是一句反问:为什么不骑自行车呢?
徐阳的这辆“自行车”,叫超级安踏。
超级安踏是一个“目的地式”的零售场,消费者可以一站式购买从专业运动到运动休闲、从鞋履服饰到运动装备的商品,一应俱全。产品按照性别、不同的消费圈层、细分场景、专业场景全面覆盖。
以运动鞋为例,超级安踏有跑鞋、篮球鞋,还有小众的拳击鞋。而即便是常见的跑鞋,在超级安踏里,有二十多款不同功能的跑鞋,覆盖马拉松、户外越野、日常慢跑、竞走、通勤等多个场景,每一列从高到低,四个单品,四个价格档次,每一列鞋墙可以直接打开,消费者可以从隐藏鞋柜中挑选尺码。
与常规门店不同的是,超级安踏的门店面积高达1000平方米,产品零售价格平均低33%,但营收却要多3倍。在过去的一年里,超级安踏已经开出45家店,2025年计划开出160家。

超级安踏的“场景走廊”设置与行业内声名鹊起的迪卡侬相似,但安踏认为两者实际上并不在一条赛道上。
迪卡侬以卖运动装备为主,鞋服占比不超过15%,而超级安踏鞋服占比超过80%;此外,一些时尚休闲品牌也尝试过大店模式,但考虑到换季流行频繁,往往会导致SKU过多,以至于库存率高居不下。超级安踏却是以“丰富的场景+单一场景全链条产品”,强化了门店和品牌的专业性,让产品具备功能性,由此达到聚焦SKU的目的。
从更深的战略层次来看,超级安踏有其内在的驱动力。
露露乐檬(lululemon)的创始人奇普·威尔逊,曾创造了DTC一词,Direct to Consumer(直接面对消费者),意思是“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向消费者出售高性价比产品”。
2020年,DTC首次出现在安踏的财报中,安踏结合自有战略将其重新理解为“直营门店业务”,而非露露乐檬的“线上直营”或耐克的“线上+线下直营”。
这意味着近十年来,安踏从批发模式,彻底转向直营模式,从零售品牌转到直营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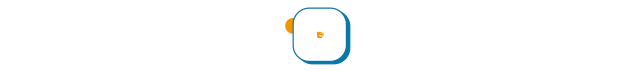
自我革命
安踏的前方很快遭遇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过去30年的自我经验”。
DTC自然利好消费者,但对曾经的经销商来说却是一把刀子。
服装行业有其特殊的“期货模式”,通常一年有4次订购会,设计师提前对设计的样品进行打样,集中陈列在订货会现场,由各地经销商下订单,厂商汇总进行排期生产和供货。好处是让市场需求传导至生产端,实现“以销定产”。可见,经销商和厂商的利益捆绑之深。

但问题是,当厂商有了其设计、研发和营销能力后,就需要通过更精准的市场洞察、用户数据做出更敏捷的反应和动作,让订单快速滚动起来。
显然,一年四次的订货会难以再适应波谲云诡的市场,而当消费者数据掌握在经销商手中,也不利于品牌洞察市场趋势。
降低价格,提高销售和店效,只有DTC占比超过80%的公司才能做到。
DTC能将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化整为零,打通人、货、财务、数据,让超级安踏实现许多以前备受掣肘的动作。它不再是传统的期货模式,而是“小单快返量产”。
在生产端和供应链端,可以看到DTC模式给安踏带来的变化。超级安踏每天的SKU销售数据都会反映在供应链报表里。而当SKU被极大地精简,供应链也最大限度地集中,销售数据可以针对市场情况以最快速度转化成生产订单。由于面料供应集中且提前预备,可以及时地柔性生产。
如此一来,超级安踏能极大地降低“库存率”。
在疫情期间,安踏几乎完成了代理商的“收编”。短短3年多,品牌直营门店超过7000家,收入占比达56.1%。在过去的一年里,安踏还更换了5位(区域)总经理,包括了收编前的代理商,它正在拼上“全直营”的最后一块拼图。
不动既得利益者利益,又谈何改革。吴老师曾评价超级安踏:“这是一场刀口朝内的自我革命。”

通过对渠道金字塔模型和供应链的解构,放弃对竞品和自己的对标,安踏找到了那辆带它飞奔的自行车。

新物种的土壤
超级安踏是安踏制造出来的新物种,但它与安踏依旧血脉相连。
在多次思考“我是谁”的命题时,丁世忠曾多次强调“必须拥有一定的自生产能力,以快速反应来自市场或渠道的需求变化,同时获得部分成本优势”。
“超级安踏”这个新物种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正是继承了这些思想——将生产、技术、渠道控制在自己手里,并时刻关注效率和市场的变化。

新的养分则来自安踏多年的全球化尝试。20年前丁世忠就喊出豪言壮语:“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
2009年8月,中国运动鞋服品牌安踏以3.32亿人民币收购Full Prospect的85%股权,取得运动时尚品牌斐乐(FILA)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的商标使用权和专营权。
自2018年起,斐乐将业务拓展到网球、滑雪、高尔夫、户外等领域,每年投入千万元研发材料和科技,到了2023年,斐乐在专业运动品类的收入占比达到了40%。这是安踏的“向外求”。
而借助集团层面的收购和策略转型,安踏开始用一种“向内求”的姿态去重新考虑全球化——先通过自我革命,在内部打磨出一个更高效的模型。全球化的成功并非开海外公司,本质是新模式的输出。
这便也是“超级安踏”这一试验品的由来。
安踏内部有一句老话:“吹过的牛都能实现”。三年前,安踏开始培养10年以后的高管团队,希望未来的管理者不能只有执行力,也要有战略眼光,“敢吹牛,打硬仗”。
当你敢在一条拥挤的跑道上飙到180公里/小时,对于前方也就无所畏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