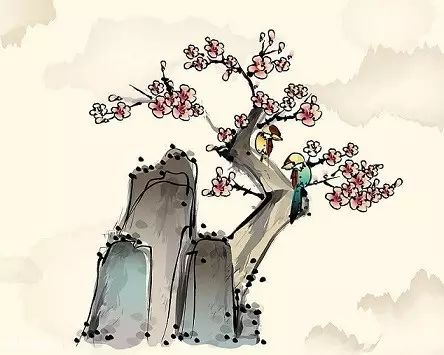建筑中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权力?本文聚焦于罗马城中的公共建筑,从权力-空间的视角总结出了三种权力在空间的表达方式:占领、渗透与辐射。不同于从史书中研究罗马史的传统方法,作者深挖罗马城公共建筑所映射罗马帝国前期的权力变迁,颇有以微知著之韵味。(政治学人编辑部)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帝国前期罗马城里典型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阐释政治权力在敞阔空间里的三种表达方式:占领、渗透与辐射。广场作为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皇帝们进行权力展示的典型场所,权力对空间是占领关系。以大角斗场为代表的敞阔性空间,不仅是罗马社会的浓缩模型,更是权力对空间渗透的场域。复合型的建筑风格和具有综合功能的皇家浴场从感官上实现了敞视性的效果和权力对肉体的隐秘控制,在这类生活娱乐的公共空间里,政治权力渗透个人生活。罗马城恢宏的公共建筑是政治精英炫耀性权力的展现。凭借罗马帝国的背景,罗马城对帝国发挥着辐射作用,首都与疆域广大的帝国紧密关联。通过分析政治权力在敞阔空间的三种表达方式,可以发现,竞争性的权力格局作为共和传统的遗留,塑造了帝国前期政治权力的表达方式。
在欧洲政治发展的长河中,古代罗马共和国以其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制度荣膺西方政治制度的“王座”,它的璀璨光辉一直照耀进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之中。罗马作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政治体,它的辉煌之巅是帝国阶段。从共和国到帝国,罗马经历了政治权力的集中,著名的军事将领将各种权力集合于一身,其中的权力角逐是史学家们撰写罗马史的主题,因此,罗马史研究的多是战争史和王侯将相史。本文另辟蹊径,从空间分析的角度,以典型公共建筑和罗马城为研究对象,分析政治权力在敞阔空间里的发生和表达,探讨罗马共和传统对帝国的影响以及繁盛的罗马帝国前期在空间上的宿命。
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中,空间是规制政治权力的重要维度。执政官和保民官的权力仅限于罗马城内和罗马城外的一罗马里,征战回来的军事统帅也不得带领军队跨越罗马城外的卢比孔河。这些措施都是要避免出现一个绝对强大、不受时空限制的权力,但是,公元前149年,凯撒带兵跨过卢比孔河,进入罗马城。此举显然是对共和制度的破坏。罗马共和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广场,主要是指罗马广场和马尔斯广场,罗马人在这两个广场上召开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共和国标志性的权力机关,当时的公民大会主要有三类:百人队大会、部落大会和平民大会。百人队大会在罗马圣城之外的马尔斯广场集会,部落大会和平民大会通常在圣城内的罗马广场进行集会。早期公民大会的决策方式是欢呼,后来发展为投票。当代学者苏米曾这样构想,“在一场标准的选举中,罗马人民拥挤地聚集在马尔斯广场,逐一部落或逐一百人队地进入选举棚进行投票。这里用 ‘椭圆形’是非常贴切的描绘:选举人进入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曾经通过欢呼,后来通过秘密投票来选举官员”。早期的选举棚是临时搭建的,选举之后就被拆除。相对应地,在罗马圣城之内的投票点是罗马广场东南角的卡斯托神庙。
在共和时代,罗马广场是圣城之内最重要的公民集会场所。在空间上,与卡斯托神庙成对角线排布的是元老院,元老院墙基向外延伸出演讲台。演讲台的弧形结构围起了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公民集会的场所。演讲台不仅是政治精英发表演讲的地方,也在投票环节发挥作用。完成投票的公民会逐一走上演讲台,这是一种展示也是一种监督。所以,作为罗马广场上视觉的制高点,演讲台也是权力焦点。
由此,选举棚、卡斯托神庙、元老院和演讲台成为共和时代最重要的权力建筑标志。这种空间格局一直持续到共和国晚期的凯撒时代。凯撒当政期间,计划将选举棚修建成永久性的建筑,成为共和的标志。公元前26年,朱莉亚选举堂在马尔斯广场建成。这是一座长310米宽120米的围合型建筑,东西都配有精美的柱廊。进入帝国时期,奥古斯都及其以后的两任皇帝在选举和集会的间歇,都将其作为观看角斗表演的场所和市场。公元80年,一场大火将其烧毁,复建以后的选举棚在110年又遭到大火的焚烧,哈德良皇帝将其重建。
朱莉亚选举堂曾经一度是共和国时期最大的有顶建筑。这一点足以看出它在共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帝国早期选举堂功能发生的变化,有学者非常尖锐地指出:“民主,从传统意义上说,几乎死亡。”这一评论虽显极端,但却是一针见血。事实上,共和国晚期,凯撒已经控制了半数官员的任免权,平民的参政频次大大降低了。由此,选举堂变成了一个纪念品,是对共和传统的纪念,其原初的功能已经遭到贬损,但它的纪念意义毋庸置疑,后世的皇帝也因此没有捣毁它。更关键的是,它奠定了罗马政治的空间基调——公之于众。虽然政治精英们在暗地里进行着权力斗争,但是,权力还有其外显的一面,本文后面谈到的权力炫耀性就是以权力的公开性为基础的。
共和国晚期,除了朱莉亚选举堂成为共和没落的标志之外,元老院和投票点神庙的变化也昭示着共和时代的结束。
公元前29年,屋大维启用了新的元老院朱莉亚元老院,因为旧元老院在公元前52年的一场骚乱中被毁,它是凯撒时期就决定建立的。内战后,屋大维把它完成,并把凯撒在战争中俘获的胜利女神雕像放在新元老院里,用以铭记他的胜利。新旧两个元老院位置比邻,朝向不同。在同一年,在火化凯撒的地点上建成了狄乌斯朱莉亚神庙,它位于罗马广场的正东面,到公元前9年,这里已经成为投票点。共和时期的投票点卡斯托神庙在公元前14年经历了一场大火,大火后虽然被重建了,但是投票点还是转移到了狄乌斯朱莉亚神庙。
元老院和投票点位置的变化是共和空间解体的最后一步。在此之前,早在公元前44年,凯撒就把曾经是元老院一部分的演讲台挪到了广场的西端,成为独立的部分,使其面对广场的开阔区域。“将高台从元老院的结构中剥离出来,标志着与共和的断裂。站在新高台上的演讲者不再以元老院为背景,也就减小了对贵族的约束。”
由此,演讲台、投票点和元老院都有了新的位置和朝向。这些变化使得原来的共和空间不仅实现了体量上的增大,而且还构建了一条新的权力轴线。共和时期,位于广场西北角的元老院和演讲台紧密连接,构成权力的核心,投票点卡斯托神庙在广场的东南角,权力的轴线是西北-东南走向。到了凯撒和屋大维时期,元老院偏踞广场的西北角,演讲台和投票点构成了东西向的权力轴线。元老院疏离于权力轴线的空间地位与其在共和国晚期的权力式微相吻合。“罗马广场,成为了国家的神龛,被费尽心机地完好保存着,但是,它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
另外,选举堂、元老院和投票点神庙这三个重要公共建筑都冠以凯撒的家族姓。这种命名既是对凯撒的铭记,同时也是对共和空间印记的擦除,因为,作为人民的事业,共和国是匿名的,“人民”才是它的标记。
综上,共和建筑的名存实亡与传统共和空间的退隐很大程度上缘自凯撒家族对空间的占领与重新刻画。
罗马广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当时,火神庙是广场上的主要建筑,包括神庙和祭祀居住的地方。共和国时期,元老院和若干神庙被重建,成为公民集会、辩论和审判的地方,稍晚一些建成的巴西利卡成为广场的边界。公元前63年,西塞罗著名的反喀提林阴谋演讲,就是在罗马广场的和平神庙里进行的。作为共和派的领袖,西塞罗更强调广场的平民性质,将其称为罗马人民的广场,凯撒的火葬也是在此举行。屋大维上台以后,除了为自己建造了凯旋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建。上文谈及元老院、投票点神庙和演讲台点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罗马广场的总体轮廓。
罗马广场不仅是一个开放的政治空间,也是一个记忆的空间。共和国早期,无论是罗马的显贵还是普通公民都可以在广场上安置自家的神龛或者建筑雕像来纪念军事胜利,这就导致了广场的拥挤和杂乱。公元前158年,监察官清除了广场的大部分雕塑,只留下那些由元老院和经过公民大会同意而竖立的雕塑。
如果说罗马广场是平民的广场,是共和时代的遗产,那么后来在它北边陆续修建的凯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韦斯巴芗广场和图拉真广场等就是帝国时期皇帝们想为自己留名的佐证。这些广场都供奉着皇帝家族的神庙,建有标记战功的凯旋门,以及增加视觉美感的开放庭廊。这些建筑物表明,当权者认为公共空间就是一种资源和媒介,可以用来展示和强化政治权力。这些广场不仅是政治仪式的舞台,而且也是日常生活必需的公共空间,用来完成多种多样的功能。在日常生活的层面,皇帝广场上的柱廊和小厅(带座的凹室)首要用来承担法律和行政事务,奥古斯都和图拉真广场有时还是思想活动的中心,各种各样的演讲都会在那里举行。“很难想象,诸如法庭诉讼这样的活动在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进行,有时只是用帘子隔开。这不仅是鼓励观众的评论,而且还孕育着一种非凡的有关权力和法庭要牢固系于人民的观念。的确,皇帝本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连续数个小时主持法庭审判……我们必须这样想象这个空间:它充斥着各种目的的到访者,赶去会友的,找熟人的,闲逛的,看热闹的。”
另外,这些广场自然地按照从南到北逐次排开,从中可以分析出如下政治意义。首先,皇帝们是开拓新的空间建立广场,而不是对既有的罗马广场进行覆盖,或进行重命名。这就揭示出罗马广场的地位:罗马广场因其承载着共和时代的记忆而不可被替代或擦除。由此,共和传统被嵌入帝国的时代。其次,皇帝们同样也没有覆盖前任统治者的广场。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能力不及,出于道德不可以去“斩尽杀绝”,或者认为广场就是公共空间,功能比归属更重要。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罗马的各个广场在帝国前期形成了一幅“拼贴画”,虽然各个组成部分大小不一,但是它们在同一时空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竞争性的共存,空间共存的表象之下是各个权贵家族之间的力量对峙。
在古代罗马人的公共娱乐活动中,观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观剧、观看战车比赛和观看角斗与处决罪犯。观看战车表演的大竞技场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后来,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统治者不断地对其进行加固和完善。角斗活动起源于罗马祖先的祭祀活动,在共和时期,这种娱乐活动也是存在的,只是表演结束以后,场馆和设施就被拆除。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罗马人的道德自律,娱乐是暂时性的;其二,大规模的民众聚集蕴含着暴乱的危险。公元59年,庞培圆形剧场的一次骚乱遭到严厉惩罚,角斗表演被禁止达十年之久。尽管如此,这些观演活动仍使得敞阔性的空间成为公共生活的必需,大角斗场就是这种空间的典型代表。
公元71年,皇帝韦斯巴芗决定建造一座供民众娱乐的永久性大型建筑。皇帝不再担心民众骚乱了吗?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韦斯巴芗皇帝的前任统治者是臭名昭著的尼禄,他为自己建造奢华的宫殿,遭到罗马民众的极端厌恶,韦斯巴芗皇帝决定排干尼禄金宫的私人湖,在旧址上建造一座大角斗场。建造的资金来自皇帝本人镇压犹太人起义后流入罗马的贵重战利品。通过这种方式,前后两个皇帝形成鲜明对比:一个自我享乐,一个为民造福,因而后者显得越发仁慈伟大。所以,皇帝虽然担心民众骚乱,但是,与获得的民众好感相比,后者更有吸引力。另外,韦斯巴芗皇帝的这种做法也符合罗马人对独裁者的惩罚原则——“除名毁忆”。
历时十年,大角斗场于公元80年建成,成为古代罗马体量最大的公共建筑。它呈椭圆形,外围长轴187米,短轴155米,中央为表演区,长轴86 米,短轴54米,它的看台逐层升高,约有60排,分为五个区,最下面前排是贵宾(如皇帝、元老和祭司等)区,第二层供贵族使用,第三层给富人使用,第四层给普通公民使用,第五层也就是离表演区最远的一层,给底层妇女使用。大角斗场可以容纳约八万名观众。除了角斗表演之外,处决罪犯、历史戏剧和神话戏剧的演出也在这里进行。
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大角斗场的内部空间构成了敞视性权力的场域。
第一,大角斗场的座位层级与观看者的社会地位对应,成为囊括所有罗马社会阶层的整全性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被精心地区分好,甚至不同层级空间的人在走向自己的座位时,使用的通道都是彼此不交叉的,加之大角斗场的体量巨大,这使它能容纳每个阶层的众多成员。大角斗场空间的包容性和区隔性使得各种社会地位的成员都能实现“全员到场”。这是敞视性权力“出场”的前提。
第二,从空间-身位关系看,无论是皇帝还是卑下的婢女,大角斗场里的观众之间都是彼此可见的。在这样一个“全员到场”的场合,皇帝不仅扮演着“与民同乐”的亲民形象,而且对角斗士的赦免也是他行使生杀予夺权力的最佳时刻。这种权力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它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个场景将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表达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帝制中国时期,高墙深院里的皇权使用的则是另一种空间策略——通过距离与神秘让臣民感到恐惧进而服从。大角斗场里的罗马皇帝则是利用敞视性的空间将最高权力用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一种敞视性的权力,权力本身由于这种敞视性的空间而得到了加强。
另外,民众也可以在这个敞视性的空间里展示权力。正如有学者评论说,“大角斗场是个建筑精美而又封闭的世界,它将皇帝、精英人物和臣民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塞到一起。排列得密密实实的观看者兼参与者,看别人又被别人看,按地位高低排列有序——按规矩,高官靠前,群众在后——隔着中央的竞技场彼此面对。这是一个绝妙的环境:统治者可以向他的公民兼臣仆展示权力,臣民可以把他们的集体力量显示——或者至少幻想着展示——在皇帝面前”。可见,敞视性的空间使得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被看到和关注到。大角斗场里的敞视性权力无论是属于皇帝,还是属于民众,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那么,皇帝之所以被其他人关注,在这个敞视性的空间里获得优势地位,正说明罗马人是预先带着“皇帝有着生杀予夺大权”这种观念进入角斗场的。罗马的大角斗场是一个特定的场域,里面预先设定了某种关系,而这种空间特征又强化了这一关系。当然,罗马皇帝并不都是每场角斗的“裁判员”。尽管如此,罗马皇帝具有的这种敞视性权力是存在于角斗场这种大体量广角空间里的,它是罗马皇权在空间上的体现。
第三,大角斗场除了是一个娱乐表演场所之外,还是一个社交场所。“坐在前排的罗马社会精英也会向朋友们点头,炫耀自己的地位。此时此地肯定也进行着买卖合同、推销、结盟、婚姻初次提起或往下进展的事情。”所以,大角斗场是一个嘈杂的,兼具娱乐、政治和社交功能的场域,罗马皇帝权力的展现“被编织”进大角斗场的图景里,成为突出的前景。
综上所述,皇帝的最高权力被空间方位上的优势地位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权力对空间的渗透;同时,在大角斗场的敞阔空间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着,他的主宰力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展现出空间对权力的助推。
装饰作为建筑的细节,是建筑品质的外在表现。共和国晚期,在对建筑装饰的讨论中,西塞罗曾经指出:“罗马人民憎恨个人奢华,但是他们喜欢公共排场。”对精美之物的道德评价,要看它们是用在什么之上:用在个人生活中就是被憎恨的奢华,用在公共事业上就变成了令人称道的荣耀。所以,罗马公共建筑的装饰是非常精美的,而且表现出复合型的特征,这种复合既是指建筑风格上的,也是指功能上的。
早在共和国早期,幸运女神庙就融合了经典的雅典柱式和流行的罗马拱券式,这种融合在大角斗场的外墙体现得更加明显。角斗场的主体用拱券式架高,用三种风格的柱式进行支撑和分隔。这三种柱式从低到高依次是多立克柱式、科林斯柱式和爱奥尼亚柱式,越往高处花纹的细密程度越高。
那么,这种具有复合特征的建筑装饰如何表达帝国时期的政治权力呢?在观看者的角度,这些综合性的建筑风格和元素是一览无遗的,呈现出敞视性的效果。作为公共建筑,神庙和大角斗场本身就是当时罗马建筑水平的集大成者。讲求排场和荣耀的罗马人,自然会把他们认为美的元素都表达出来,这些杂糅的元素与罗马帝国本身庞大疆域里的不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诸如大角斗场这样的宏伟公共建筑,当然是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最高审美的体现。从感官层面上讲,各种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拼接在一起,装饰着罗马宏伟的公共建筑,这些不同颜色的石头来自帝国的不同地区,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帝国的广袤;从心理层面上讲,公共建筑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表征物,具有敞视性视觉效果的建筑装饰暗示出罗马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的思维模式甚至可以迁移到罗马人对集权的欢迎:原来分立的各种角色,如保民官、执政官、将军等都可以赋予一个人。
这种复合性不仅体现在建筑的装饰上,而且体现在建筑的功能中,最显著的一个例证就是提图斯浴场。它兼具浴场、体育馆、演讲大厅和图书馆的功能,而且,这种多功能的浴场成为皇家浴场的标准设计模板。图拉真、卡利古拉和君士坦丁等皇帝在整个帝国境内都修建了这样的浴场。公共浴场是罗马帝国时期又一项公共福利。浴场的结构复杂,不仅提供各种洗浴方式,更是公民运动和社交的场所,罗马公民可以在这里悠闲地度过大半天时光。由此,权力对公民时间的操纵是不言而喻的。
公共浴场构建了身体和心灵都被关照和服侍的空间。当代学者保罗·赞克认为,皇帝有意识地将洗浴置于古典“派地亚”制度之中,是对古典生活的回归。“派地亚”的含义后来演化为“教化”“抚育”,这种公共浴场使帝国权力实现了对个体全面而彻底的渗透。将身体与权力联系起来的经典理论首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思想,依照福柯的视角,公共浴场可以看作是政治权力的延伸,通过使人身体舒适和心情愉悦产生对权力的认可。依循这条解释路径,视觉上的敞视性和身心的舒适性都暗含着权力者对观看者和洗浴者最大程度上的给予,这种给予可以解释为一种影响力,一种潜在的权力,它跨越公共空间进入个人的领地,与极权政治类似。
由此,复合型的建筑装饰和功能可以营造视觉上的敞视效果,使得身心皆感到愉悦,这是一种权力对肉体的隐秘控制,是权力基于生理反应的渗透。
到公元一世纪结束,罗马城的公共建筑不仅数量繁多,而且质量精良,“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的建筑工程达到了罗马建筑学的最高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缘于历代罗马皇帝们对公共建筑累积性地投入。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记录了从凯撒到图密善的十二位皇帝在任职期间在城市公共建设方面的成就。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政要人物也被要求修建公共建筑。奥古斯都在自己做出表率之后,“还经常督促其他知名人士新建纪念碑或重建与装修旧纪念碑以装点罗马……他还将其余的大道分配给其他那些曾经受过凯旋式荣耀的人,要求他们把战利品获得的钱用于铺路”。罗马政要们之所以要修建公共建筑,是因为他们意图通过修建公共建筑为自己赚取“空间资本”,表达自己的能力,这既可以赢得民众的喜爱,更可以向自己的竞争对手示威,是一种以竞争为内核的炫耀性权力。所以,政治精英们首先是排他性地占据了公共空间,然后用带有自己印记的公共建筑去刻画它,从而使公共空间成为个人权力的表征。
事实上,这种炫耀性权力是共和国的遗产。“在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国时期,私人住宅简单朴实,显示出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庄严雄伟的建筑物则都作为公共用途,可以展现人民的主权,这种共和精神在重视财富和建立帝制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公共建筑物关系到国家的庄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最重视道德原则的皇帝,也要竭尽所能力求完美。”另外,共和国时期,战胜归来的将军都会用战利品来装点和美化城市。共和国晚期,共和派领袖西塞罗也指出,“每当最杰出的人物就任市政官时,人们就期待他举行盛大的请客招待活动,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这说明,无论是共和国时期还是帝国早期,伴随着党派斗争,这种炫耀性权力是内生于政治制度中的,而且被整个罗马社会认可,甚至被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