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被誉为拉美文学爆炸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科塔萨尔短篇小说的最让人着迷的是拼接的叙事效果——画面的拼接,时空的拼接,以至结构的拼接,读者仿佛在一个变幻莫测的魔方里享受探索叙事的乐趣。他认为“现在”是愚蠢谎言,因此时间和空间的穿越再自然不过;他认为“现实”过分天真,因此怪诞的幻想和例外更层出不穷。科塔萨尔那细密的笔触就这样跟随着他的思想,在过去和现在,现实与幻想,日常和例外之间施展魔法,扣人心弦,如幻亦真。

胡里奥·科塔萨尔作 何旸译
有一阵子,我脑袋瓜里尽琢磨着美西螈。我常常到植物园水族馆去瞧,观察它们纹丝不动的神态或隐蔽细微的动作,一呆就是好几个钟头。如今,我自己也变成一尾美西螈了。
我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偶然去看美西螈的。那时节,巴黎正熬过漫长的冬季,容光焕发,宛如孔雀开屏。我骑车沿皇家港林荫大道而下,随后踏上圣马尔塞路和医院路,只见一片灰白之中绿意绽露,便不由得想起了狮子。我是狮子和金钱豹的常客,可水族馆那幢房子潮湿阴暗,我是连门槛也不迈的。我把自行车往铁栅栏上一靠,就去观赏郁金香了。没料想那会儿狮子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极不中看;而那头豹子呢,又高卧未醒,于是我就挑了水族馆随便瞧瞧。我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平庸俗气的鱼类之后,不料竟和这美西螈邂逅相遇。我足足欣赏了一个钟头,所以,当我离开水族馆的时候,脑袋瓜里就再也不想别的了。
我在圣热内维埃夫图书馆查了查词典,了解到美西螈实为虎螈幼体,有外鳃,系两栖纲钝口螈科。该物原产墨西哥,这一点,我从它们本身的模样,从它们那种阿兹特卡人
(
古代居住在墨西哥一带的印第安土著居民
)
一般窄小的红脸膛,以及从高挂玻璃缸上方的说明牌上,早就知道了。我看到词典上说,这种蝾螈,非洲也曾经发现。旱季能在陆地生活,雨季一到,复回水中谋生。我还查到了它的西班牙文名称,叫做“
ajolote
”(阿霍洛特);那词条提到,美西螈可供食用,其油可与鱼肝油同样服用(虽说可能不太普遍)。

专业书籍我不打算去查考了,不过第二天我又到植物园去了一趟。从此,我每天上午都去,只是有时早点有时晚些。水族馆看门人在收票的时候,总是笑嘻嘻的,带着一种令人迷惑的神情。我呢,则扶着围在玻璃缸前的铁栏杆,观赏起来。这一举动,不足为怪,因为打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休戚与共,一种消失殆尽而且相隔遥远的东西仍然把我们维系在一起。那天早晨,我头一回站在玻璃缸前,看着水里冒着一个个气泡,就足以证明这点了。美西螈挤在玻璃缸里那块又小又窄的泥土上和苔藓里(只有我才知道,那是多么的窄小)。一共有九条美西螈,它们大多把脑袋贴着玻璃,黄金般的眼睛打量着走近的人们。我居然不顾羞耻,对这堆悄然无声、纹丝不动地拥挤在玻璃缸里的角色探头伸脑,不禁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脸上一阵发烧。我心里默默地把呆在右边、有点儿离群的那条美西螈单独隔开,仔细观察。我看到它身材纤细,粉红透明(我立时想起乳白色的中国小瓷人来),活像一条十五厘米长的小蜥蜴,后面拖着一条玲珑剔透的鱼一样的尾巴,这也好比我们人体感觉最灵敏的部位。它脊梁上长着一道透亮的背鳍,横贯而下,跟尾部融为一体。但更使我倾倒着迷的是它那几只脚,真个是小巧玲珑,指甲纤纤,跟人长得一模一样。当然,它们并非仅仅形状酷似。然而,过去我怎么一无所知呢?也就是在那会儿,我才发现它的眼睛以及它的脸庞。它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除了一对眼睛之外,就没有别的特色了。那对小窟窿般的眼睛,像大头针的针头那么大小,黄金似的透亮,却毫无生气。然而一个劲儿地瞧着,像是要透过我的目光看穿我的心思;而我的目光又似乎正穿过这黄金似的小窟窿,消失在清澈而内在的神秘之中。一条细长乌黑的环带围着眼睛,使其深深陷进粉红色的肉里,嵌在粉红色的、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三角形脑袋上。脑袋周围,线条却弯弯曲曲,很不规则,活像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斑驳剥蚀的一尊塑像。嘴巴被扁平的三角脸遮盖住了,只是从轮廓看来,还能估摸出它的相当可观的大小。从正面望去,美西螈的脸庞似乎有点微豁,像是雪花石膏上划了一道口子。脑袋两侧,也就是在那可能长过耳朵的地方,长出三根珊瑚似的红枝权,那是一种植物赘疣——我猜想,那就是外鳃吧。那是它仅有的富有生气的部位,每隔十秒或十五秒钟,这些小枝权硬邦邦地支棱起来,随即又耷拉下去。有时候美西螈动动腿,我就可以看到它细小的脚趾轻轻地踩在苔藓上。我们观看的人都不太爱动,而水族馆又那么窄小,只要稍微一动,互相之间不是碰了屁股就是撞了脑袋。于是乎行进就难乎其难,打架吵嘴接连不断,最后落得精疲力竭。要是我们个个安分守己,莫非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吗!
我第一次看到美西螈的时候,它们那种安详自若的神态就把我给迷住了。我仿佛隐约地感到我理解它们内心的奥秘。那就是,用一种旁若无人的凝止状态来打破这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后来我更加明白了,它们那外鳃的收缩,细小的四足在石块上的探索,以及它们之中有几条突然纵身在水中的一跃(它们游水左不过是躯体的蜿蜒曲伸而已),原来都在向我证明它们是有能力摆脱那消磨岁月的地穴里的昏睡状态的。在它们一旁的其它几个玻璃缸里,五花八门的鱼儿向我显示着它们长得跟我们一样美丽的眼睛,然而却透出一股傻气。美西螈的眼睛告诉我,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察事物还有另一种方式。我把脸贴近玻璃(有时候看门人惴惴不安地咳嗽起来),想把那些黄金似的小圆珠子看个仔细。那可是进入这些粉红色的小生物漫长而遥远的世界的大门啊!在它们面前,用手指敲击玻璃是徒劳的,它们永远也不会有丝毫反应。它们那黄金一般的眼珠子依然闪耀着柔和而炽烈的光芒,依然莫测高深地瞧着我,把我看得晕头转向。
但它们离我确实很近。这是我以前,在我想变成美西螈以前就知道的,是我第一次接近它们那天知道的。我和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认为猴子酷似人类的外貌正好显露出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美西螈和人类毫无共同之处,恰巧证明我的观察极有价值,并非仅仅依据简单的推理。只是那几只小爪子……但是小蜥蜴不也有这样的爪子吗,跟我们可一点儿也不相象呀。我认为,跟我们不相象的是美西螈的脑袋,长着黄金似的眼珠子、粉红色的三角形脑袋。可它会观察事物,知情通性,会呼唤鸣叫。它们并不是单纯的“动物”。
看样子,这似乎很容易,几乎很明显地会变成神话故事。我在观赏美西螈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开始变形,但怎么也消除不掉那神秘的人性。我想,它们是有思想意识的,尽管身不由己,命中注定要囿于深海一般的沉寂,命中注定要陷入一种毫无希望的冥思苦想。它们那种呆滞的目光,毫无表情然而却炽烈地闪烁着光芒的黄金似的小圆珠子像是传递一种信息一样直射我的心田:“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吧!”我惊诧不已,一面喃喃地讲着安慰它们的话语,传递给它们微薄的希望。它们依然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忽然间,它们的外鳃的粉红色小枝权支棱了起来。这时候,我感到一阵隐痛。也许它们看到了我,而且正奋力获取我那股力争进入它们生平不可侵入的领域的力量。虽说它们并非人类,但我从未在任何其它一种动物身上发现和我有着如此深厚的关系。美西螈好比某种事情的见证人,有时候又像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法官。在它们面前,我感到自己卑微低下,它们明亮的眼睛惊人的纯洁。它们虽是幼体,但幼体即外壳之意,亦可作幽灵解。在这些冷漠的、甚至严酷无情的阿兹特卡人般的脸庞后面,即便到了死期,还会有一副什么样的模样?
我害怕它们起来了。我认为,要不是我感到别的游客和那个看门人近在咫尺,我是决不敢呆在它们面前的。“您简直恨不得要把它们生吞下去呢!”看门人笑着对我说。他准在心里琢磨,我这人精神有点儿失常吧。他决没有觉察到,是美西螈睁着黄金似的眼睛在这个吃人肉的勾当中慢慢地把我活剥生吞下去的。我远远地离开了水族馆,可心里一个劲儿地总琢磨着美西螈,似乎隔了一段路,它们还在对我施加影响。于是我每天都去,而一到晚上,我总觉得它们纹丝不动地呆在冥冥之中,然后慢慢地向前挪动一只小爪子,蓦地,又看到另一条蝾螈的爪子。就是深更半夜它们的眼睛没准儿也能看清楚东西,大白天更不在话下了。美西螈的眼睛是没有眼皮的。
现在我知道这不足为怪,这类事情本该发生的嘛。每天早晨,在我俯身玻璃缸的时候,我观察得就更加清楚了。它们在水底下忍受着严酷的折磨,我肉体的每根纤维都感受到它们这默然无声地忍受着的苦楚。它们在搜寻着什么东西,搜寻着那早已消逝了的、被摧毁了的统治,搜寻着那自由的时光,那时候,整个世界都是美西螈的天下。它们那顽石一般不动声色的脸庞终于按捺不住,露出了痛苦的痕迹,这证明它们忍受着外界的刑罚,挣扎在水底地狱里。我自己觉得,对于美西螈,我有一种无形的感情,不过要证实这一点却是徒劳的。我和它们全都明白。所以,发生了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我的脸紧紧地贴住玻璃缸,眼睛企图洞察那些既没有虹膜、又没有瞳孔、黄金般的眼珠子里的奥秘。我紧挨着一条贴着玻璃的美西螈的脸庞看着。我毫不畏惧地一眼望去,只见我的脸贴着玻璃,不是美西螈,倒是我的脸贴着玻璃,我看到自己的脸在玻璃缸外面,在玻璃的另外一边。于是,我把脸挪开,也终于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只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我还能像过去那样继续思索,知晓事理。察觉到这一点在最初那一刻就仿佛被活埋的人知道面临厄运那样毛骨悚然。在玻璃缸的那一边,我的脸又贴近玻璃,看到我由于想尽力理解美西螈而双唇紧闭的嘴巴。我已变成一尾美西螈,我这才知道不可能还有别的理解。“他”在玻璃缸之外,“他”的思想只是玻璃缸之外的思想。我一面了解“他”,就是“他”本人,而同时又是一尾美西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由于我确信自己已经身为美西螈,带着人的思想附在美西螈身上,活活地埋在美西螈里,命中注定要神智清醒地在无知无觉、麻木不仁的生物之中活动,我感到毛骨悚然,这是我在最初那一刻就感受到的。但是等到一只爪子迈过来蹭了蹭我的脸,这种恐惧的心理就烟消云散了。我刚刚向一边挪动,就看到一条美西螈紧挨着我,盯着我瞧,我知道原来它也知晓事理,我们虽然不可能沟通思想,然而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我就附在它身上,或许,我们大家就像一个人那样思考,不善表情,只有眼睛发出金黄的光芒,直勾勾地盯住贴近玻璃缸的人的脸庞。
“他”又来了好几次,可现在来得少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有露面。我昨天看到了“他”,“他”瞧了我好长时间,又匆匆离去。我感到“他”似乎对我们不怎么感兴趣,似乎要遵循一种什么习惯。我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思索,对于“他”我就能想得很多。我想,我们之间开始还是互相交流思想的;我想,“他”一定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和使“他”入迷着魔的神秘东西联系得更加紧密了。但是我与“他”之间的桥梁却被切断了,因为“他”过去之所以着魔入迷,也就是现在变成一条美西螈,和“他”作为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我认为我最初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复“他”的原状的——是啊,只是以某种方式——,能够对“他”打算更好地刺探我们的企图保持警惕。我现在彻头彻尾地变成一条美西螈了。如果说,我仍然能像人一样思索,那仅仅是因为美西螈尽管有着一副粉红色石头般的外表,却都能像人一样思索。我觉得,在最初的日子里,当我还是“他”的时候,把这种种情况已经向“他”作了若干交代。在这最后的孤寂的时刻,“他”已经不复返回了,我想,“他”也许会写写关于我们的事,认为只需编个故事,便能把关于美西螈的一切境遇统统写出来。我想到这一点,便感到莫大的安慰。
原载于世界
文学丛刊第八辑《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1982)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
相关阅读:
第一读者|胡里奥•科塔萨尔【阿根廷】:妈妈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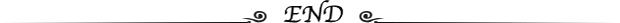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