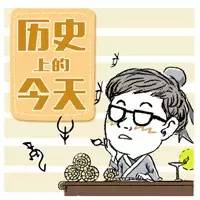图/《黑镜》
拉黑,是一个哲学问题。
/
文|
阿饼
来源|
新周刊(ID:new-weekly)
开门见山,喜欢就处,不行就分,喝点热水,重启试试。
豆瓣网上有一个“史上最沉默小组”,创建于2007年1月5日,成员有23482人。迄今为止,没有人发表过一个小组话题。
在众多聊天软件中,有一个功能是不能随便加的:“已读”。如果非要加的话,应该再推出“已读已读”功能,让对方知道我已经看到了你“已读”了,然后再“已读已读已读”……很好,中间再插入“对方正在输入”“对方已撤回”“评论已删除”……无需多说,就可以通过对方“已读”几遍、等待“正在输入”多长时间等判断对方对自己的重视程度了。
热文《新世纪社交礼仪》中列举了实用的词例:如何表达笑?——“呵呵”是想挑事,“哈哈”意味着“滚”,“哈哈哈”是“好无聊”,“哈哈哈哈”是敷衍。想表达真的好笑,就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叠词越多越好。当然也不能多到刷屏,那是另一种搞事。
在如今的日常社交中,这样的“潜规则”还有很多。幼儿园级别的词汇,甚至不需要任何言语,却蕴含了更耐人寻味的表达。不过,不懂、搞错了也没关系,喜欢就处,不行就分,喝点热水,重启试试。
“轻社交”下的朋友圈没有朋友
心理学家乔治·莱文杰(George Levinger)提出人际关系发展的五阶段模型:相识/吸引、关系的建立、加固/延续、恶化、终止。
互联网时代虚实结合的“轻社交”将这个过程大大简化、缩短——用最少的精力去维护一段并不深厚的感情,是通信技术和生活方式进步的必然结果。它固然使得我们联系朋友的方式更加多样更加便捷:懒得打字、抽不开手的时候发段语音,不想电话打扰可以等对方上线收阅后再回复,而且还不用话费,确实比传统的电话加短信模式方便很多,这些交往方式悄悄成为年轻一代的主导人际模式。
工信部2014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2.35亿人使用移动通信服务。从台式机的MSN和QQ时代到移动微信时代,“你好,在吗?”已经成为最容易引起警戒心的开场白。我们越来越礼貌。没有特别正式重要的事情,一般不用见面聊天;没有特别紧急繁琐的事情,一般不用电话;短信已成为快递员、银行信息和垃圾小广告的阵地。
每个人的手机里通常有至少一百多个电话号码,几百个QQ、微信好友,通过“扫一扫”“摇一摇”“约”“附近”“左滑右滑”等快消社交,还能更轻松地获得新的社交对象。当对方通过你的好友请求后,从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到友尽的最后一句话,再加上取关对方所有的社交媒介,可能不需要活太久就能有幸见证。这种友谊关系是如此虚幻却实在。

虚拟世界的“好友”数量不断增加,但真正的朋友有几个?图/《黑镜》
我们经常联系的人不会超过十个。“朋友圈”有了字面意义以外的许多定义:五花八门的微店代购、早已不再联系的同学、为工作所需而添加的陌生人、名存实亡的群聊,还有45°仰望着你的大头自拍、每天背单词的打卡截屏、没人点开的小视频、来源不同的公号文章分享……
不过,相比真实生活的种种人际问题,这些五花八门的存在造成的困扰并不算大,甚至会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娱乐性所在。
心情好,你可以轻松地给予反馈——点赞和评论;心情不好,你可以视而不见或设置屏蔽。毕竟我们都在同一个表演剧场,互相成就了一个貌似热闹的自我世界的中心。这些反馈与被反馈的互动变成了一场有意的展示,多少有些虚假性。但在虚拟世界里,这种虚假显得很真实。

虚拟时代的社交关系有点假。图/《她》
“轻社交”又拓展了你的关系网与世界观
“轻社交”即superficial social interecourse,直译就是“肤浅的社交往来”。这不像贬义词。
《群体性孤独》作者、社会学家雪莉·特克认为,我们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对社交媒体上形成的关系的认识和维护,还处在婴儿期。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如何有意识、有意义地与人互动。在她看来,这种保持多线程的“轻社交”,是我们对掌控的渴求,“我不会过度专注于某一段关系,我随时有很多退路”,本质上是寻求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