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自二十五岁那年携
《白牙》
一举震惊文坛后,如今的
扎迪·史密斯
(Zadie Smith)俨然成为英国青年一代作家的代表,以其讽刺幽默的文风、节奏鲜明的叙事、丰富的语言表现力捕捉着隐藏在当代社会庸常生活背后繁杂的冲突与隔阂,并被推举为“种族、年轻、女性”的代言人。然而,除了出众的写作能力,她还是一个敢言善论的批评家、一个流行文化的关注者、一个针砭时事的通讯作者……简言之,你绝不能简单地用她的小说去定义她。
|
|

本文原载2016年11月20日的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原题为
《扎迪·史密斯谈种族、女性与文学创作》
,首发于公众号“
上海书评
”(id:shanghaishuping),转发已获授权,在此表示感谢。
|
我们需要寻找身份认同,但没那么重要
——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专访
文|
张芸
- 声明:如需
转载先请
私信联系
-
上海书评:
您的小说
《美》
和
《西北》
新近出了中译本,根据这两本书的创作时间,我们先聊一聊
《美》
。它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大波士顿地区,您恰好曾在哈佛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请问,这本小说与您本人的经历有怎样的关系?
史密斯:
我开始在拉德克利夫(Radcliffe)研究院,那以前是一间女校,后来到哈佛待了一年,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要说里面最有自传色彩的元素,应该是雪,到处是厚厚的积雪,这些雪自然被我写进了小说。但更具体来讲,小说里的故事素材更多来自另一个剑桥,英国剑桥。我对学术生活的许多感想源自我在英国剑桥的经历,而不是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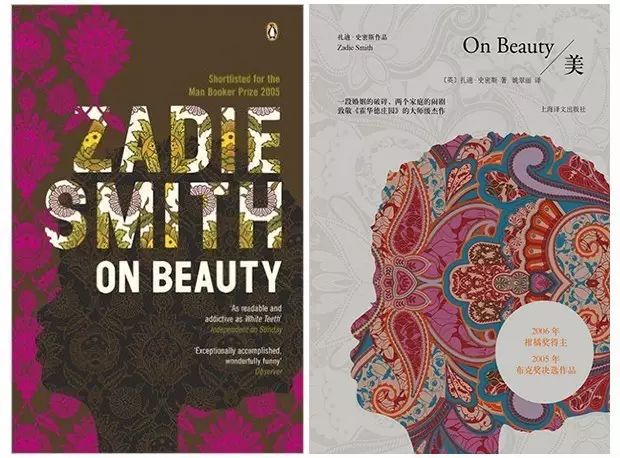
《美》(On Beauty)
英文原版和上海译文出版的简体中文版
上
海书评:
原来如此。您是英国人,也在美国的几所大学教授小说写作,从您的角度看,美国的大学生活和英国的有什么不同?
史密斯:
我觉得现在来讲,两者变得越来越近似。但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在英国,大学是免费的,在那种条件下,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与现在不同。教授在我心目中是相当崇高、高贵的,他们的薪水不丰,但却有着卓越的学识和才华,因此,和他们的关系,有点类似和牧师或医生的关系。而在美国,大学和钱密切挂钩,学费很高,所以师生关系更倾向于服务性质,我为这些学生打工,因为他们付钱来上学,让我有薪水。
上海书评:
小说《美》刻画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观念冲突。有调查显示,近一二十年来,大部分美国大学的教授支持和认同自由派,在英国也是一样的情形吗?
史密斯:
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我应该属于自由派,但我不愿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我知道眼下,在许多大学的保守派中间,存在一种害怕自由派大行其道的恐慌,例如在纽约大学,这种情况特别显著。从一个角度讲,人道主义的部分观点与自由派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开明和争论的相对性,所以人道主义从本质上讲是自由主义,这一点很难反驳。但我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对各种不同的观点,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的信念,保持开放的态度,注意到学生可能持有的不同理念,避免让我的教学变成说教。
上海书评:
小说里有一位主人公是受邀到美国担任访问学者的英国教授,这种局外人的身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更容易在美国大学里发出保守派的声音?
史密斯:
说到蒙蒂,我觉得他算不上是一个真正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更像是个异议分子,他只是非常看不惯自由派,他的反应其实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天生具有反对派的个性,他讨厌仅因为他的种族背景他就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预设,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叛逆,他想要做的是颠覆人们对他的期许。所以,我不觉得他有多么保守,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个喜欢质疑、反抗的挑衅式人物。
上海书评:
在小说里,还有一些人物,总在努力寻找归属感,比如霍华德的儿子利瓦伊,他喜欢和贫民区的黑人男孩混在一起,觉得自己同他们更亲近,而抵触他生来所属的那个精英世界。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
史密斯:
我笔下的人物通常和我自己是不一样的。就我本人来讲,“我是谁”、“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人”,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我觉得有比它们更重要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的确,作为人,人们对你有一个印象和定位,如果在别人眼里找不到对你的定义,那是成问题的。但当你在他人眼中有了明确的身份和定位后,我认为,这并不能解决人生中实际遇到的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一个开端。所以,我虽然相信我们需要寻找身份认同,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没有那么的重要。
上海书评:
您自己有过这方面的身份困扰吗?
史密斯:
没有。我不是那种经常思考我是谁或我不是谁的人,虽然我塑造的人物时常受困于其中。我可以说我自己是英国人、黑人、女人,这些是客观事实,但这些事实对我起不了太大帮助,不能教会我怎么在这个世上生存和立足。我觉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立足才是更基本的、超越“你是谁”的存在问题。
上海书评:
这部小说的标题叫作“美”,似乎含有一层反讽意味,因为小说里的故事有时并不那么美好。尤其到结尾的高潮,局面几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活像一出闹剧,令人发噱。能否请您谈谈这种喜剧元素在您作品中的分量和作用?
史密斯:
我觉得喜剧是一种美。我明白,从严格意义上,喜剧缺少升华的特质,但我认为,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喜剧是具有美感的。因此,对我而言,很难在作品中不掺入喜剧元素。换句话说,喜剧是我感受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角度,我曾颇为努力地试图遏制我作品中的喜剧色彩,但后来放弃了,因为我发现这是我创作中与生俱来的元素。我的一个弟弟是表演单人喜剧的,所以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家的遗传吧。
上海书评:
去年,我有机会翻译了奇玛曼达·阿迪契的小说《美国佬》,这本书给了我全新的视野,让我认识黑人。书中的主人公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她说,她到了美国才意识到自己是黑人。您出生在伦敦,您的母亲是牙买加人,父亲是英国人,能否请您聊一聊,作为一个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在英国成长的经历?
史密斯:
我的经历和奇玛曼达不同。我始终知道我是黑人,那是我周围的世界给我的定义。当我后来去西非的时候,我能完全体会她笔下主人公那番话的含义,感受到自己不是众人中的一员。我觉得这种感到自己与周遭人不一样的经验,发生在每个走入陌生环境里的人身上,我猜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也有类似的感受,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他者。不过,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认识自己的视角,把自己放在彻底异类的位置上,从历史角度讲,各方面,不同的背景、属性,追溯到不同的血统乃至人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立场。
上海书评:
当一个别人眼中的他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
史密斯:
我向来认为,人活在世上是不容易的。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但这些难处通常源于感觉自己被人误贴标签,感觉别人不了解自己或了解得不够,换言之,问题总是由外而来,加诸你身上,而不是你本身所有的。就我自己来说,我想我总是怀着一种好奇,想知道自己可能是个怎样的人。
上海书评:
现在您住在英美两地,请问,在美国和英国,黑人的处境有所不同吗?
史密斯: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确不一样。首先,历史根源不同,黑人最早以奴隶身份踏上美国这片土地,这与从殖民地移民宗主国的方式截然不同。具体来讲,黑人在美国和英国的境遇千差万别,各有优劣,但有一点我更欣赏美国:人们公开明确地讨论种族问题,我觉得这比遮遮掩掩强。
上海书评:
继《美》之后,您创作了小说《西北》。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与《美》迥然不同,以碎片拼贴、非线性时间的方式组织故事。一般来说,您是怎么确定一部小说的叙事手法和形式的?
史密斯: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很难给出理性回答的问题。好比绘画,一个画家从风格上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如蓝色时期、红色时期、抽象时期、具象时期,但若问那个画家,为什么这幅画是蓝色,那幅是红色,他恐怕难以给出理性的解答。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主题决定形式;另一方面,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重复同样的写法,我会厌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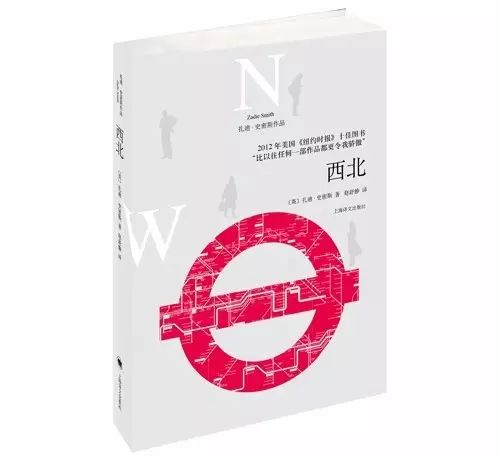
《西北》
上海译文2015年4月出版
上海书评:
所以是有故事在先?
史密斯:
那样说也不对。通常在写一本小说时,我并没有计划好的故事大纲。通常我有的是一个细微、模糊的想法,然后我会尝试寻找一定的笔调、口吻去表述。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久、很艰难,但一旦找到准确的调子后,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就像画家,在画第一笔前,要在调色板上找到准确的色调,那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上海书评:
在《西北》里,主人公利娅是她工作团队里唯一的白人,这令我想起《美》里面的琪琪,在和她丈夫的朋友、同事聚会时,察觉到自己是众人中唯一的黑人,因而感到不自在。这种隔阂,似乎是您小说要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
史密斯:
绝对是。我认为,当人们在一个环境里感到不自在或无法完全融入时,那提供了一个可发挥的创造性空间。当你和一个环境完全融合、在里面如鱼得水、没有丝毫距离感时,你不大会对很多东西提出质疑,一种怠惰会在头脑里油然而生。只有当你置身于一个与你不相容的环境时,比如白人在非洲,当他们第一次发现或体验到自己是少数族裔时,那常常会引发相当有趣的思考,是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有益的心态,让人对事物、对现实更投入。
上海书评:
所以对小说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故事素材。
史密斯:
是的。我自己有过很多这类隔阂的经验,那为创作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去想象或突然间意识到一切都不是注定或必然的,人生的种种取决于当下的情况,完全存在另外的可能,对我来说,这是创作小说的原动力,即探索事情的多种可能性。
上海书评:
小说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娜塔莉 / 凯莎,竭尽全力挣脱她原本的出身,可她的成功,在她的家人眼中却被视为某种背叛。您觉得,这是想要出人头地者经常会面临的两难境地吗?
史密斯:
据我的观察,以纽约为例,在很多新的华人移民家庭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子女一辈融入美国的生活,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在事业上取得不小的成就,但他们的父母依旧保持着他们刚来时的状态,他们可能不讲英语,对他们而言,不仅与自己的祖国分离,也和他们的子女分离,这是一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难想象的经验。在你接受教育的同时,却和你的家人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变得像陌生人,这种境况,想来是匪夷所思的。从父母的角度讲,这是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他们为了孩子的前程而献出了自己与孩子间的纽带。这不是一种容易相处的关系,我觉得这里面藏着几分动人而哀伤的味道。
上海书评:
的确,这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别的小说里,比如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新书《我叫露西·巴顿》(My Name is Lucy Barton),讲一个家境贫寒的姑娘长大后成了知名作家,但与家人的关系疏离紧张。
史密斯:
我知道,我等不及要读这本书。诚然,几乎每个工人阶级背景出身的作家身上,都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狄更斯式的故事。当你积极投入创作时,你与你的家人从根本上分道扬镳。以我自己为例,我的父亲从未读过我的小说,这是一种颇耐人寻味的感受,不一定就是残酷无情,只是你不可能、没有办法建立那座联结的桥梁。
上海书评:
在小说里,利娅和娜塔莉相信,大家都认为她们应当生儿育女,娜塔莉按人们的期许照做了,而利娅始终犹疑不决,这一分歧给她们的友谊蒙上了阴影。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普遍的认为女性应当为人母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