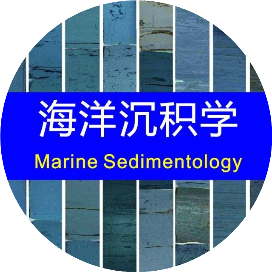主要观点总结
文章主要研究了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揭示了两种(迟滞和瞬态)深水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与反馈机制。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主要发生在宽陆架且无峡谷延伸到内陆架以及冰室气候条件下,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主要受可容空间驱动。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则主要发生在窄陆架、温室气候、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或相邻、断陷湖盆以及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等条件下,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对物源供给更为敏感,主要受物源供给驱动。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文章梳理了深水源—汇系统对从构造尺度到人类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揭示了两种(迟滞和瞬态)深水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与反馈机制。
关键观点2: 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
发生在宽陆架且无峡谷延伸到内陆架以及冰室气候条件下,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主要受可容空间驱动,形成富砂或富泥的沉积响应。
关键观点3: 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发生在窄陆架、温室气候、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或相邻、断陷湖盆以及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等条件下,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对物源供给更为敏感,主要受物源供给驱动。
关键观点4: 气候变化与深水源—汇系统的响应
气候变化能够调控沉积物在外陆架—深水盆地的搬运—分散—堆积过程,但具体响应机制取决于源—汇系统的类型和信号的尺度。
关键观点5: 研究意义与应用前景
研究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有助于揭示油气资源沉积、预测环境灾害,以及为非常规油气资源分布提供预测依据。
正文
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与反馈机制
龚承林
1,
2
 齐昆
2
徐杰
3
刘喜停
4
王英民
2
齐昆
2
徐杰
3
刘喜停
4
王英民
2
1. 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 102249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北京 102249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洋学院,北京 100083;4.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摘 要
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是当前深水沉积学研究的前缘和新动向。通过梳理外陆架—深水盆地沉积物搬运分散系统(深水源—汇系统)对从构造尺度到人类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揭示了两种(迟滞和瞬态)深水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与反馈机制。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的过渡区较宽、响应尺度较大(
T
eq
≥10
4
年),有利形成条件为:宽陆架且无峡谷延伸到内陆架以及冰室气候;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主要受到可容空间的驱动(吻合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在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中,构造—轨道尺度的冰室气候期浊流活动较强、形成的沉积体相对富砂,温室气候期浊流活动较弱、形成的沉积响应相对富泥;而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常被快速海平面上升所“淹没”、不能调控深水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瞬态响应源—汇系统过渡区较局限、响应尺度较小(
T
eq
≤10
4
年),有利形成条件有:窄陆架、温室气候、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或相邻、断陷湖盆以及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对物源供给更为敏感,主要受物源供给驱动(偏离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在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中,不论是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还是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只要其能够诱发物源供给的变化(而不论可容空间是上升还是下降),都能够对深水源—汇过程响应进行调控。
关键词
深水沉积;气候变化;层序地层学;迟滞响应源—汇系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从剥蚀区形成的沉积颗粒进入被称之为由源到汇的系统中并最终沉积下来的源—汇系统研究”(
图1a
)
[
1⁃9
]
和“从沉积记录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的地球古气候变化及重大地质事件并为未来气候预测提供依据的古气候研究”不仅是许多重大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中国沉积学发展的战略方向
[
9⁃12
]
。围绕“源—汇系统”国内外许多重大地球科学计划设立了长期性的研究课题,譬如“大陆边缘科学计划”、“大陆边缘地层形成机制”和“台湾高屏峡谷的沉积物宿命研究”等;而“古气候”是“地球—生命转变研究计划”和“中国陆相白垩纪科学钻探高分辨率古环境记录与古气候演化”的核心科学问题。
图1
(a)源—汇系统组成要素;(b)不同研究手段的适用范围;(c)不同类型气候信号的响应尺度;(d)不同记录载体的时间尺度和分辨力(据Ruddiman
[
13
]
修改)
近年来,随着研究手段的革新(譬如CT连续扫描成像和深海浊流观测等),人们愈发意识到在亚轨道和年际尺度内,气候波动(譬如台风、厄尔尼诺等)也能够启动沉积物由源到汇的搬运分散过程(
图1
)
[
13⁃15
]
。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学者Brian Romans教授、Andrea Fildani博士和Angela M. Hessler博士等人提出了“气候沉积学(Climatic Sedimentology)”的研究计划
[
14
,
16⁃18
]
;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资助实施的智利陆缘102,156和161航次也以“气候变化的深水沉积响应”为核心科学问题
[
19⁃21
]
。此外,国际沉积地质学会2020年沉积地球科学国际会议设置了“沉积记录中的气候变化”分会场,并得到了高度关注。
不难看出,揭示多尺度气候变化是如何调控沉积物在外陆架—深水盆地的搬运—分散—堆积过程是当前沉积学领域的热点和新动向,并将有望在今后的数年内取得更大的进展
[
3
,
6⁃8
,
14
,
17⁃18
]
。这一科学命题的内涵是利用沉积、地层和地化手段解译多尺度气候变化对沉积物由源到汇的剥蚀—搬运—分散—堆积过程的调控作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具体来说,地球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比现在更温暖的温室气候期(地质历史时期中温室气候约占72%,而冰室气候约占18%),目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正在从一个“不太寻常的冰室气候期”进入“寻常的温室气候期”,这迫切需要科学界全面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层系统(譬如深水浊流)所产生的环境效应
[
10
,
12
,
22
]
。此外,全球深水油气资源依然是未来世界油气勘探的主战场,在全球925个已发现的浊积岩油气藏中有43个油气田的原油当量超过了50亿桶
[
23
]
;而巴西外海已发现油气储量的约87.5%来自深水浊积岩。更为重要的是,陆相深水湖盆有利于非常规油气资源沉积富集
[
24⁃25
]
,孕育了数个10亿吨级致密油、页岩油大油田
[
26
]
。揭示深水沉积的沉积特征(如岩性、厚度和规模等)对气候变化(事件)的沉积响应可从成因上探讨优质储层发育机制,为有利储层、非常规油气甜点区(段)与资源分布预测提供依据,将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
24⁃25
]
。
以外陆架为界可以将由陆到洋的源—汇系统划分为“物源区—内陆架”和“外陆架—深海盆地”两个次级源—汇系统(
图1a
)。本文无意对“由陆到洋的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这一领域作全面论述,而聚焦在外陆架—深水盆地子系统(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和反馈机制,仅就该领域内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和笔者的一些思考作简要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由陆到洋的源—汇系统一般由物源区、过渡区和沉积区构成(
图1a,图2
),过渡区对环境信号具有非线性的过滤作用,换言之“并非所有的气候信号,如今日刮风、明日下雨的高频低幅天气变化都能够被深水源—汇系统响应”
[
6
,
8
,
14
]
。基于此,我们将“过渡区对气候信号的过滤,使其破坏甚至消失,从而不被深水源—汇系统所响应的效应”称之为源—汇系统的滤波效应(
图2
)。

图2 可容空间驱动的缓冲响应源—汇系统(a)和物源供给驱动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b)的组成要素
过渡区对气候信号的滤波效应取决于信号的时间尺度(
T
p
)与系统响应时间(
T
eq
,是指沉积物分散系统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所需要的时间)之间的大小关系。自然界存在4种尺度的气候信号:边界地质条件长期变化引起的百万年跨度的构造尺度(
T
p
= 10
6~9
年),太阳辐射变化驱动的十万年跨度的轨道尺度(
T
p
= 10
4~5
年),几百到上万年的亚轨道尺度(
T
p
= 10
3~4
年)和年代际以及更短时间跨度的人类尺度(
T
p
≤10
3
年)(图1c,d)
[
27⁃28
]
。当“
T
p
≥
T
eq
”时,气候信号能够被沉积纪录所记载;而当“
T
p
≤
T
eq
”时,气候振荡往往在沉积物分散系统中被“淹没”
[
26
]
。据此,我们将不能响应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信号(
T
eq
≥10
4
年)的深水源—汇系统称之为“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
图2a
),而将能够响应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信号(
T
eq
≤10
4
年)的深水源—汇系统称之为“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
图2b
)。
以下两种地质背景条件使得积物分散系统的过渡区较宽,响应尺度较大(
T
eq
≥10
4
年),常常不能对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做出响应,形成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2a
)。
(1) 宽陆架(≥50 km)且无峡谷水道延伸到内陆架:如果陆架的宽度≥50 km,且无峡谷水道切割陆架坡折并延伸到内陆架或河口;这样的源—汇系统往往发育一个较宽的沉积物过渡区(譬如图3a所示红河和珠江源—汇系统),而过渡区犹如信号滤波器一般,能够对母源区的气候环境信号进行滤波;从而将那些如台风、洪水等高频(≤10
4
年)低幅的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信号过滤掉(
图2a
)。母源区的气候信号会迟滞、破损,甚至不被深水沉积所响应,形成“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2a
)。世界上绝大多数被动陆缘,常发育一宽阔且平坦的大陆架(如图3a所示的珠江和红河源—汇系统),多为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3 (a)地貌图示意了南海北部陆缘形成发育的红河、珠江和高屏三大源—汇系统以及图3b,5a,11a和13a的平面位置(地貌图由曹立成博士提供);(b)~(d)地震和钻井剖面(剖面位置见图3a)示意了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源汇系统的剖面地震反射特征和岩性特征
(2) 冰室气候:在冰室气候背景下,冰盖和冰川广泛分布、全球气温大幅度降低,而海平面也以高频(10
1~2
次/千年)高幅(10
1~2
m)的升降变化为主(如上新世—更新世的海平面变化)。冰室气候期高频高幅的海平面变化所诱发的快速可容空间上升使得源—汇系统的响应尺度往往比较大(
T
eq
≥10
4
年),能够对高频(≤10
4
年)低幅的气候信号进行滤波、屏蔽,形成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2a
)。
以下五种地质条件使得积物分散系统的过渡区较为局限,响应尺度往往也比较小(
T
eq
≤10
4
年),能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做出反馈,形成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图2b
)。
(1) 窄陆架(≤20~50 km):当陆架宽度较窄时(如活动陆缘),源—汇系统的过渡区往往较为局限,从而导致亚轨道和人类尺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如D/O事件、厄尔尼诺和热带气旋等)能够被深水沉积所迅速反馈和响应。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的典型实例有南加州活动陆缘的Santa Ana和Santa Clara源—汇体系
[
14
,
29
]
,智利活动陆缘
[
19
,
21
]
,北阿尔及利亚Bejaia地区的Soummam Oued峡谷
[
30
]
,菲律宾外海的Malaylay峡谷
[
31
]
、坦桑尼亚陆缘
[
32
]
和东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湾
[
33
]
。
(2) 温室气候:与冰期气候条件显著不同的是,温室状态下南北极冰盖退缩、地球气候更加温润,而海平面也以低频低幅升降变化为主(如晚始新世—早渐新世和晚白垩世—早古新世海平面变化曲线)。低频低幅的海平面升降导致的可容空间以下降或缓慢上升为主,源—汇系统的响应尺度往往也比较小(
T
eq
≤
10
4
年),形成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
图2b
)。已有的温室陆缘研究实例也表明温室陆缘一般不发育高角度上升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指示的快速空容空间上升
[
34
]
,在这样的盆地中过渡区往往比较局限。
(3) 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或相邻(≤30 km):当深水峡谷水道的头部和河口相连或相邻时,所形成的源—汇系统过渡区不发育或较局限,形成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亦即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5 km)所形成的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的典型实例有我国台湾的高屏源—汇系统(
图3a
),刚果源—汇系统(
图4a
)
[
35⁃36
]
,加州Monterey峡谷和法国外海的Var峡谷
[
37
]
。峡谷头部和河口相邻(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介于5~30 km)时,过渡区较为局限,形成瞬态响应源—汇系统,譬如恒河—雅鲁藏布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Swatch of No Ground峡谷和河口之间的距离约30 km左右(
图4a,b
)
[
38⁃39
]
。

图4 峡谷头部和河口相邻(图a和b)以及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图c)所形成的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a)中的地形图下载自谷歌,(b)(c)中的地形图下载自ESRI
(4) 断陷湖盆:湖盆一般缺少如海盆那样宽阔且平坦的陆架区,源—汇系统的沉积物过渡区颇为局限,系统的响应时间
T
eq
也就比较小,能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的高频低幅信号做出迅速而快捷的响应,形成常说的“洪水期一片天、枯水期一条线”的瞬态响应源—汇响应格局(譬如江西鄱阳湖)。岷江在洪水期能够将汶川地震所形成的崩塌沉积物迅速搬运到紫坪铺水库
[
40
]
,而阿拉斯加Eklutna湖忠实地记载了1917年、1929年、1964年、1989年、1995年和2012年发生的6次大型洪水事件
[
41
]
,两者都是瞬态响应源—汇系统的典型实例。
(5) 陆架边缘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一般而言,陆架宽度≥50 km且无峡谷延伸到内陆架陆缘常常为迟滞响应源—汇系统。但在高速沉积物供给条件下,陆架边缘三角洲越过先期陆架坡折,从而使得前陆架边缘三角洲与陆坡水道的头部相连(
图3b
)。在这样的地质背景条件下,陆架边缘三角洲和陆坡水道形成了一个闭合而联通的沉积物分散系统,使得河流搬运而来的沉积物即使在海平面上升时也有可能能够被搬运到深水盆地
[
15
]
。
2 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
2.1 构造—轨道尺度(≥10
4
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汇过程响应
珠江口盆地现今陆架宽约100~200 km,陆坡水道终止在陆架坡折处,为一典型的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3a,图5a
)。珠江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忠实地响应、反馈了构造尺度的气候事件(如中中新世变冷事件和中更新世气候革命)和亚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如冰期—间冰期旋回)。

图5 (a)珠江口盆地中中新世区域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3a)和(b)连井沉积相对比剖面揭示了中新世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深水扇源—汇系统的沉积特征(原图由徐少华博士提供)
(1) 构造尺度的中中新世变冷事件(MMC):在中中新世,南极冰盖逐渐扩张并永久性形成,气候也随之显著变冷,这一事件被称之为“中中新世变冷事件”
[
42
]
。这一气候事件使母源区机械风化作用加强,与此同时南极冰盖的扩张导致海平面大规模下降(最大幅度可达80 m)
[
43
]
。大量沉积物(尤其是粗粒沉积物)在中中新世由物源区被搬运到珠江口外陆架和前方的深水区(
图5
),在白云深水区形成一大型富砂的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沉积体系(
图5
)
[
44
]
。在地震剖面上,下降体系域时期海底扇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中振幅、杂乱的反射,而低位体系域时期海底扇在地震剖面上以中—强振幅、连续—杂乱反射为主,多期双向下超特征明显(
图5a
)。在连井剖面上,中中新世珠江海底扇以低伽马、箱型测井曲线响应特征为主;而中中新世的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以漏斗型的伽马测井曲线响应特征为主(
图5b
)。
(2) 轨道尺度的中更新世气候革命(MPT):在中更新世,全球气候变化的周期由 40 ka跃迁为100 ka,这一气候事件被称之为“中更新世气候革命”
[
42
]
。在珠江源—汇系统的深水部分,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自中更新世以来经历了早期进积(MIS 20⁃12)、晚期加积(MIS 12⁃1)的发育演化过程;它们的前方分别发育进积特征和退积特征明显的深水扇(
图3b
)
[
45
]
。研究表明中更新世气候革命之前(MIS20⁃12)冬季风盛行、气候干冷,机械风化作用增强但河流搬运能力较弱,从而导致向珠江源—汇系统供给的沉积物量少但相对较粗(富砂)
[
45
]
。这一时期全球冰量的增加导致高频(41 kyr)低幅的海平面变化(海平面平均高度约为-55.8 m,标准方差为±24.2 m,数据据Miller
et al
.
[
46
]
),从而使得沉积物能够越过内陆架、“驻留”在陆架边缘向深水中输送沉积物的频次增多,形成进积特征明显且相对富砂的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沉积体系(
图3b
)
[
45
]
。中更新世气候革命之后的MIS 12⁃1期,夏季风盛行、气候润湿,化学风化和河流搬运能力相应增强,从而导致向珠江源—汇系统供给的沉积物量多且相对较细(富泥)
[
45
]
。这一时期全球冰量减少造成低频(100 kyr)高幅的海平面变化(海平面平均高度约为-62.7 m,标准方差为±33.2 m,据Miller
et al.
[
46
]
),使得沉积物能够越过内陆架、“驻留”在陆架边缘向深水中输送沉积物的频次减少,形成退积特征明显但相对富泥的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沉积体系。
(3) 轨道尺度的冰期—间冰期旋回:在10
4~5
年尺度的轨道尺度上,气候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冰期、间冰期的周期性出现。陈芳等
[
47
]
认为白云深水区的更新世沉积速率从3.14到5.74 cm/kyr不等;据此推测珠江峡谷的6个柱状样中沉积物的年龄从6.42到21.41 kyr不等(
图6a~e,图7
)。其中如图6b~d所示的柱状样GC19,GC20和GC21中的沙层形成于MIS1和3末次冰期,而如图6a所示的柱状样GC18中的沙层则主要形成于MIS2亚冰期。MIS1和3末次冰期间夏季风增强、气候润湿,化学风化作用和河流搬运能力较强,沉积物供给高
[
49⁃50
]
;高速沉积物供给能够抑制海平面上升将沉积物搬运到外陆架和白云深水区(
图6f,g
)
[
15
]
。在这一高沉积物供给背景下,所形成的陆架边缘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达10~15 km,并和陆坡水道相连接,形成联通而顺畅的由源到汇的沉积物分散系统,使得在海平面上升的间冰期也发育浊积沙(
图6
)
[
15
]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论需要高精度的测年数据来证实或证伪
[
15
]
;这也是笔者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珠江峡谷末次冰期以来浊流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尺度与反馈机制(41972100)”的立题依据之一,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图6 (a~e)珠江峡谷内重力活塞样在冰期和冰消期形成的浊积沙;(f~h)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IS1-12期以来的海平面变化曲线(据Miller
et al.
[46]
)、磁化率曲线(据Guo
et al.
[48]
)和珠江深水浊流活动史
图7 珠江深水源—汇系统沉积区深海柱状样P1(柱状样位置见图3a)的Geotek岩芯扫描照片及其对应点状磁化率和XRF元素分析
此外,更新世亚马逊海底扇碎屑锆石的铀—铅年代学研究表明,在两次冰期(低位期),剥蚀作用强,大量源自安第斯山脉的碎屑颗粒被亚马逊河搬运到深水区,滨线向海进积、亚马逊海底扇活跃发育;而在间冰期(高位期),风化作用减弱,亚马逊源—汇系统由源到汇的沉积物搬运分散能力减弱、滨线轨迹向陆退积,海底扇停止发育
[
51
]
。
2.2 亚轨道—人类尺度(≤10
4
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汇过程响应
尼日尔三角洲盆地陆架宽约50~100 km,陆坡水道终止在现今陆架坡折,为一典型的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在这样的深水源—汇系统中,沉积物在外陆架—深水盆地的分散—堆积过程不能够忠实地记载反馈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变化。在深海氧同位素MIS5时期,尼日尔源—汇系统的母源区以“润湿气候”为主,润湿气候使得母源区的化学风化作用增强、河流搬运能力增强;但宽阔的陆架和同期的海平面快速上升使得润湿气候所造成的供给量增加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从而导致深水水道内浊流活动停止,水道废弃
[
52
]
。在深海氧同位素MIS3时期,海平面下降,使得尼日尔陆坡水道中的浊流活动加剧且富砂
[
52
]
。由此可见,如经典层序地层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沉积物在迟滞响应的搬运分散过程主要受海平面变化的控制,而气候变化对其无明显的调控作用(
图2a
)。
此外,珠江源—汇系统的过渡区(陆架宽约100~200 km)较宽,在如
图7
所示来自珠江深水区的柱状样上,点状磁化率、锆/铷比、硅/铝比的正异常以及钛/钙的负异常与浊流沉积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如何通过多种手段重构珠江峡谷内外的浊流活动史,进而结合
14
C测年,揭示珠江峡谷末次冰期以来浊流活动对亚轨道尺度气候和海平面相互作用的响应机制,将有望在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与反馈机制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3 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
3.1 构造—轨道尺度(≥10
4
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汇过程响应
前已述及,温室气候期低频低幅的海平面升降使得源—汇系统的响应尺度往往比较小(
T
eq
≤
10
4
年),形成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它们忠实地响应了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如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和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
(1)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ETM):在古新世—始新世之交,全球温度在短暂的一万年内陡增了4 ℃~8 ℃,这一全球突然变暖事件被称之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
[
42
]
。Clare
et al.
[
53
]
通过对深水浊流事件的统计分析表明浊流活动的频率在极热事件期间急剧减小,而在极热事件后则显著增加。Egger
et al.
[
54
]
认为浊流的沉积速率在极热事件期间从20 cm/kyr急剧减少到5 cm/kyr;而Schmitz
et al.
[
55
]
研究表明在极热事件期间巴斯克盆地(Basque Basin)浊流活动的频率也减少了10倍。此外,Sømme
et al.
[
56
]
研究表明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使得挪威外海的沉积物供给量相较于极热事件前的Thanetian沉积期显著减少了约10倍。Clare
et al.
[
53
]
将这一“古新世—始新世极热期浊流活动显著减弱”的现象归因于干热的气候条件,认为干热的气候导致河流搬运能力减弱,供给到陆架边缘的沉积物也相应减少;并最终使得沉积物在深水中的搬运—分散过程也较弱。
(2) 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EOGM):在始新世晚期—渐新世初期,环南极洋流阻止了南极底层水与赤道地区水体之间的交换,从而使得南极大陆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冷,形成大规模冰盖,这一事件称之为“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
[
42
]
。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所导致的气候明显变冷也被鲁武马盆地渐新世(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海底扇所纪录。具体来说,在如图8所示的东非渐新统连井剖面上,1井和5井暖水种浮游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的丰度显著降低,是渐新世初大冰期变冷事件作用的结果
[
57
]
。相较于以灰绿色泥岩为主的始新世海底扇,渐新世初大冰期形成的海底扇以中粗砂岩为主;这一海底扇岩性变化可能响应于寒冷干燥气候(
图8
)
[
57
]
。干冷的气候使非洲大陆机械风化作用加强,并伴随着海平面急剧下降,从而导致更多的陆源物质(尤其是粗粒物质)由源到汇输送搬运到鲁武马深水区,形成富砂的海底扇(
图8
)。

图8 鲁武马盆地区域连井剖面(陈宇航等
[57]
,修改)及其与古气候事件(Zachos
et al.
[58]
)的对应关系
3.2 亚轨道—人类尺度(≤10
4
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汇过程响应
与前已述及的“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响应模式”不同的是,瞬态响应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记录了亚轨道—人类的气候波动。
(1) 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波动的响应:在以下四个典型的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如厄尔尼诺、Dansgaard/Oscheger事件、Bølling⁃Allerød事件、强台风和风暴)对沉积物在深水中的搬运分散过程有着明显的调制作用。
在南加州Santa Ana和Santa Clara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陆架宽约5~30 km):人类尺度的厄尔尼诺伴随的润湿气候使得母源区遭受强烈的化学风化,同时河流搬运能力增强,使得大量的沉积物被搬运到南加州外海。所形成的Hueneme海底扇的平均堆积速率由中全新世的5~8 m/kyr激增到晚全新世厄尔尼诺气候期的10~12.5 m/kyr;而Newport海底扇的平均堆积速率也相应从8~10 m/kyr增大到15~22 m/kyr
[
14
,
29
]
。
在北阿尔及利亚外海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陆架宽约5~20 km):人类尺度的Dansgaard/Oscheger暖事件使得D/O1⁃14期间浊流的沉积速率是同一地区距今2215年以来沉积速率的数倍。Giresse
et al.
[
30
]
将D/O1⁃14沉积期浊流沉积速率显著增高的现象归因于温润的气候:在温润气候条件下,水动力强、河流搬运能力大,更多的沉积物被搬运到Soummam Oued峡谷头部堆积;而在距今2 215年以来的干冷气候条件下,水动力较弱,河流搬运能力小,向峡谷内输运的浊流沉积物也随之减少。
在坦桑尼亚窄陆架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陆架宽约5~10 km):在Heinrich亚冰期(19.3~14.6 ka,海平面低位期),由于干旱的气候,使得坦桑尼亚陆缘的浊流活动停滞
[
32
]
。在Bølling⁃Allerød事件—早全新世(14.6~8.0 ka):伴随着回暖事件浊流活动增强,浊流沉积的频次、厚度和粒径在新仙女木期(T2⁃T4)显著增强,最后在早全新世浊流活动再次增强。在中—晚全新世(8.0 ka至今):气候变冷,浊流活动也相应减弱
[
32
]
。
在菲律宾Malaylay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陆架约5~10 km):Sequeiros
et al.
[
31
]
研究揭示Malaylay峡谷内浊流活动主要由2006年和2016年间的两次强台风(Durian和Nock⁃ten)所致。与“高屏峡谷内洪水成因的浊流”不同的是,Malaylay峡谷的头部未与河口相接,峡谷内的浊流主要是由台风所诱发的巨浪使得峡谷外陆架沉积物被再次启动、搬运到峡谷中所致。此外,东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湾(St. Lawrence Estuary)陆架宽度小于1 km,也为一典型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在该源—汇系统中,Pointe⁃des⁃Monts峡谷中所观测的浊流也是由风暴作用所致
[
33
]
。
(2) 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波动的过程响应:在以下几个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沉积物向深水中的搬运分散过程受到了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如末次冰期和间冰期、热带气旋和洪水事件)的调控。
在我国台湾的高屏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
图3a
;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约为1.0 km):亚轨道尺度的末次冰期和间冰期以及人类尺度的台风事件对峡谷内的浊流活动有明显的调制作用。Yu
et al.
[
59
]
研究表明MD3291柱状样(区域位置见
图3a
)34.0~15.3 m深度段仅出现两层薄粉砂层和一层厚砂层,其年龄跨度为26 205~12 310年(末次沃姆冰期);而15.3 m海底深度段累积出现四十余层浊积粉砂和一厚约几十厘米的浊积沙,其形成年龄跨度为12 310~60年(末次间冰期)。Yu
et al.
[
59
]
将这一“海平面下降的末次冰期浊流频次少活动弱—海平面上升的末次间冰期浊流频次多活动强”现象归因于末次间冰期以来的温润气候及其所伴随的充沛的降雨。Zhang
et al.
[
60
]
在高屏峡谷水深2 104 m的TJ⁃G断面处(位置见
图3a
)长达3.5 年内共监测到16次以“高沉积物通量、高悬浮物浓度、温度增加但盐度降低”的浊流事件(
图9a~e
),这16次浊流事件与区域地震活动并无匹配关系,而是由途径台湾的16次强台风所致(
图9
)。

图9
(a~e)高屏峡谷TJ-G观察点(位置见图3a)的16次浊流活动的沉积物捕获量;(c)(d)和悬浮物浓度(e)及其与区域地震活动(a)以及河流径流量(b)的关系(据Zhang
et al.
[
60
]
);(f~i)CT扫描照片揭示了阿拉斯加Eklutna湖洪水型和滑塌型重力流沉积(据Vandekerkhove
et al.
[
41
]
)
此外,在法国外海的Var峡谷(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仅为0.5 km)两年的浊流观测中,一共监测到6次洪水事件所形成的浊流,这6次浊流事件将重达1.07 t的沉积物搬运到Nice外海
[
37
]
。在下刚果盆地的刚果(
图4c
;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约为1.0 km)峡谷水深3 420~4 790 m深度段监测到多次的浊流事件,这些浊流事件也被认为是由刚果河2 000~2 005期间的洪水事件所致
[
35
]
。
(3) 峡谷头部和河口相邻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波动的过程响应:恒河—雅鲁藏布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的深水浊流活动忠实地反映了亚轨道尺度的新仙女木事件和季风波动以及人类尺度的热带风暴事件。
在恒河—雅鲁藏布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
图4a,b
);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约为30 km),亚轨道尺度的新仙女木事件和季风波动控制了孟加拉扇上的浊流沉积。孟加拉扇的水道—天然堤沉积体系在末次盛冰期不发育,而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的暖期(约9.7 kyr)浊流活跃、天然堤快速沉积建造
[
49
]
。在12.8~9.7 ka期间沉积建造的天然堤宽约13 km、高达 50 m,平均沉积速率从0剧增到300 cm/kyr(平均约130 cm/kyr);而这一时期,海平面持续上升,从现今海平面以下-100 m左右上升到-45 m处
[
49
]
。此外,孟加拉扇中扇水道堤岸处MD12⁃3417柱状样14.5 ka至今的浊流活动与印度季风活动(Indo⁃Asian monsoon)“休戚相关”。在9.2~5.5 ka浊流活跃作用期:印度季风增强、气候润湿;物源区遭受剧烈的化学风化且河流搬运能力显著增强;充沛的陆缘碎屑物质被剥蚀搬运到孟加拉湾,浊流活动频次高、活动强(平均每500年3次)
[
39
]
。在5.5~4.0 ka浊流活动停滞期:印度季风减弱、气候干旱,恒河—雅鲁藏布江搬运能力变弱,搬运分散到孟加拉扇的沉积物量显著减少,浊流活动近乎停滞
[
39
]
。在4.0 ka至今浊流活动期:印度季风增强,气候润湿,物源区化学风化较强,大量的沉积物被搬运到SoNG峡谷内,形成高频的浊流(平均每100年1次)
[
39
]
。
除了上述亚轨道尺度气候变化驱动的深水源—汇过程响应之外,风力在10~25 m/s不等的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也能够驱动孟加拉湾Swatch of No Ground陆架峡谷中的沉积物搬运—分散—堆积过程。风暴使得三角洲前缘和内陆架的沉积物被再次启动,搬运到峡谷内形成风暴浊流
[
38
]
。这些风暴浊流沉积可见粒序层理、以粉沙—沙层为主、单层厚约2~4 cm,忠实地记录了孟加拉湾自1970年至今的风暴事件
[
38
]
。
(4) 湖盆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波动的过程响应:湖盆一般缺少宽阔的陆架区(过渡区较局限),所形成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能够能对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做出快速响应,譬如洪水事件在阿拉斯加Eklutna湖和我国龙门山地区的紫坪铺水库湖盆源—汇系统的深水沉积区都留下了“烙印”。在阿拉斯加Eklutna湖,Vandekerkhove
et al.
[
41
]
识别了1989年和1995年的洪水型重力流(
图9f~g
)以及1964年阿拉斯加大地震和1992年大坝溃堤所致的滑塌型重力流沉积(
图9h~i
)。美国阿拉斯加地区1917年以来的6次大型洪水事件(1917年、1929年、1989年、1995年和2012年)在区域上具有横向可对比性(
图10
)
[
41
]
。汶川地震两年后,由于强降雨带来的洪水才将汶川地震崩塌的沉积物带到位于龙门山地区岷江流域的紫坪铺水库中
[
40
]
。
图10
区域连井剖面揭示了1917年至今6次大型洪水所形成的洪水型重力流以及1992年大坝溃堤和1964年阿拉斯加大地震所形成的滑塌型重力流(据Vandekerkhove
et al.
[
41
]
)
在构造—轨道尺度上,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响应时间
T
eq
≥10
4
年)能够对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
T
p
≥10
4
年)做出响应和反馈(
图2a
),这一过程响应是通过气候变化诱发的海平面升降(可容空间)来完成的(
图2a
)。譬如,中中新世变冷事件导致珠江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在下降体系域和低位体系域形成大规模的富砂海底扇(
图8
);在这些冰期变冷事件过程中,海平面也随之大规模下降,海底扇主要出现在海平面下降的背景条件下。这一观点也被如图11a所示的晚中新世—第四纪红河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3a
;现今陆架宽达100~450 km)和如
图12
所示的上新世—第四纪冰室数模结果所佐证。晚中新世(10.5 Ma)—第四纪红河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发育三期陆架坡折迁移轨迹(每期时间尺度约为10
6
年);海底扇(中连续、强振幅、中频的下超反射)主要出现在构造—轨道尺度的下降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示意可容空间下降)的前方(
图11a
)。在上新世至今的冰室模拟陆缘上,海平面下降(约占模拟时长的60%)也能够驱动三角洲越过内陆架形成陆架边缘三角洲并向深水中输运砂体,形成低位浊积沙(
图12
)
[
61
]
。
图11
构造—轨道尺度迟滞响应(中新世—第四纪红河,剖面位置见图3a)和瞬态响应(由序号1-20沉积斜坡组成的早始新世Spitsbergen陆缘)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之对比(图b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Ron Steel教授提供)
图12
(a)不同时期的冰室和温室陆缘的地貌形态,(b)海平面变化情况和形成陆架边缘三角洲的时间占比以及(c)深水沉积物分散模拟结果(据Sømme
et al.
[6
1
]
)
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气候波动(
T
p
≤10
4
年)往往被快速海平面的上升所“淹没”,对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响应时间
T
eq
≥10
4
年)的深水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没有调制作用(
图2a
)。如图13a所示的自红河源—汇系统的地震剖面,琼东南盆地现今陆架宽达100~450 km),为一典型的“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3a
)。在红河迟滞响应源—汇系统中,每个上升—下降海盆坡折轨迹对的时间跨度约为10
4
年,底积层出现在下降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橘红色点)而非上升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蓝色点)的前方(
图13a
)。这表明正如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可容空间下降的干旱气候期,底积层发育;而在可容空间上升的润湿气候期,底积层不发育
[
15
]
。
图13
(a)亚轨道—人类尺度迟滞响应(第四纪红河,剖面位置见图3a)和(b)瞬态响应(匈牙利Pannonian湖盆)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之对比
由此可见,迟滞响应源—汇系统中沉积物在深水中的搬运分散过程吻合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主要受到可容空间的驱动(
图2a
)。在构造和轨道尺度上,全球变冷冰室气候期浊流活动较强、形成的沉积体相对富砂,而全球增温暖室气候期则使得浊流活动较弱,形成的沉积响应相对局限且富泥;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气候信号往往被快速海平面上升所“淹没”(
图2a
)。
在构造—轨道尺度上,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T
eq
≤10
4
年)能够对大尺度的气候变化(
T
p
≥10
4
年)做出响应和反馈,这一过程响应是通过气候变化诱发的沉积物供给(物源供给)来调制的(
图2b
)。譬如,构造尺度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使得浊流活动减弱,而渐新世初大冰期变冷事件使得鲁武马瞬态响应源—汇系统的海底扇相对富砂(
图8
)。如
图11b
所示的早始新世Spitsbergen陆缘,温室气候和窄陆架(陆架宽约20 km)形成一典型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在Spitsbergen下降型和上升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的前方均发育海底扇,可见沉积物由陆架边缘向深水中的搬运分散独立于海平面或可容空间变化,而主要受控于沉积物供给的变化(
图11b
)。在
如图12
示的温室(晚始新世—早渐新世和晚白垩世—早古新世)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海平面下降(低位期)和海平面上升(高位期)均能驱动三角洲越过陆架形成陆架边缘三角洲,且三角洲在外陆架“驻留”的时间亦较长(约占模拟时长的72%~75%)
[
61
]
。
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T
eq
≤10
4
年)同样能够对小尺度的气候波动(
T
p
≤10
4
年)进行响应和反馈(
图2b
)。多瑙河流域的Pannonian湖盆具有陆架—陆坡—盆底的三分地貌单元,陆架的宽度从30~60 km不等,是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图13b
)
[
15
]
。在Pannonian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每个上升—下降湖盆坡折轨迹对的时间跨度约为10
4
年,底积层出现在上升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蓝色点)而非下降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橘红色点)的前方(
图13b
)。这表明与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不同的是,在湖平面下降的干旱气候期,底积层不发育;而湖平面上升的润湿气候期,底积层则更发育
[
15
]
。此外,Liu
et al.
[
32
]
利用柱状样(GeoB12624⁃1)重构了坦桑尼亚末次盛冰期以来的三期浊流活动史,认为深水沉积物搬运—分散—堆积的源—汇过程并非如经典层序地层学所预测的那样(海平面下降时增强),反而在海平面上升的润湿气候期更加活跃。
由此可见,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物源供给的变化则更为敏感,气候变化能否在深水中被记载取决于其能否诱发沉积物供给的变化(物源供给驱动)(
图2b
)。不论是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还是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只要其能够诱发沉积物供给的脉动,它们都能够在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均能够“雁过留痕,风过留声”(
图2b
)。
“多尺度气候变化的深水源—汇过程和响应”是当前沉积学领域颇为关注的科学命题,存在如下颇具争议和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多尺度气候变化对深水源—汇系统的调制”是源—汇系统研究的重要命题,近年来人们在“深水沉积对古气候的反馈/响应”取得了重要进展
[
14
,
16⁃21
,
32
]
,但也存在如下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1) 多尺度气候环境演变是如何调控沉积物在深水沉积环境中的搬运—分散—堆积的地表动力学过程?
(2) 多尺度气候环境变化是如何在外陆架—深水盆地的源—汇系统中传输、分散和保存的?
(3) 多尺度气候环境演变是如何调制深水源—汇系统构成要素的沉积构成样式和发育演化过程?
尽管本文对“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做了简要的梳理,但这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
气候和海平面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控制着沉积物在深海环境中的搬运—分散—堆积过程
[
16⁃18
,
62⁃63
]
,但目前浊流活动(频率、周期和堆积速率等)对气候变化的源—汇响应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具体说来,以伦敦大学学院Mark Maslin教授为代表的古气候学家研究认为气候变暖会导致水合物分解和地震活动剧增,从而诱发大规模的高频浊流事件
[
6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