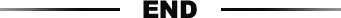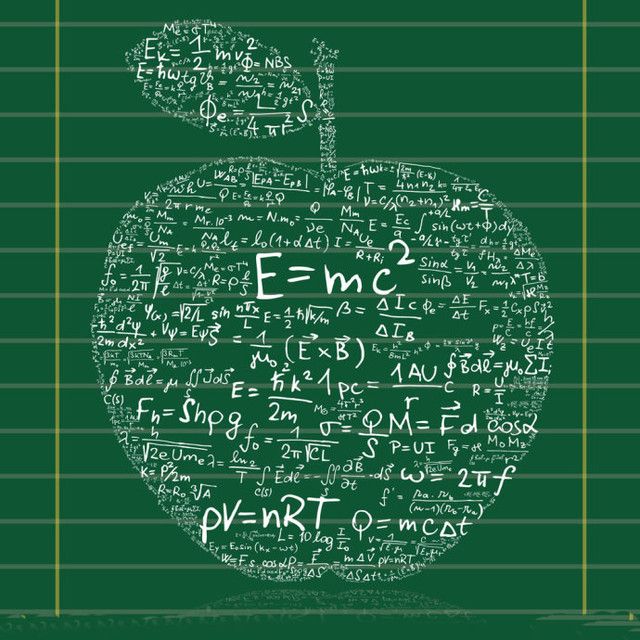跟导师的第一面就是不顺利的。他不了解亚洲以及亚洲文化,也没有带过亚洲的学生。所以他假定我的英语很好,可以轻松的融入那个社会;他甚至假定我有环境科学的背景,了解相关知识。因此,在交谈中当他发现我听不懂他的方言英语并且对环境知识一无所知时,很不开心,并认定我是个不爱学习的坏学生。但事实是,我只是一个从未去过西方的经济学学生,我怀疑我在他的工作任务中微不足道,以至于他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有的工作逻辑去面对我。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因材施教”的方法,他怕是半分都没有领会。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我去旁听硕士的环境课程。我英语不好,他们的南欧英语让我感觉非常痛苦;课程时间紧张,身体得不到休息,经常上课时打哈欠,头脑一团浆糊;上课多是讨论,我不知道怎么参与;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任何环境专业的知识,像听天书一样。但是他不会理解你的难处,也从没有询问过或者专门找你聊天;如果你学不好,那就是坏学生。还有一次,他在发课程考卷,临到我时,看到分数只有60多分,很生气的扔在地上,转身就走。周围同学很惊讶,教室一下子寂静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默默地把试卷捡起来。那时我感受到的不只是羞辱,还有歧视。我还清楚记得旁边一个本地同学惊讶和怜悯的目光。我心里很感激她,哪怕只是一个目光。有次我做了几个图并附有文字解释发给他提建议,结果他不好好提建议,抓住一个remarkable(我想说“曲线明显的增长了”)的单词使劲的批我:这个词能用在这里吗?你告诉哪里明显增长了?语气十分激进。全篇没有建议,只有批判,这样的态度,我哪还敢把写的东西发给他?才发现,“穿小鞋”不是中国人的独创,只要你得罪了他,干什么都是错的。他都可以挑刺,然后抓住那一点使劲批你,让你连话都不敢说,厚黑的功夫一点不比国内差。
还有一门课程实在听不懂,就逃课了,老师给他打小报告,他知道后极为愤怒,之前所有的不满都通过这个机会宣泄了出来:给我连发几封邮件,几乎每一句都有问号和感叹号,看着让人心惊肉跳。一封骂完意犹未尽又接着骂,把所有的愤怒和不满都骂了出来,看得我胆战心惊。我只是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外国学生而已,他掌握我的生杀大权,一句话就可以把我赶走然后我就要打道回府还要赔钱,而他有十个博士生少一个对他没有任何伤害。所以在我与他的博弈中,我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委曲求全。那种寄人篱下却又无法摆脱的滋味让人痛苦至极,现在回想起来还唏嘘不已。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可奈何怕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体会和理解的。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也不敢回复,怕哪句话惹到他又会把我狗血淋头的重新骂一次。我很难过,那是一种死寂和生无可恋的难过,我看不到任何希望。他像一个电源一样,接触就会被伤害,不接触他会抱怨你不懂得合作不努力。但是很庆幸有个中国博士去陪了我,坐在学校的草地上一直说着宽慰我的话,让我的心重新明亮起来。如果没有那次宽慰,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因为面对面交谈经常挨批,所以我只敢发邮件致歉,告诉他我听不懂,自己看书可能更有效率。结果他针锋相对的说,既然你觉得不用上课都可以学会,那你去参加考试吧;联系课程老师说自己是主动要参加考试,考完了试卷拿给我批。就这样,我成了旁听生里唯一一个要去考试的人。期末时,考了9点几分,班级前列。他在办公室跟我说我考的很好,他的表情告诉我这出乎他的意料。只有我不觉得惊讶,因为我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学期结束后的一天,我跟同一个导师的博士聊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和导师确定了未来研究的主题和具体计划,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遗忘了,每天帮他傻乎乎的找一些数据做一些计算,然后就是旁听跟自己完全不相关的课程,我甚至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研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几天后我找机会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他突然愣住了好几秒——原来他压根就没想过我的培养计划,我不过是给他和他的项目打杂的免费劳力。那一刻我深刻地意识到,我只能自救,否则这里会毁了我,以及我的前途。若干年后,我在人大经济论坛偶遇了一个帖子,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德国博士半夜发的无奈呼喊,他只被安排做一些跑数据的无技术含量的工作,毕业时把他的名字加在作者目录的后面,导师签字也就可以毕业了;虽有德国博士的名号,但是含金量却还不如国内。他想上进,但却无能为力。我很能理解他,我曾经也是如此。
当地的生活与世隔绝,因为南欧人教育水平低不会英语,我们留学生也不会当地语言,所以基本算是瞎子和聋子。再加上长期巨大的学习压力,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精神也接近崩溃的边缘,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沉默不言:不跟人说话,不去办公室,不参加任何活动和聚餐,周围同事经常拿着看神经病的眼神看我,路上碰到也会远远躲开。那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段时间,这相当一部分是他造成的。记忆尤深的是,有次邀请隔壁系的中国朋友来所里厨房吃午饭,正好他跟另外一个老师过来吃饭,我就笑着跟他打招呼,他却斜眼都不看我一下,冷笑着回应了两句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在隔壁桌子吃饭,一直用当地语言跟另一个老师交谈。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只知道那个老师用非常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我猜,他再向那个老师尽数我的“劣迹”吧。就这样,一对师生连最起码的见面交流都无法进行,他已然放弃了我,在笑看我的“覆灭”。
曾经一直百思不解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没有经过仔细面试审核就愿意接收我,后来在慢慢的了解中才发现,他的研究主题,是一个非常偏激以至于遭人耻笑的主题,国内更是没有市场。那一思想来自于地中海沿岸国家劳工的街头运动,他们通过街头抗议表达对自己底层身份的不满,偏右翼激进派,骨子里就是偏激的。我曾在年度测评提及这一主题,结果一个老师乐了好久,他觉得这很可笑;另外一种反应,就是瑞典老师听到我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惊讶的说 “it is stupid for me!”;我无奈的跟他说我导师研究这个,我也没办法。他默默地点点头,我感受到了一种理解的尊重。所以,稍微理解这个理论的经济学硕士生都不会去申请,只有我这个不了解内情的傻瓜才会去申请。另外,他想要用实证去支撑他的理论,否则没有说服力。所以他想要找一个会计量的经济类学生帮他,于是我“幸运的”被他发现了。但是他却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欧美不同,很多只学理论不学计量,所以当他有一次跟我meeting时问我这个模型什么意思然后我说不知道之后,他才明白我没法帮他,如意算盘打空了,收了一个没用的累赘,他当时惊讶和泄气的表情让我记忆犹新。从那之后他就开始敷衍我,没多久就不联系了,这一断联情况持续了博一的冬季学期,接近半年的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明白,这是冷暴力,他想赶我走但找不到合理的理由,于是故意不理我,让我知难而退自己离开。
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段时间,经过痛苦的思考,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学计量将无法毕业,我不想被赶走灰溜溜的离开,我也要让他看得起我,我要证明给他看。于是我闷在屋子里几个月的时间,除了出去买菜,我几乎都在电脑前学模型。这很痛苦,对于没有数理基础的学生而言,有人教尚且不易,没人指导更加艰难。于是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我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买了一本中文STATA教程一页页的看,一点点的学,没有具体内容的地方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尝试,错了再试,一点点的往前推进,十分的艰难。有些问题书中没说,也实在没法解决,就上人大经济论坛咨询。可能是有过切身体会的缘故,一般提问题都会有人解答;有时心中很着急一天发几个帖子,有坛友感受到了我言语中的不安和慌乱,就会好心回复我,像在帮助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所以我对论坛很有感情,可以说没有论坛的帮助,我不可能发表之后的英文SCI,也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所以第一篇SCI出来之后我专门发了一个奖励回帖的帖子,去帮助那些像我一样急需帮助的人。我很感恩这个论坛,她陪伴我走过了人生最痛苦难熬的时光。
在这样的努力下,我终于完成了三篇论文的初稿,主要是计量分析和一些跛脚英文的解释。但我已经很开心了,因为这些文章的创新想法是我自己的,我发现了前人研究的缺陷和没人注意到的近几年的趋势变化;模型也是很先进的模型,是我自己努力做出来的,很有成就感。我天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讨好他,不会被他赶走,顺利的合作下去。于是我主动要求去见他,没想到等我高兴地把三篇文稿放在他桌前的时候,他轻蔑的冷笑了一声,翻都没翻直接扔在桌子一边,跟我说,这个主题已经研究到头了。然后开始指着鼻子骂我,似乎要把之前的不满都发泄出来。我傻乎乎的听完,再次尝试跟他解释我的文章内容,结果又被他打断,继续斥责,一直到下一个博士过来。等我离开办公室时,我侧身看见那个博士很奇怪的问他我是谁,他嘲讽的笑着跟他说些什么,我猜,他在笑我是个自以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做出新研究的中国傻瓜吧。回到办公室,我无力的瘫坐在椅子上,万念俱灰。自己再努力,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无法教育的外国学生。我自学计量做出来的模型,他也觉得是靠不住的:哪有不上课自学模型可以发表好文章的?他自己四十多岁教授级了一个模型都还不会做。我至今记得那时欲哭无泪的感觉,没有退路,却也找不到目标,人生被挤压在无奈的现实中,无所适从。
那天晚上,我像一个没有感情的纸片人一样,不知道怎么走回家的。躺在满是热水的浴缸里,想着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没人能帮我,不敢告诉家人,周围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也无力帮忙。但是这样僵持下去最终倒霉的是自己,我毕不毕得了业对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已经撒手不管乐得在一边看笑话了。最终,我做出一个决定:他让我做他的主题?可以,就当是为了毕业;但是他的主题太偏激没有市场?没关系,我自己找有价值的主题自己做,大不了多花一倍的时间,没有休假没有娱乐而已。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全然不觉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水完全冰冷,感冒了。但是那个晚上是我博士期间最重要的转折点,我在他的胡乱指挥和各种压力下浑浑噩噩的过了将近一年,现在终于有了清晰地方向,虽然会很累,但我最起码知道该往哪走了。同时,我学会了和现实做出妥协,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匹夫之勇,并做好了在之后几年中与不得已的事情相存共生。但是可笑的是,这个时候在那里读博士已经成了一种拖累,我无法从所里和同事老师那里得到计量方法、研究方法和创新思维,这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还不得不去花时间去完成他的主题,否则无法毕业。即便如此,那晚的我还是豁然开朗了。回想那时,惊讶于自己有那样的勇气,并感谢自己拯救了自己,否则哪有现在闲庭信步、风轻云淡的生活和心境。
半年多以后,以我为独立作者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了。那时我在维也纳交流,他发邮件祝贺我,然后问我作为导师为什么他不知道?这很有趣,当年把它甩在一边说没有研究价值的人又是谁呢?我如果告诉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炫耀?我只能“认错”并告诉他下次我会注意。从那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和善了很多,因为他开始意识到我是有一些科研实力的,而不是他当初认为的学术混混。又过了一年左右,被他甩开的第二篇文章上线了,发在了一个质量很不错的期刊上,在办公室里他向我祝贺,语气很柔软,全然换了一个人,但是我注意到他低着头,眼睛一直没敢与我对视,因为他记得这是他曾经说过的没有研究必要的那篇文章。又过了半年多,第三篇上线,一位美国老师在推特上说,这篇文章改变了他对这个领域一贯的看法,因为文章部分否定了前人的结论。有趣的是,博士期间发表的三篇文章,全是他曾经否定过的;而他的主题文章,至今都没定稿。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开辟自己的研究,我至今一篇文章也没有,连毕业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 。
毕业前一年左右的时候,我跟他谈论毕业时间。我说想提前几个月毕业,因为我的各方面成果已经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他跟我说他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博士一般都是4-5年毕业;而他最优秀的一个博士四年才毕业。然后他看了看我,言下之意是你不是最优秀的,为什么要提前。我什么都没说,最后曲曲折折、紧拖慢拖的终于毕业了,还是提前了几个月,是他所有博士中最早毕业的,并得到了评审委员一致给出的“Excellent”的成绩,还是国际联合培养。一个海归博士能得到的,我大都得到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答辩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出钱请答辩委员和其他老师一起吃饭庆祝我毕业,饭桌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说,以后去中国发展,就要靠你了。全桌的人都很惊讶,一下子安静下来。我说没问题。这不是敷衍,而是实话,我会尽力帮他。没有感激之情,也不存在什么愤懑了,哪怕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无可奈何和多少个不眠之夜了。因为我已经明白,愤懑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伤害的只是我自己;在我忍受他的时候,他也在忍受我,只是我承受了更多。晚餐结束离开,已经半夜十一点,一个人走在路上看着熟悉的城市,突然间意识到:近四年的困兽之斗终于结束,我可以离开隐形的牢笼开始新生活了!回去后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告诉国内的朋友我毕业了。我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引用了苏轼《定风波》里的那句很有哲理我也很喜欢的句子:“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记:犹豫了好几次终于贴上论坛了,把伤疤揭开给众人看,是因为之前有前辈也回忆了自己艰难的博士历程,给我很大的触动,心有戚戚焉。我希望通过此文告诉大家,能找到一个好导师是一种幸运,碰到一个不合拍的导师是一种锤炼。我一个朋友从博一被他导师用脏字骂到了毕业,他那么憨实的人有次气的差点动了手。受锤炼的远不止我一人,只是我说出来了而已。国外学术界未必多干净,导师素质未必多高,国内博士的研究成果优于海归博士的也大有人在。至今为止,我都自负的以为我的能力配得上更好的学校,也会做出更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现实无法改变,只能在已有的平台上尽力做到最好。于我而言,国外读博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知道如何抗压,并能够成熟的去理解和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能力的培养,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比论文本身更重要。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后人以指导,不要误入歧途,造成终身的遗憾。读博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