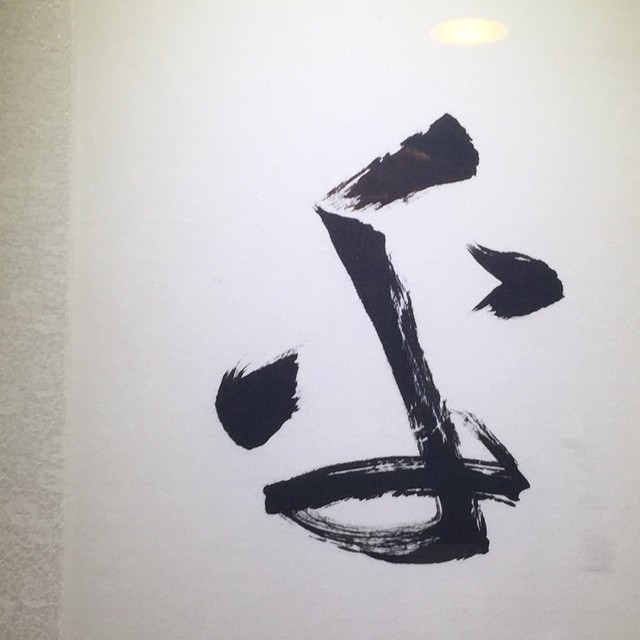![]()
张宪超|文
晚清开埠后的上海由之前的小县城,迅速成为炙手的地方,远东第一大港,这个名号的由来,恐怕都要归结于洋人的功劳。当时北有天津,南有上海都有洋人最早的租界在里面。上海的发展在当时的美国记者眼中,比日本开埠后的一些港口都要好,繁荣程度甚至要和美国的一些城市相媲美。
在1843年,根据中英签订的条约规定,将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大部分的洋商都集聚到了这里。当时的上海道台,为了防止辖下的居民与洋人有过多的接触,主动和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这就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来了,上海方面分别与其达成共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法国的租界则是法国专管租界。
中英《南京条约》的续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载明:“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实际上,晚清政府对于洋人要取得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概念。他们也正是看到中国的司法太落后,所以才要领事裁判。
在租界刚刚划定的时候,洋人和大清子民接触的还不是很多,地方官普遍都实行华夷分居,这里说的“华”,当然是指大清子民,“夷”是指洋人。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已经成为通商口岸,但是广州当局,一直坚持不让英商进城,只允许让他们在城外做买卖。广州入城问题,一直拖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当时已经升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是出了名的顽固。
当年在广东巡抚任上和时任两广总督徐广瑨,一直阻止英商入城,这个后来自称“海上苏武”的叶相,此时对英国领事置之不理,一不接见,二不回函,后来这事就演变成为战争的一个由头。
上海开埠后,贸易中心从广州逐渐转移到了上海,上海虽然是一个小县城,当官的基本上也大愿意让他们进城。上海方面,只有在县城外划一块租界,统一规定在此活动,对于官方来说也便于管理和控制。由于大清子民和洋人隔绝,地方官员也就不足畏惧,问题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就又不同了,特别是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残卷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好多的人都躲进了租界里。这样一来,华人和洋人混杂在一起,对于中方官员的管理成本也就大大增加。
英美租界合并后,在1868年上海当局和英美之间商定《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公共租界里设立会审公廨。洋泾浜是上海的一条河流(后被填平,即现在的延安路),正好位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间。会审这个说法,自中国古代就有,明清两代称作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只有是重大的案件才要三堂会审。这样的会审,司法程序相较更为严苛。
![]()
至于说上海租界里的会审公廨,简单来说就是由大清官员和洋人领事一起审案子。根据当时中外双方的规定,案件涉及到洋人或是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则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是观审。
在名义上,这个机构属于大清的司法机构,在涉及到洋商问题的时候,大清官员不能完全做主,真正做主的,还是背后的洋人。中方的谳员,只能是在纯粹华人案件中才能做主。
会审公廨的设立,不可否认,是洋人对晚清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说明当时中国的司法体系确实太落后了。严格说,没有行政和司法的划分。在地方上,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司法官员,法庭开在衙门里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通过读书入仕的文人,有没有审判断案的能力还不好说。
从朝廷的逻辑来看,读书越多,做的官越大,相应的能力就越强。但实际上,这本身并没有多大相关性。文人士大夫的终极目标无非就是“立言”、“立德”,入仕为官,点了翰林就是莫大的荣幸,如果德行好学问大,做了帝师,那更是一辈子的荣耀。晚清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两代帝师,不论其官阶高低,所有人见了面也得称一声“翁师傅”。这在晚清还绝无仅有。除此之外,夫复何求?
在以前的朝代,地方官员大抵都会聘请幕僚辅助自己工作,有清一代,师爷非常活跃。清朝直隶河间府出太监,晚清时绍兴地区则专门出师爷。地方上至督抚,下至州县,都聘请师爷辅助工作,还不止一个,很大程度上官府公务、审案断案,他们的意见会发挥很大作用。换言之,人的意志在司法审判中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官员扮演司法审判的角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些师爷们仲裁调解的本事高。
审判程序的简陋,再加上严酷的刑罚,让洋人瞠目结舌,这就造成他们要求获得治外法权。据一个美国律师在中国的观察:几个月前,上海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即把他关进笼子中,头伸出笼外,卡在一个洞中,不能动弹。然后,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中取走一枚石子,直到其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就更不用说,凌迟、枭首那些极其残忍的刑罚了。
在一次庭审中,会审的领事正在惊讶辩护律师之余,审判已经结束,中方官员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律师,上海也没有律师协会。在“少见多怪”的洋人眼里,一切都太草率,程序也不正当,更没有律师为之辩护,不过被审理者是个清国人,他也就不再追问。
我们应该能想象的到,电视剧里时时再现的情节,证据不足最后给屈打成招,牢狱之灾总是能联系起血光剑影。如果做官的都是“包龙图”还好,凭着独到慧眼辩清真假忠奸,但是现实又怎么可能。
![]()
读过圣贤书的官老爷们,能写的一手锦绣文章不假,圣贤书里面也刻有自省的句子,吾日三省吾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至于说,司法的道理,恐怕就黔驴技穷了。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们来说,人的意志在任意主宰着他们,仰人鼻息也从来不特指吃官司的时候,反过来说,吃官司的时候,平时可能仅有的点尊严也会荡然无存。
晚清以降,官场更是腐败成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卖官买官也是公然标价,实缺、肥缺从不吝啬,只消银子说话。本来就不济的官僚队伍,混进这些蛀虫,对上蒙混过关,对下能欺就欺能压就压。这样的现状,司法能讲什么道理么?可不就如同那位美国律师所见到的,快刀斩乱麻的审判和没有道理就被指控为“疯女”的情形。
他们做官要的是收回自己当初买官的银子,对于审案子这件事别说不懂,即使真的是位“神断”,对此八成也会不屑。司法断案对于一些官员来说是分外的事,捞银子才是正经的工作。
古代有法律,也可以称之为法制国家,要么刑律,要么礼法典章,唯独缺少制约强权的法。读书人靠道德伦理,能分得清礼义廉耻,很大程度上也能规避一些有违纲常之事,这更多的是靠自律,并没有形成更现代意义上的法。升斗小民同样受宗法影响,宗族内部是有人订的规矩,但是私心作怪也不可避免,一旦冲破宗族规矩的束缚,交由官府发落,这时有无公正的司法体系就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