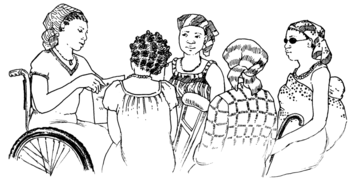近年来,女性和家庭照顾者角色的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讨论。当我们继续沿着性别角色和家庭责任的脉络思考,更多、更被主流话语所遗忘的声音便开始出来了:残障女性这个群体,身处残障议题和性别议题的交叉点之上,也承受着社会和文化的双重歧视。那生活在现代社会下的残障女性面临的处境是怎样的呢?当她们成为母亲时,她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呢?
本文作者郭惠瑜来自台湾,系英国利兹大学社会政策博士。本文基于作者对两岸小儿麻痹女性群体的访谈成果,试图打破社会对于残障女性的刻板印象。
随着社会结构变迁,我们对于“母亲”这个群体的样貌有了更多元的理解。近年来社会关注单亲妈妈处境,以及新移民女性在亲职上的困境,乃至刻画同志母亲的生命经验,丰富我们对于母亲样貌的多元理解。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一群仍然被主流论述遗忘的女性——身心障碍女性家庭照顾者。
英国身心障碍女性主义学者珍妮·莫利斯(Jenny Morris)指出,在家庭照顾议题的讨论里,身心障碍者往往被视为家庭依赖者,而家庭照顾者多为女性,因此身心障碍者被视为造成女性照顾者的压迫来源之一。莫利斯批判这种照顾者/受照顾者二元论述,忽略了许多身心障碍女性本身也是家庭照顾者,而她们的照顾经验长期被漠视,需求也被服务体系所忽略。
研究者发现,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大多数残障女性都承担着家中主要的照顾者的角色,不仅养儿育女,也提供家中经济支持。而这些女性渐渐迈入中老年阶段,也开始需要扛起照顾年迈公婆与父母的责任。这些身障女性承担家庭照顾责任,努力扮演“好母亲”或“好媳妇”的角色,但她们在家庭照顾中所面对的困难,却仍然被漠视。
身障女性的母职角色遭到漠视,来自于社会长期以来对于身障女性的歧视。近年来女权思想逐渐被社会所接受,许多女性选择跳脱传统女性角色框架,开始思考母职角色对于女性的长期压迫,选择不婚或不生育。然而对于身障女性而言,想成为一位母亲,却仍然需要面对社会的质疑。

美国身障女性主义学者米歇尔·芬恩(Michelle Fine)与阿德里安·艾许(Adrienne Asch)指出,许多身障女性不婚或不生育,很多时候并非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因为母职角色遭受否认所导致。许多身障女性不被鼓励生育,来自于亲友对于疾病遗传性的担忧,认为身障女性会将自身的状况遗传给孩子。即使某些疾病不具遗传性,遗传可能性也容易被误解或夸大,而限制身障女性的生育选择。
譬如小儿麻痹症并不具备遗传性,但仍有受访者提及,婚前遭受男方家长质疑是否会将疾病遗传给孩子。这般社会偏见也造成身障女性对于生育的恐惧,如一位受访者发现自己怀孕时,担心如果自己生出一个“怪物”来。而对于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女性而言,在生育抉择上往往受到更多质疑。
除了遗传性的担忧,身障女性常被认为没有能力照顾孩子,因此不被鼓励生育。而身障女性的母职经验,则需要放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下去理解。
在社会传宗接代观念里,身体残障的女性同样背负生男压力,许多残障女性表示,她们被要求替夫家生儿子。此外,怀孕对身障女性的身体造成极大负荷,她们怀孕过程所产生的生理变化可能与一般产妇不同,但是在孕程中所面对的风险与问题,却无法在现有生育服务中得到支持。

譬如身障女性在怀孕过程中,为减少跌倒风险,原本使用拐杖者需改坐轮椅,但仍然缺乏辅具调整以及健全的无障碍环境。残障联盟曾经针对台湾肢体障碍母亲进行调查,发现目前能够提供给肢障母亲的育儿信息不足,产检设备与医疗院所也充满环境障碍。
身障女性在照顾孩子过程中也面临许多挑战,照顾方式因此必须进行调整。例如一位手不方便的母亲提到:
 我的手没有力量,小孩还小,我得用牙齿咬住孩子衣领,把他从学步车上移出来。
我的手没有力量,小孩还小,我得用牙齿咬住孩子衣领,把他从学步车上移出来。
缺乏适当的支持,使得这些女性必须发展自己的育儿策略,而来自伴侣的协助自然也相当重要。
国外研究早已开始重视身障女性的亲职支持,如身障者的辅具不仅用于行动上的辅助,也需回应身障母亲的育儿需求,提供适合身障母亲使用的辅具。网络上也出现为身障父母设立的网站,用以分享彼此育儿经验与信息,如哪里可以购买方便穿脱的童装或是适合身障母亲使用的育儿用品。
现有的身心障碍服务缺乏性别意识,忽略身障者之间的性别差异。现行服务把身障女性视为家庭依赖者,而忽略其家庭照顾者的角色。现行居家服务的僵化不断被人所诟病:有受访者申请居服员协助打扫居家环境,居服员(编注:居家服务员,简称“居服员”,是台湾地区政府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的照顾人力,其服务内容以家务整理为主。)被规定只能打扫她常坐的那张沙发,其他家人使用的家具则不在清洁范围,而备餐份量也规定“不能煮太多”,因为担心她会将食物分给孩子们吃。一旦服务超出身障女性本身的照顾需求之外,都不能够被允许。整理家务与为孩子备餐被视为母职任务的协助,都被排除在现有服务之外。
另外,陪同幼儿就医也是困扰许多残障女性的难题,对于使用拐杖或轮椅的身障女性而言,无法亲自牵着孩子或抱着孩子去医院,因此需要第三人陪同送孩子就医。如果她们的伴侣也是障碍者,或是因为突发状况而家人也没时间陪同就医,她们求助无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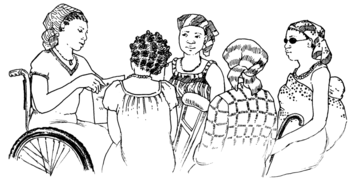
然而,即使在残障群体权益状况相对进步的台湾,现行的身心障者陪同就医服务(编注:身心障碍陪同就医服务,即陪同身心障碍者去医院完成就医、治疗等过程的陪伴服务),仍然局限在以身障者就医需求为主,身障母亲需要其他人协助陪孩子就医的需求,则很难得到回应。
这些例子凸显了身障女性获得亲职照顾支持的迫切性,但其亲职需求仍然被忽视。近年来,英国社会政策开始回应身障父母的亲职需求,强调身心障碍成人服务应该将身障父母亲职需求纳入,并整合儿童服务,妇女服务来协助身障父母实践亲职角色。
除了母职的角色,迈入中高龄的身障女性开始需要面对另一个照顾上的难题——这些女性在50岁左右开始面对提早老化及体力退化状况,但另一方面却需要承担家中年长者的照顾责任。而目前在台湾,老年照顾服务未臻完善,长期照顾服务所提供的社区照顾支持仍然不足,聘用看护照顾家中长者成为台湾主要的照顾型态。
不少残障女性面临由于自己体力上限制,未来也只能雇用看护来照顾家中失能长者的状况。但若缺乏政府于雇用费用上的支持,并非每个家庭都有能力聘用看护。除了少数家境优渥者,大多数残障女性仍属于就业结构中的弱势,长期处于低薪与不稳定的就业型态。特别是夫妻皆为身障者,若无人共同负担照顾费用,家中长者的照顾支出是相当沈重的经济负担。这些长期处于经济弱势的身障群体,同样需要家庭照顾上的支持,但却难以负担家庭的照顾支出。
调查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身障女性无法实践母职角色,并非出于自身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于社会歧视与偏见的影响或缺乏适当社会支持、无障碍设施等保障,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上的排除。

现有服务与政策忽视身障女性照顾者的需求,这些负担家庭照顾责任的身障女性,她们的声音仍然不被听见。台湾于2014年通过国际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联合国残疾人公约》施行法,公约第六条强调各国需认知身心障碍妇女和身心障碍女孩遭受多重歧视,应采取措施确保她们充分平等地享受参与权和基本自由。
残障女性不是依赖者,必须将其视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提供足够社会支持协助其实践生活中的各种角色。把“当妈”或“不当妈”的选择权,还给她们。
作者| 郭惠瑜
转载自残障女性发声平台“DAWS残障姐妹小组”
欢迎扫码关注


微信最具影响力女权公号
回复关键词,获取精选资讯
高跟鞋| 反逼婚 | 直男癌| 乳头 | 女歌
女权ABC | 腋毛 | 女足 | 同性婚姻 | 女博士
性骚扰 | 荡妇羞辱 | 家务 | 冻卵 | 性工作 | 男孩危机
校园霸凌 | 妇女节 | 二胎 | 月经 | 剩女 | 防狼手册 | 同工同酬
微信号:genderinchina
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