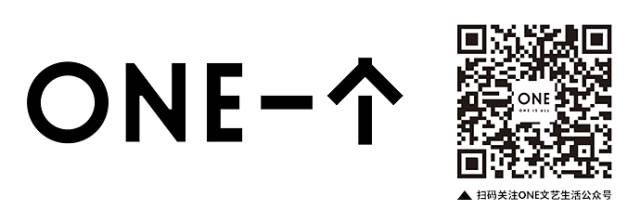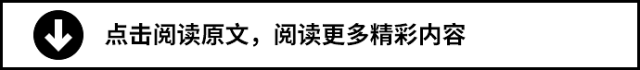挑选遗照的时候,觉得我那么好看,
我不能死。


这句话是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的。
她有段时间陷入抑郁情绪里,有天半夜突发奇想,要给自己选遗照。就是翻自己的相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也太好看了,“我这么好看,我不能死”。
我以前最最不开心的时候,就打麻将。
一口气打六个小时麻将,因为心不在焉,所以打得很烂,不断输钱。没关系,输钱也打。洗牌的声音能够让我镇定下来。
我另外一个朋友,在最难过的时候去洗药浴。在药浴的桶里哭,药浴到十分钟以后会浑身瘫软,觉得透不过气来,她用最后的力气站起来走出木桶。她说是站起来的那一刻,她发现自己还是想活下去的。
我不太喜欢跟人说“没事的”、“都会过去的”这种话,网易云音乐里有个评论,说过去的伤痕会变成故事的花纹。但确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过去的,强行鼓励别人坚强等同于剥夺了别人软弱的权利,人当然是可以软弱的。
今天说两个关于“绝望”和“活着”的故事。故事来源都是我身边的人,但他们都不是网红,所以我隐去了他们的部分真实信息,我宁愿你们解读成,关于活下去的那些时刻。
“我妈嚎啕大哭,说你给妈妈争口气啊”
楠楠本名叫“若男”。
她成年后自己改的名字。会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父母一心求子的意志昭然若揭。
楠楠是家里第八个女儿。她出生在一个小镇上,母亲在她之前生过七个女儿,除了大姐,其他的都被送了人,她是因为体弱送不出去才勉强留下。在她之后母亲再没有生育,楠楠看起来瘦不拉几的,却意外地活了下来。
楠楠形容青春期的自己是“像疯草一样长高”。十六岁的时候,班主任开玩笑说,你读书反正读不好,不如去做模特吧。班主任说的模特,是县城里饭店开幕式上,穿着短短的红色紧身旗袍的模特。
但楠楠被这句话激得跑到北京。她是坐T字开头的硬座火车来的北京,身上只有一个旅行包,包上印着Gucci的标志性花纹,但楠楠不知道,这个包是县城里买的,售货员和她都不知道这是山寨品牌抄袭Gucci的图案。
关于她走红前的故事,她没有跟我说过。但我记得一件小事。
我在北京的一家一点也不著名的咖啡馆里写东西,那家咖啡馆既没有格调也没有名气,但是我看到两个摄影师在架机器做采访,有个女主持人在采访一个瘦骨嶙峋的浓妆女孩,她说自己是中戏毕业的,是大明星xxx的同学。
采访过程我没细听,但我每次抬起头来看,发现那两个摄影师都在埋头管自己玩手机,没有人真的专心做这一档采访。
我跟楠楠说,他们心知肚明自己在做一档压根就没有人看的节目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楠楠说,他们在想今天的劳务费够开销多久。
然后她说,她们至少还能坐在一个咖啡馆里体体面面说话,比我当初好多了。你要是觉得她们可怜,那我当初算什么。

楠楠后来走红了。对普通人来说仍然是个陌生名字,但各个时尚杂志的内页都有了她照片。她替家里在省城买了套小房子,可是她父亲并不领情,他说,我在网上搜你的名字,怎么都搜出来走光、露点这种信息?你在北京到底在干什么呢?
楠楠没法跟父亲解释,人就是爱看负面的东西,她无法阻止别人对模特生活的肮脏想象,她也没有大腕到,可以决定自己出席活动的时候穿什么。
搬进新房子以后,父亲叹气说,我宁愿你跟别人的女儿一样,去工厂老实上班,也不想花你的脏钱。
楠楠尖叫起来,说我的钱怎么就脏了?
父女对骂,最后父亲动了手,抄起扫把朝她身上打,混乱中她看到妈妈抱住父亲,替她挨下了重重的一记。父亲停下来发愣的时候,她听到妈妈伤心欲绝的声音,她说楠楠你替妈妈争口气啊。
楠楠再也没有回过省城。都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楠楠照旧给家人打钱,但过年的时候,要么带父母出国度假,要么让她们来北京,她不愿再回去。那个新房子给她的全部记忆,就是“楠楠你替妈妈争口气啊”。
谁也不知道那声音要多久以后才消失。
“会不会我死在公寓里,都没有人发觉”
阿花是我见过最讨厌上海的人。
我是浙江人但我超喜欢上海的。喜欢到以前知乎上有个高票答案讽刺我,形容装逼的生活是“像倪一宁一样转悠在上海的每一条弄堂”。
我确实很爱吃本帮菜。明明不是上海人,但酒香草头、响油鳝丝、葱油拌面、本帮熏鱼……这些字眼简直能勾起我的乡愁。
上海有不少深得我心的本帮菜馆子,这些以后找个机会可以介绍,但我想说的是,阿花超讨厌吃本帮菜。她觉得太甜,太腻,吃一口菜就会毫不遮掩地灌一大口水。
她也受不了南方没完没了的雨和梅雨天永远拖不干的地。
我有天没忍住,问她那你干嘛来上海呢。她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工作啊,不为赚钱谁会来啊。
我那时候很好骗,还真的相信,她大动干戈换城市换公司是为了更好的前程。
她跟每个人都是这么解释的,我们也真的信了,包括她的前任。
她前任是地道的上海人。他跟阿花异地恋半年,两人总隔着电话吵架,阿花觉得这不是办法,就说我要搬到上海来。
他试图制止她,他说上海很潮的,你能适应吗?
阿花说瞧不起谁啊,我不潮吗,我不时髦吗?
前任长叹口气,他说我的意思是上海很潮湿的……
这是一段牛头不对马嘴的恋爱。所以阿花搬到上海两周后,前任就开诚布公地跟她讲,我们还是分开吧。如果阿花能够像普通的爱卖乖的女生一样说一句“你看我为了你……”,或许负疚感还能让他们再拖一阵子。可是阿花说不出来,她用刚学会的一句上海话讲:“好的呀。”
谁也不知道那个湿冷的冬天她是怎么熬过去的。阿花住在上海的老公房里,室内比室外还冷,空调费用又太高了,她舍不得开,为了蹭空调,她就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回到家,蜷在被子里继续改方案。她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朋友诉苦,为了一段生死未卜的感情跑到陌生的城市却分开,这样的遭遇很难不让人说一句“我早就跟你讲了”。
阿花高烧的时候想,会不会她死在公寓里,都没有人发觉。
好在春天总会来的。当上海的三月份,姆妈们不再追着小孩子穿棉毛裤的时候,阿花认识了一个新的男生,她跟他说,我是为了上一段感情来的上海。
男生被她的故事感动得稀里哗啦的。阿花只是平静地讲,平静到,她甚至有点惊讶于他的感动,这有什么好感动的呢,她想。

就像战争总会给幸存者留下一些烙印一样,从绝境里活下来的人,心脏上总会结一层硬痂,别人看他们的故事觉得动容,他们自己却是真实的无动于衷。但无动于衷也是一种保护,有时候你控制不了事态的变化,你只能盼望自己无动于衷。
而在困境里的人,其实不需要什么多余的安慰,只需要说一句,“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