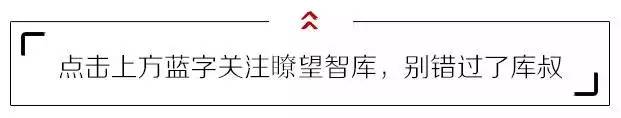

号称一纸报告就能摧毁一个国家的穆迪,日前以中国面临的经济与金融风险为由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与日本、沙特阿拉伯、捷克等国同级。
这是中国自1989年以来首度遭遇穆迪降级。穆迪给出的相关依据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未来几年很可能放缓,导致经济更加依赖政策刺激,这样的刺激将导致中国债务的上升,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财政实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而经济体系的整体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相应的改革计划难以对冲上述负面影响。不过,穆迪将其对中国的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
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般情况下会在中长期推高一国的国债收益率,助推所有债券的收益率。这等于向市场喊话,中国借钱的成本有可能越来越高,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加息,区别在于央行加息会吸引资金,而评级机构调低主权信用评级会引致资金撤出中国。
中国财政部在回应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一事时,认为穆迪高估了中国经济的困难程度,同时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而外媒代表性的评论是穆迪此举凸显中国面临的挑战。
其实穆迪在今年3月2日,即“两会”召开前夕,就宣布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前景展望,由平稳降为负面,其给出的理由也差不多,例如政府债务上升、外汇储备下降以及推进改革的不确定性。
那么,一个普遍的问题出来了,穆迪的评级到底靠不靠谱?客观性究竟如何?它是醒脑药方还是工具推手?
文丨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穆迪的评级体系究竟靠不靠谱?
毋庸置疑,成立于1900年的穆迪是当今世界最为权威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之一,与标准普尔和惠誉并称为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垄断着全球信用评级业务。
而信用评级作为现代金融市场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参与者,其好坏程度直接关系到市场对从普通参与主体到国家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的即期信心和发展预期。
说白了,信用评级机构给出评价,是作为独立服务性中介机构对市场参与主体以及金融产品发行主体进行风险综合评估,进而通过简洁的符号表示对其履行经济承诺能力和可信度进行等级划分,从而提供给市场主体作为决策参考。
正如经济学研究必须要有偏好(或者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一样,穆迪在对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信用进行评级时,也必须有参照系和分析工具,简单来说,既要看基本面,更要通过数据和评级模型,来导出评级结果。而所有这些,除了机械性的软件处理之外,就要通过分析师的脑和手来实现。
换句话说,即便是任何看起来相当客观、非常中立的评级结论,其实都离不开基于分析师偏好的某种“加工”。因为对一国或者企业即期或者远期经济信心或者风险的评估,是需要语言表达的,虽然这种语言表达需要结合数据与评级结果,但有关措辞与风险描述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夹杂着各种偏好。
因此,尽管任何一个懂得金融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信用评级结果可能既靠谱又不靠谱,但由于基于权威评级机构的报告是市场交易的重要参考,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早在32年前即认可穆迪等三大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实际上是赋予了穆迪等机构垄断地位。于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穆迪更是长期握有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
而且由于三大评级机构之间既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又不乏利益冲突,因此,它们给出的评级结果往往又不一致。有时候甚至出现基于利益驱使的荒谬评级,造成投资者承受巨大损失的情况。
此外,三大评级机构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国际顶尖投行又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以及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商业银行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构成了美国赖以主导世界的机制化霸权体系。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造成三大评级机构尽管被公认为最专业和最具前瞻性的市场中介,但预测不准以及自我纠错动力不足也时有发生。
尽人皆知,三大评级机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无一发出预警,倒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早在亚洲经济被广泛看好的1994年即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1996年克鲁格曼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危机终于在1998年爆发。
另一典型案例则是2001年安然事件,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安然及其合伙公司正式调查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将其列为投资级;然而到其破产前的第4天,三大评级机构迅速将其评级连降三级,安然的信用评级迅速跌至投机级,进而引发了安然被投资者抛弃,股价在2001年11月30日当天跌至每股0.26美元。
至于三大评级机构在雷曼兄弟破产、希腊债务危机乃至欧债危机过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更是遭到了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有人拿标普当年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A”降至“AA+”的破天荒之举来说明三大评级机构的独立和客观性。但实际上,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问题上向来慎之又慎,不至于太放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唱点“双簧戏”,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们很快可以上调这种评级。
一言以蔽之,穆迪们何时出牌,如何出牌,基于什么目的出牌,这些主动权都掌握在它们手中。
2
为何选择在目前这个窗口下调?
穆迪选择在中国大力整顿金融业,排查金融风险点,以清理金融业长期以来的发展沉疴的微妙时间窗口,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肯定不是时间上的偶合,而是剑指在西方竞争对手眼里堪称“巨无霸”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庞大且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国资体系,无论是业务规模还是市场活力乃至自我调整能力,都远远超过前苏联时代的国资力量。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中实力绝对不容忽视的一股庞大力量。
但在中国早已融入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今天,这股力量被美欧和日本的产业与金融资本视为“异类”力量,且它们在与中国同行的竞争中并未占据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入下风。
对于全球产业与金融格局竞争中的上述变迁趋势,长期“吃这碗饭”的穆迪可谓洞若观火,亦深知中国国资体系的软肋以及在中国经济中的极其重要地位。
因此,穆迪选择在中国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并采取空前行动扎紧金融篱笆的微妙时刻,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其目的很值得玩味。
事实上,穆迪已经将中国超过一半的国有企业的信用评级置于“中等信用风险”级别,若再下狠手就是“垃圾债”级别了。而以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为代表的中国国有企业最近两年在海外发行了上千亿美元的债券,这当然让美欧企业很不爽。穆迪在此时出手,意在封堵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渠道,大大提高中国企业发行美元债券的成本。
3
中国的债务风险究竟有多大?
债务安排既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推手之一,又是滋生系统性经济风险的毒瘤。因此,在经济发展中,既不能不借债,又不能“无债不欢”。
那么当今中国的总体债务风险是否已经到了穆迪在5月26日所警告的“中国结构性改革不足以阻止债务上升,有可能再度下调对中国的信用评级”的地步?这需要基于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进行分析。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相关数据,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国总体杠杆率为255.6%,而同期美国为255.7%,英国为283.1%,法国为299.9%,加拿大为301.1%,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为372.5%;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为279.2%。这说明中国总体杠杆率尽管已经不低,但在主要经济体中还是相对较低的。
而就杠杆率的变化趋势而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国总体杠杆率同比增幅较上季度末下降2.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保持下降趋势;环比增幅较上季度末下降1.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季度保持下降趋势。
至于一般认为比较严重的企业杠杆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最新数据,中国2016年三季度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2%,较上季度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19个季度上升后的首次下降。2017年3月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企业微观层面的杠杆率也呈下降趋势。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上述这些数据分析就认为中国没有债务风险,而应看到我们当前在债务领域确实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必须正视可能的风险。
1994年,中国的总债务水平为GDP的78.6%,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负债率已与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相当。
但是,美国人均GDP高达5.59万美元,相当于中国的7倍,且早已建立了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相形之下,中国迄今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即便是在号称经济最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且宣称淡化GDP考核指标的上海,依然有不少人的年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换句话说,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未富高负债”的典型代表。
格外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中国没有美国那样足以向外辐射或者转嫁国内经济发展成本的通道,一旦爆发债务危机,相应风险都要在国内消化。例如,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主要就是国内经济问题,因为外国投资者并不持有中国的债权,使得业已占到GDP规模二分之一以及银行资产五分之一的影子银行资产问题成为高悬在中国头顶上的一颗经济炸弹。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绝大部分净资产为房地产,中国去年超过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的内在结构中,仅仅房地产行业所占的比例就在四分之一左右,比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前的比例还高。天量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使得各级各地政府普遍患上房地产依赖症,房地产不仅成为事实上的经济鸦片,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支柱产业,也是蕴藏极大风险的高危产业,早已形成对整体经济的绑架,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将对整个经济系统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成为爆发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暴眼。
房地产狂热、地方政府融资以及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体系已将中国深度绑定在债务拉动型经济列车之上。中国也许再难像过去那样在西方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可以通过加大杠杆率来对经济进行热启动了。
尽管中央层面的资产负债表目前相当健康的,这也是从官方到部分市场人士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大规模债务危机的底气所在。此外,政府手上还掌握着不少可以变现的资产以及可以开辟潜力的税源。但即便是世界上最为强大、最具动员力的政府,恐怕也无法做到对财务窟窿越来越大的地方经济全面托底。
自2008年以来,我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膨胀的速度非常快,不少银行为了掩盖信贷的高速增长,大力发展表外业务、理财业务、通道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委外业务。这些表外业务如今成了银行体系的黑洞,隐藏着不确定性风险。
于是危机意识敏锐的银监会,最近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目标直指银行的表外业务。
中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上处于债务扩张与债务消化赛跑的境地:假如债务扩张能够被逐渐消化,则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反之,若债务消化的速度赶不上债务扩张的速度,则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就在增大。
目前看来,留给中国避险的时间并不充裕。各地投资饥渴症依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未来财政收入不大可能呈现大幅度持续增长,而中国也不要指望能够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对外辐射经济风险。
因此,关键之举在于:一方面,各级各地政府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提振内需等方面有真正突破,将中国经济切换到内生性增长轨道上。另一方面,中国必须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新的市场化平台。更要大力培育新的市场投资主体,有序增设民营银行,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推进深层次金融改革。
4
如何提高金融危机早期预警能力?
从风险预警的角度而言,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风险也可被视为一种“另类提醒”。使得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经济体系中的风险因子,并采取切实行动予以防范。
因为鉴往知来的教训已经警示:即便是最为强大的美国,也无法确保本国经济长期运行于高杠杆债务区间还能与债务危机乃至系统性金融危机绝缘。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充分表明:金融过度深化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最终会对经济体系造成摧毁性的破坏。
中国尽管在防范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方面拥有较丰富的经验积累和较强的财力工具,但金融危机的重要特点在于其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破坏性。
正如拥有最先进预测技术的地震局也难以做到精准预测地震一样,我国必须未雨绸缪,对可能面临的风险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必须高度重视企业高杠杆率的危险性与复杂性,严控债务风险。
“信贷差距”基准被视为观察金融危机的一个有用的早期预警指标,它衡量的是企业和家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和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从中可以看出当前和历史借款规律之间的差异。我国目前的信贷差距已经远超10%的担忧值。
为此,必须尽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进行全面清查,确认问题贷款的数额,那些被银行移除资产负债表的问题贷款必须计入不良贷款,以确认真实的不良贷款率。
2.应当保持货币发行的工具理性。
任何泡沫的渊源都可从货币政策那儿找到影子,化解资产泡沫需要正本清源。就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而言,无论是暂停土地拍卖还是从销售终端抑制购买的调控措施均属于治标不治本,甚至会向市场发出更大的价格反弹预期信号。
建议对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最近十年来的房地产市值走势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纽约、东京、伦敦、香港等国际指标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曲线的历史走势,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变迁,审慎评估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程度,给出一线城市房地产的相对均衡价格,严控房地产信贷风险。
房地产泡沫的治本之策,是各级各地政府必须戒除“房地产”作为经济“鸦片”之瘾,消除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
3.守住 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安全底线。
人民币汇率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动态竞争力的体现,更是主导性金融大国和国际金融资本试图对我国进行战略锁定的重要目标。
鉴于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进程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国家竞争战略,且有欧元的前车之鉴,建议国家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密切跟踪国内外交易主体的相关行动,特别是表外资产和表外交易,以及这些交易涉及的外储资产规模和金融杠杆,切实做好风险管控,保持较为充足的外储流动性头寸(不低于6000亿美元),稳守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安全底线。
4. 必须逐步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避免陷入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怪圈。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作为皮与毛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颠覆。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存在,而非绝对主导力量。
5. 微观主体创新禀赋的广泛激活是对冲金融危机风险的重要依靠。
当下,全球科技发展正发生不完全以政府规划为静态指标参照的变化,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以及现在看起来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性企业,其在跨产业整合方面的延伸能力,其对人类未来消费体验的前瞻性研发和测试,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
正如苹果、谷歌以及中国的华为均非政府规划的产物一样,各级各地政府所关注的,应该是如何做好幕后工作,营造更适宜的创新生态环境。
学术合作联系人:聂智洋(微信号:i87062760),添加时请注明:姓名+职称+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