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1-201
从1月15日至今,偶然的因素,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被“留”在了疫情阴影下的上海。之后的日子里,他相伴于她的身旁,时时感受着疫情中的特殊上海,火热的心和激情的泪,随这座城市一起跳动和流淌……
“心疼时,我会慢慢地靠近窗口/看看你是否还在流动/其实你一直在流动/而我却在担心哪一天/你不再流动……你在流动/我生命的热血就会随你而动/你在流动/这座城市就会力量无穷……”在诗歌《致黄浦江:你是否还在流动》中,何建明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黄浦江、对上海这座城市、对身边百姓的挂怀。
“写到悲情,我的眼眶常常盈满了泪;写到趣事,我也会开怀大笑;写到温暖,我会肃然致敬大上海……”何建明的新书《上海表情》,是他对上海的一份礼赞与感恩。既是这座伟大城市和2400多万人民战疫的表情,同样也是他在其中的一些悲喜之情。它是真实的,有时是悲怆的,更多的是痛苦与感动交织的复杂情感。与此同时,何建明的第二部抗疫著作《第一时间——写在春天的上海报告》即将出版。
《非典十年祭》中,何建明曾经提出:“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有时我想想这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何建明在文中疾呼,“我们的社会应当严肃考虑这些问题。从管理体系到灾难预防能力,从公民意识到灾难资金的投入。但是,非典过去10年,真的有再深思熟虑这些问题吗?——苦难和死亡早晚还会向我们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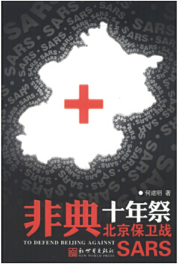
中华读书报:
近几年,您先后为上海写了《浦东史诗》和《革命者》两本报告文学,目前又在写以上海“抗疫”为主题的作品,是什么留住了您的眼光和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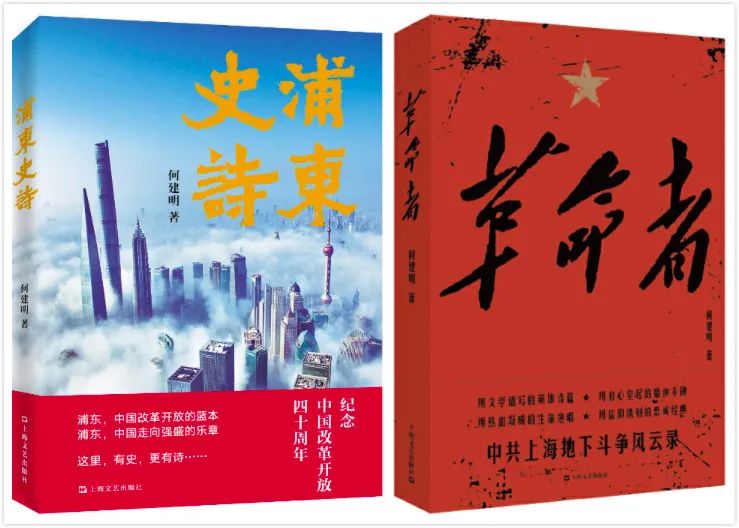
何建明:
写完《浦东史诗》后,我有种很强烈的感受:中国作家过去一百年基本的努力都在进行传统的“农耕社会生活”叙述和书写,而且也确实创造了许多高峰,从鲁迅到莫言,几乎都是写农村的。城市书写当然也有些,比如巴金、张爱玲等等,但这些作家笔下的城市基本上与现代城市和当下中国的城市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的中国城市之发展和变化,以及随之变化中的新城市人,可以说是当代生活最精彩的时代画卷。《浦东史诗》的书写过程,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点:这30年的新上海生活的丰富性、多彩性和深刻性,足以产生多部经典作品,然而我们没有多少与之相称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我一直认为,创作确实需要沉淀。然而如果与其等我们快进坟墓时去品着茶在草地上回味年少时的往事,还不如现在去拥抱正在发生着的那些燃烧到我们筋骨的现实生活、去书写当代的火热生活。
也正是这个原因,前年和去年写完两部重大题材后,我持续关注上海。我发现这个大都市里有一些年轻人生活得很优越,家庭条件也好,学历很高,但他们因为个人的自私、自傲和孤僻,结果走上了高智商的犯罪道路。1月15日我到上海采访这方面的事情,正巧与上海疫情的“一号病人”擦肩而过,之后就被“留”在上海度过了整个疫情,至今仍在上海。
本来是被动的“宅”在上海,远远地“隔岸观火”,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上海也面临着惊心动魄的“疫”战考验,我也亲历了疫情中的许多感受深刻的事情,决定投入到“疫”战创作……结果一投入,就再也出不来了。现在上海也成了中国防控境外疫情的最前线,我就干脆直接进入了主战场的生活与采访及创作。
中华读书报:
最新完成的作品《上海表情》,是一部怎样的作品?为什么叫“表情”?
何建明:
《上海表情》大约20万字,写了从我1月15日与上海“一号病人”同时进入上海一直到3月10日我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这段时间我孤身一人被“留”在黄浦江边的一家酒店,可以说,在疫情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上海人能够像我一样专注地凝视着黄浦江两岸的风云变幻……一个24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在瞬间看不到一个人、街头见不到一辆车、听不到另一个人与你说话,外面的天还时不时地下着寒冷的雨,许多时间我独自站在窗口,凝望着黄浦江,直怀疑它是不是还在流动。因为武汉疫情大爆发后,国内外有不少机构认为上海可能是中国第二个疫情大爆发的城市,而且还有人估计上海一旦全面爆发疫情,感染人数应在80万左右。这是多么可怕的预测啊!这种预测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我的心也随之紧张,甚至怀疑是不是回不到北京了?这种念头在疫情严重时是曾有过的。所以那些日子,我经常一个人走出酒店,在黄浦江边、酒店附近独自观察大上海——绝对别样的感受。我见了快饿死的野猫群,多次经过没有人的大超市,无目的地走在那些灯火辉煌但人去楼空的摩天大厦之间,那般恐怖与恐惧,非言语所能形容。尤其是我原以为自己经历过北京“非典”,以为武汉疫情,大概与2003年“非典”情形与结果差不多,所以实在想不到后来越演越烈……直到死亡人数超一千、两千时,真的有种绝望之感。
但后来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十分吃惊:上海的疫情竟然控制得那么好!上海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那种果断、迅速、细致、细心和智慧,着实令我内心强烈震撼——我待在上海多么幸运呵!
为了这份幸运和安全,我必须要表达……于是有了想写一部上海“疫”情的纪实作品。它既是我的亲历和重要的感受,同时也有很多上海战“疫”的精彩故事。
中华读书报:2003年非典时期,您也在一线采访。和那个时期相比,您的心情有何不同?
何建明:
“非典”时,我还年轻,毫无畏惧之感,第一个提出来到前线去采访,一个人居住在隔离的小房子里,整个创作处于亢奋状态。不能回家,就整天吃方便面,现在血糖高就是那两个多月的前线采访落下的病症。
这回不一样了。我觉得不会再像当年去冲锋陷阵了,尤其是新冠肺炎病毒专攻5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我想我的呼吸道又不太好,别传染上“光荣牺牲”了,那样太可惜了:我还有好多作品没写完呢!这是真实想法。没想到我还是冲到了前线——当前防控境外疫情战斗异常艰巨,上海动员10万人在阻击,我身在其中,怎能当旁观者?
既然是一名现实生活的“记录者”,就不能平时伟大、战时怂包呀!后来发现我还是一名“冲锋的战士”,或许永远是吧。
中华读书报:您在上海两个月了,这段时间生活和写作状态怎样?
何建明:
到3月15日,在上海整整两个月。虽然孤独,但也充实,因为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写作,甚至因为没有其他事干扰,我的“成果”比平时还要好。
在悲痛和悲怆的时候,我写了好几首诗。比如《见到太阳,真好》《致黄浦江》等。发表后好几位艺术家配乐朗诵,在上海传播不小。也被湖北和武汉文友拿去阅读和传颂。这是意外收获。我觉得只要情真,都可以写出好的诗歌。
中华读书报:从《浦东史诗》《革命者》到《上海表情》《上海筋骨》,既有对这座城市的纵深了解,也有瞬间的表情记录。
何建明: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疫情,让我与上海这座我热爱的城市,竟然共同度过了几乎整个“疫”期。《上海表情》之所以要写,完全是“意外收获”,或者说完全是一次不同状态下的激情投入。我自己以为在上海“度疫”可能是自己所能做得到的最好选择,因为“宅”在家也是战斗——大家都这么说。可是,后来疫情的发展和上海的战“疫”确实感动了我,也有许多在“疫”中所经历的事太令我无法平静与“宅”了……于是,许多时间我悄悄地走到大街上、走到黄浦江边、走到商场和码头,去感受“疫”中的上海。当然我也一直在把自己身处的上海和武汉作比较,并且不断受到来自大上海的那种因为细微的关怀而温暖、因为决策果断而看到的不一样的结局、因为准备充足而不惧风浪袭击的实力等等,如此这般,我发现自己这60多天变成了一次最完整和最充实的“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过程!《上海表情》就此在笔下“滑”了出来。
中华读书报:疫情如此严重,您在上海的采访是如何完成的?
何建明:
最近一段时间,我主要在采写上海疫情以来的“正面战役”,尤其是采访防控境外输入方面的事,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安排下直接到现场去采访,相对方便得多,当然危险性也不小。
《上海表情》一书的采访,大约是两种形式:一种是我在上海疫情中的所见所遇,本身就是我的生活。另一种是“疫”情中的上海情况,这一部分主要靠我的观察和可以获得的媒体新闻,再有就是上海各界许多朋友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所以能够获得全上海战“疫”的全局情况,也有不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宝贵。
中华读书报:您在“非典”十年时发表的文章一再被提及,这说明什么?
何建明:
没想到在此次“疫”情中当了一回“网红”。不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文学其实有时也能起到对时代的警示和推动作用的。有一种说法,认为报告文学或其他文学“边缘化”了。事实上真正写好了,读者是会记住的。七年前祭奠“非典”十周年,我在重新出版《北京保卫战》一书时,对“非典”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了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其实我们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比如乱吃乱为、不注重国民素质培养等等问题,所以那本书的前言,写到了不少反思性的话语,讲到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地反省暴发“非典”的原因和问题,就必定会早晚重演新一场的“非典”灾难。这样的结论,我不仅在书中写到,而且后来凤凰卫视做专题片时还专门谈过。此次疫情发生,又被人翻了出来。
我想文学参与社会建设是一件重要的事。昨天如此,明天仍然是这样。其实这类反思性、批判性的现实作品,我以前写过不少,如《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南京大屠杀》《忠诚与背叛》《爆炸现场》等等。
中华读书报:您一向比较注重文体创新,在这次的写作中,除了真实的记录,写作手法上有何讲究吗?
何建明:
这次写作,与平时写的“报告文学”不太一样:既有波澜壮阔的战“疫”大场面,又有我很个人化的“私情”,比如写与“流浪猫”的交情、写在“疫”情风口浪尖上的钟南山、高福这样的熟人,都比较“散文化”“自传化”“个性化”。我觉得不同内容,用不同手法表现,是所有文学体裁的一种“常规”,也应该是我们追求创新的一种必然的方向。情在此,特别重要。其他的可能就该退到一边。
中华读书报:通过记录,您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何建明:
人活着不容易。每一个人活着应该有自己的内容,有自己的精彩。这很重要。遇到过灾难和没有遇到灾难的人,对同一问题和生命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很不一样。反省是必要的。有些特别的收获,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懂得了什么事以后可以做、有的事就不能随心所欲了!总之,人类在自我成长和成熟中不能重复犯低级错误。
医生!作家!武汉……
这些关键词,足以使池莉和武汉一样在这特殊时期被瞩目。
“我与武汉的关系,是狗与狗窝的关系:无论我经常跑出去和跑多远,我都要回来;回来嗅嗅,是无比熟悉的气味,在窝里扒拉扒拉,很快就香甜入睡,连睡梦都充满写作激情。”池莉在散文中如此亲昵地表达自己对武汉的依赖之情。如果说她的文字中有一股血脉流淌,那便是长江或者无数湖泽。因此有人说,池莉的作品就如同一幅幅武汉的风情画。
如今,她的武汉病了。
作为一个有过医学经历的作家,池莉和她的作品一样兼具理性敏锐与充满智慧的热情。哪怕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她也保持着客观冷静的心态,时时现身说法,以医生的身份冷静地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她做过三年流行病防治医生,清楚地知道传染病对人类生命的吞噬是何等迅猛,何等地让人猝不及防。流行病防治的基本以及根本要义是“四早”,尤其是“早隔离”,对于阻断烈性传染病至关重要,只有最大可能地进行严格阻断,病毒才有可能失去传播链条,直至失活。所以,接到隔离通知后,池莉首先是严格做好自己的隔离,她将家中食品蔬菜分为十四天的等份,争取不因为买菜而必须外出。道理简单通俗:如果每个人都心存侥幸,那么这个巨大的城市和巨大的人群就有可能在隔离期间被更加广泛地再次传播,“封城”将会前功尽弃。
但是,池莉仍然注意到,有的人,正是出去买了一次菜,受到了感染,一个人又传染好多人。“人们一边自我破坏着隔离,还一边以爱的名义、情的借口,大肆地泛滥爱与情……超市还在卖菜,是大爱无疆;小贩出摊卖菜,也是生活情义;为了全家自己外出买菜,正是无畏无私的大爱。”她大声疾呼:“爱与情,都是好东西,然而绝对不可以滥用,尤其此时此刻。人啊人,醒醒吧!为了你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也是为了我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安全,能够不能够闭上嘴管住腿呢?能不能多做一点有利防疫的具体事情呢?”“隔离就是战争!战争必须让愚蠢无知廉价的爱与情走开!唯有将严格隔离坚持到底,人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当新冠病毒仍在肆虐,武汉出台了疫情爆发以来最为严格的隔离严控措施。每天,池莉给父母电话报平安,与亲朋好友通微信,叮嘱一线医生朋友做好个人防护,请染病住院的朋友加油康复。还有远方的,国外的,平时都不大会紧密联系的,现在几乎日日问候,不见字不放心。
这一天,她正站在窗前,听见窗外有位老人在哀号:“某时候才是个头哇——某时候才是个头哇——”
“我立刻冲到窗前,打开我家窗户,寻求老人目光,向他摆手摇手,‘喂——爹爹’我使出最温和安详的嗓音,与他打招呼。”焦虑不安的时候,哪怕陌生人的问候也是温暖的慰籍。老人听到池莉的声音,终于关上窗户进屋了。她仍不放心,又给物业打紧急求助电话,请他们查看楼上是否有孤寡老人,是否发生了困难。“如果老人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家有,请一定送过去。”池莉的恳切之情感动了物业,他们答应立刻派人查询。
那是隔离的第28天。池莉很清楚,焦虑和急躁开始在人们心里蔓延,我们需要对付更多敌人,包括在自己心里逐渐扩大的阴影。她说:“因此我们能做一件事情,就做一件事;能帮一个人,就帮一个人,底线是我们首先做好自己。这个时刻,真正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时刻,我们得靠每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成人类的强大意志,把我们的生命夺回来!”
疫情发生之后,池莉连日呼吁到声嘶力竭,然而食品蔬菜的套餐式配给制的无接触配送,还是难以实现。她从一个又一个视频里看见超市人头涌动摩肩接踵,唯有仰天长叹。邻居中有人积极赞同池莉的严格隔离的观点,动用了个人资源,到处联络蔬菜公司,替大家配好蔬菜套餐,做到了无接触采购。“领取了蔬菜套餐,大家在微信里笑了,随之我们互相鼓励和打气:再坚持个14天没问题!就是这样普通的一句话,就是那些枯燥的网购链接与APP,在这个非常时刻,竟然闪闪发光,温暖感人,让我瞬间泪目。”池莉感慨:“其实大家所在城市,也都面临疫病威胁,每一个人自身,也都有一定危险,但大家就是这样,时时刻刻陪伴和帮助我们;什么叫做相呴相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袍泽之谊?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
围城中的池莉,以她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和细腻真诚具有力量的文字,向读者、向她身边的人,最大限度地传递着善意和温暖,传递战胜疫病的信心与希望。她疾呼:“病毒已让世界充满了恶,作为人,当以善来抵抗。该是检视自己的时候了。该是抑恶扬善的时候了。每一个人,你做好了自己吗?总之我在努力地做。传染病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传染和病的理解。生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世界也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世界观……如果说六十多天好难过,最难过的在心里。”

在去年完成的《大树小虫》中,池莉一次次耐心细致地为我们描述着小说中的“人物表情”。她认为“人物表情”对于我们民族的性格来说,是内心独白的一种符号。一般能够说出口的话语,往往不是我们的真实内心。而表情,则是更为逼真的、无处逃遁的内心符号。此次疫情,池莉的文章为我们呈现了更为丰富的武汉表情,那就是善良、坚韧、勇敢、博爱。
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相信不久的将来,定如池莉的诗歌《人的生活方式》中所写:在那时候/人的眼睛以花瓣的形式/面对万物/那时候/花朵将成为人的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