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
出版了80多年,其中很多论断历经时间检验而熠熠生辉。格雷厄姆和多德都坚
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而且重视逻辑而非规则。他们认为应当在全面分析的前提下理智地承担风险,而不是潜意识地一味规避风险。他们提出的关于固定价值证券的四条原则,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最近空闲的时候又把格雷厄姆和多德在
80
年前著写的《证券分析》一书通读一遍,尤其是其中关于固定价值证券方面的论述,甚是精彩。有两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在固定收益证券领域,美国在
80
多年前的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领先于我们,诸多证券品种在国内目前仍是空白;
第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金融市场走过多轮周期,市场跌宕起伏,泡沫膨胀时令人得意忘形,危机肆虐时使人沮丧绝望。起起落落的市场给了格雷厄姆关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坚定信仰,其投资哲学也经历了市场残酷的考验而愈加历久弥新。因此,他的一些见解被视为圭臬,历经时间长河的洗礼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书中关于固定价值类证券的四条投资原则的论述,读起来有醍醐灌顶之感,仍然可以作为当下进行信用债投资的指引。
(格雷厄姆书中所指固定价值证券包括:高等级普通债券与优先股;高等级特权证券,但特权价值太小,在选择证券投资时不予考虑;通过担保或优先权而具有高等级优先证券地位的普通股)
规则一:证券的安全性不是由特定的抵押权或者其他合同权利来衡量,而是取决于证券发行人履行义务的能力。
关于不应该过分倚赖抵押品,格雷厄姆给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企业经营失败时资产价值会随之缩水;
第二,债券持有者的法定权利在维护过程中会遇到困难;
第三,破产清算过程会存在延误和其他不利事件。
我的理解:格雷厄姆已经将原因讲的很透彻了,核心就是一般来讲,抵押品和企业的基本面是正相关的,寄希望于在企业挂了的时候通过抵押品处置来获得清偿是多么不切实际,因为这时候的抵押品可能一文不值,遑论处置过程的漫长和一堆糟心的事情。
更何况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时候不是你想处置就处置,首要还是要讲究社会和谐稳定。想想被股票质押坑惨的兄弟们吧,这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当然,我觉得有一些情况可能是例外的:
第一,当“抵押品”是由非相关第三方提供的担保等增信措施。但在这种情况下,本质上我们也没有依赖“抵押品”,只不过是将分析对象从发行人转向了提供担保的第三方。我们对“抵押品”的认可其实是对于非相关第三方基本面的认可。
第二,当“抵押品”与证券发行人的基本面相关性很弱且其价值比较稳定。例如证券发行人通过提供非常优质的房产等物业进行抵押,那么这种抵押品是比较有效的,但也不能完全放弃对发行人基本面的分析。因为虽然可以通过抵押品的处置获得全部或者较高比例的清偿,但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
规则二:应重点考察经济萧条时期的履约能力,而不是经济繁荣时期。
我的理解:如果一个发行人能够穿越周期而发展壮大,那么这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作为投资人,你至少需要保证在你的债券存续期内,这个企业是安全的。那么,应该观察的是这个企业在经济下行周期的表现,而不是盯着景气阶段的情况。
过于关注景气阶段往往会得出乐观的结论,毕竟在繁荣期猪都能上天。只有潮水退去的时候,才能发现谁在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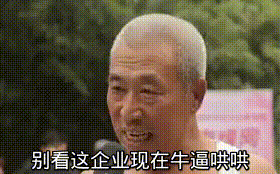
关于规则二,引申几个小问题。
观察期限、新兴行业和新兴商业模式?
要考察企业在不同经济周期的表现,就意味着对企业的观察期限要足够长,最好能够覆盖经济景气和萧条阶段。那么,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一个企业是刚成立不久,那么就要谨慎。因为它还未经历过完整的周期。第二,同样道理,如果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或者新兴的商业模式,那么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现在看起来大红大紫,可能仅仅是因为环境好,一旦经济环境恶化,可能就会暴露出问题。在
ABS
领域有很多这种新业务、新模式和新企业。
相同的,如果一个企业进行了转型,尤其是跨界转型,无论是通过收并购还是自我发展,对于债券投资人都不是好事。因为按照这条准则,转型尤其是跨界转型,意味着进入了新的领域,而企业在这个领域尚未经受周期的检验,是非成败尚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承担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
债券投资是否应当具有前瞻性?
我觉得是需要的,但要区分不同情况。在不考虑杠杆和无风险利率下降带来的资本利得情况下,投资债券获得的收益主要来自于票息。我们要尽可能确保企业能正常还本付息。这使得我们会更加谨慎。无论是对于宏观经济、行业周期还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判断都是必须的,但这要区分不同情况。如果对未来的预计是乐观的,那么这种乐观情况要打折扣甚至不纳入我们当前的判断;如果对于未来的预计是悲观的,那么这种悲观情况需要全部纳入到当前的判断中。也就是说,我们较少对乐观的前瞻性判断做考虑,但对于悲观的前瞻性看法,则需要全部纳入。这都是源自我们投资债券的谨慎性原则,我们重点考察的是企业在经济萧条和低谷期的履约能力。这相当于一种压力测试。
不同行业的安全标准是什么?
对于不同行业,从财务指标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确定其临界值,以便我们观察具体的企业其安全边际有多少,对于周期性强的企业,我们要求的安全边际可能会更高一些。比如,
EBITDA
利息倍数在多少是合适的,如果是强周期行业,我们应该将这个指标提高多少。
规则三:异常高的票面利率并不能弥补安全性的不足。
我的理解:信用债的利率大致上是由无风险利率
+
信用利差
+
流动性溢价构成,信用溢价是给予债券投资人相较于国债等无风险债券的信用风险补偿。这就是说,在给定的某一时点,无风险利率大家都是相同的,异常高的票面利率就意味着过高的信用风险,而且往往这种“信用溢价补偿”和你实际承担的风险并不匹配。想通过承担较高的信用溢价来弥补安全性的不足往往事与愿违,除非你能够做到足够分散并且运气还不算太差。
俗话说的好啊,你看上的是人家的票息,人家看上的是你的本金。
这条准则也
意味着信用资质下沉往往是最次的选择,透露出投资经理的无奈与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