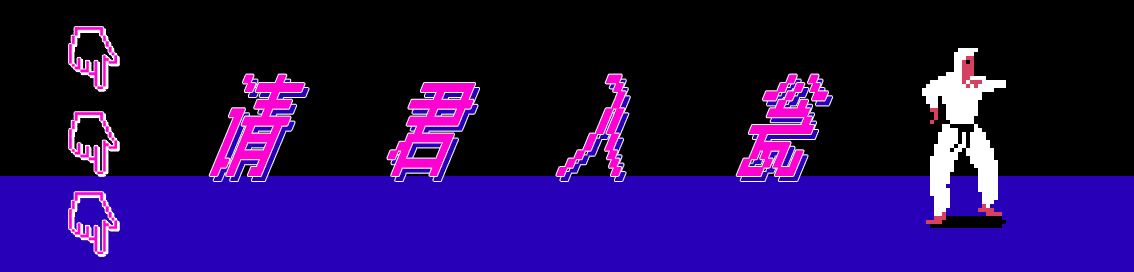利维坦按:“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提出来的,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将其称为自然选择(既最适者生存)。对于进化论乃至之后的新达尔文主义的争议一直就没有断过,有来自生物复杂性的质疑,也有来自观察和证据的质疑,还有对进化随机性的质疑……虽然老师会经常提到进化论,但作为科学依据,却很少被写进教科书中。
看过《物种起源》的都知道,达尔文的确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他自己也说过,“如果有人能证明所有存在的器官不是由无数的、渐进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理论就彻底崩溃了。”理论有漏洞实属正常,正是基于对漏洞的质疑,才会形成有益的补充——比如今天的这篇文章。
文/Kelly Clancy
译/半打
校对/石炜
原文/nautil.us/issue/46/balance/survival-of-the-friendliest?utm_source=frontpage&utm_medium=mview&utm_campaign=survival-of-the-friendliest
“暴力统治着这个世界,”1940年,诗人罗宾逊·杰菲斯(Robinson Jeffers)写道:“你看除了撕碎羚羊的狼牙,还剩什么?除了用恐惧折断飞鸟翅膀、目光凶狠的苍鹰,还剩什么?”
我们深深铭记着这些进化论的隐喻,把它们理解为生命就是一场杀戮或者被杀的竞赛。“达尔文主义”代表着“断颈割喉”,“适者生存”象征着唯残酷得幸存。我们看到物竞天择的压力使有机体奋力夺取成功,驱使基因革新成为万物的自然秩序。

进化的两种模式:“互利合作”是对早期达尔文进化论“你死我活”思想的补充。
但现在我们知道,上述的图景并不完整。进化的历程既可以通过适应环境的优胜劣汰来推动,也可以因为宽松的自然选择条件而发生。当自然选择对一种有机体的作用不是那么强烈,变异的创造力就能释放,进化因而加速。更轻松的生活所带来的解脱,和死亡的威胁同样有力,能激发新的生物形式。
减轻竞择力度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力合作。用数学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的话说就是“抱团求生(snuggle for survival)”。新的研究恰恰加深和拓展了合作的重要性,并缓解了竞争的压力。那里是一个庞大而温情的世界。

生殖成就空间(fitness landscape)模型图示意
一个种群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可以看作是种多维度空间——生殖成就空间(fitness landscape)。这一模型由该物种的能力和它周围的环境所限定。而物种在空间中的位置则是由繁育、新陈代谢、力量等参数所决定。空间中的“山峰”代表着参数空间中的一个位置,在那里的物种适应性强;“山谷”则意味着此处的物种濒临灭绝。图形的斜率(slopes of the features)也同样重要。在高适应空间中,宽广、平缓的山坡代表着该区域的种群可能变异且幸存下来;狭窄的山脊暗示着极微弱的可能性,即使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能将一个带有新突变的个体甩下悬崖。当自然选择松懈时,地形自身也会改变,陡峭的悬崖会拓展为平原。一旦选择的限制改变了某个特质,种群就能在相关特质中产生更多可能,进化就会变得更自由。
自然选择会因为环境因素而减缓,例如猎食者数量的减少。但种群也能靠自身行为减缓这种选择进程。在一个发表于2017年的研究中①,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员们通过观察“抱团取暖”这种在鼠群中格外简单的行为,尝试厘清行为和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拟建了一个鼠群,详述它们的隔热率和新陈代谢率(insulation and metabolic rate),以及它们是倾向独处还是喜欢扎堆儿。由此,他们验证了一个进化算法,即充分利用每个种群的新陈代谢消耗,以将体温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内。
并不是恶劣环境在驱使进化,而是进化使得在恶劣环境下生存变得可能。
对喜欢独处的老鼠来说,使之能有效保持足够体温的方案空间非常小。这对于种族而言是雪上加霜。首先,如果可行的方案空间有限,倚靠随机的方法进行进化就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其次,一旦找到解决办法,探索后续、潜在的有益变异也会更难。当一个物种在生殖成就空间中沿着狭窄山脊缓慢移动时,走错任何一步都可能将其推向灭绝。在研究者模型中,抱团取暖可以用来对抗对于动物隔热(animal’s insulation)的自然选择,在不危及维持理想体温的能力情况下,允许基因更灵活地控制它们的新陈代谢来。这样一来便缓和了生殖成就空间的山峰,后代可以迅速探索适应一片广袤的适应度地形,并积累更多样的变异,以提供一个更丰富的基因谱,为应对日后的环境变迁进行选择。当然,松弛选择也会增加许多潜在的有害变异,因此需要权衡。但当自然选择松懈,种群更自由地探索生殖成就空间,它们也许会更快地在大型适应性创新中栽跟头。

抱团取暖可以用来对抗对于动物隔热的自然选择
作者们将温血动物(warm-blooded animals)的进化与冷血爬行动物并行绘制。看起来,爬行动物的一个旁系在它们开始维持高体温之前,演化出一种用来松懈自然选择的隔热因素,比如皮毛或较大的身体质量。小型温血动物则面临着更大的新陈代谢挑战。因为它们容积表皮比例(ratio of surface area to volume)太高以至于它们会散发大量的热。一旦隔热发生,原始哺乳动物(proto-mammals)的新陈代谢会更自由地变异,并碰巧发现稳定的体温。而且,当这些动物“开发出”了温血模式,他们便意识到一大优势:最早的哺乳动物习惯在夜间捕猎和进食,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生态位(niches),最终产生出进化上有优势的动物。作者们认为老鼠可以通过抱团有效地形成一个“超级有机体”。共享热量使它们不必进化出更大的身体,就能在行为上接近更大型有机体所固有的好处,进而使它们能更自由地改变自身的新陈代谢。虽然计算研究让我们能模拟出需要在自然界中花上千年才能展现结果的实验,但是,鉴于任何模型所必需的假设和简化,我们必须对计算研究采取一些保留态度。
通过研究相关物种的系统发生史(phylogenetic history),我们可以开始在现实世界中,将行为的相互影响与演化动态相关联。今年,通过跟踪鸟类进入新生态系统的行为,分析鸟类之间已知的基因关系,瑞典隆德大学的科学家分析了4000种鸟类的繁育策略②。合作繁殖策略(cooperative-breeding strategies)常见于恶劣环境,这点一直广为人知。这种假设认为,困难的条件会鼓励物种进化出(至少是针对近亲的)社交行为。但如果这个假设的因果颠倒了呢?通过分析鸟类的迁徙历史,研究者们发现,那些在宜居环境中已经进化出合作繁殖行为的物种,移居至恶劣环境中的几率是没有合作行为的繁殖者的两倍。研究者们推测,合作缓和了不可预测的繁殖季节,使得已经适应群居的种群能在涌入新的生物位时更加成功。艰困的环境不能驱动行为的进化,是行为使其得以殖民恶劣环境。

生态位是一个关系网,不只在一个物种和它的栖息地之间,还在该物种和在同一空间中共存的其他所有物种之间。
我们倾向于认为生命与它的栖息地可以分开讨论:环境是一种容器,生命就像为了填满容器而去适应其形状的液体一样。阿瑟·坦斯利爵士(Sir Arthur Tansley)在1935年初次提及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概念。他相信大自然犹如一部机器或工程师,通过生命和它所在的环境,绘制出能量和物质流动的地图。但是,正如我在二年级做鞋盒模型中学到的,生态位不是未经处理的关于动物所处环境的物质参数:盐度、碱度、湿度、温度。它是一个关系网,不只在一个物种和它的栖息地之间,还在该物种和在同一空间中共存的其他所有物种之间。与坦斯利的机械观相反,生态位跟进化一样充满动态。“古生物学家常说化石记录中的多样性爆发只是‘填补生态空间’,好像每一个新物种只是要在既存的棋盘上占上一个格,”古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厄温(Douglas Erwin)如是写道③。他认为物种自己建造了这个棋盘才是更好的类推。举例来说,珊瑚通过礁来形成它们自己的保卫生态位(protective niche),以此来减缓水流并减少对自身的侵蚀。礁类同时还用作无数其他种群的居所,其中很多物种反过来进化出了保护珊瑚的行为。如果一个有机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或它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来改变它的生态位,那么它就有机会建造一个可以使后代在其中演化的世界,并将其重塑得更好以确保它们的生存。
进化不是一场军备竞赛,而是独立国家间的和平条约。
微生物研究初期曾出现过的一个谜题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案例。在19世纪,细菌学家使用温桶里的肉汁培养微生物,这在当时是尖端科技。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医师认识到这样的肉汤很可能隐匿了许多种不同的细菌。他猜测如果能给细菌一个固体媒介来生长,也许就能使不同的菌落彼此分开,并单独对其进行研究。他用消过毒的刀切开一个土豆,把病人伤口上的刮屑涂抹到土豆上,创造了第一个固体培养菌。随着不同菌落的形成,他将每一个菌落挪到一个分离的土豆切片上,但只有一小部分分隔的菌种单独存活了下来。
目前有大约98%的细菌种群无法在实验室中单独培养,这一限制不仅是单纯的学术难题:它还严重阻碍着新生物医学化合物的发现。我们最好的抗生素就是从细菌那里偷来的。经过百万年的共同演化,许多细菌已经进化出了阻挠其它细菌的有效毒素。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验室中培养大部分种类,我们就无法分离它们生产出的潜在有效的化合物。从1987年到2015年,我们始终没能发现一纲新的抗生素。而且因为细菌进化地非常快,其中许多已经对我们在过去30年间使用的抗生素产生出了抗药性。细菌抵抗研究室生长环境的原因无疑有很多,但其中首要的是细菌在自然环境中并非自给自足这一事实:它们共同演化,彼此共生。从自然选择的有利位置来看,物种需要依赖彼此来生存,看上去不太稳固。但是广泛存在的相互依赖表明,这种关系一定具有重要的优势。黑色皇后假说(Black Queen Hypothesis)就描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黑色皇后假说借用了红心大战这个游戏的名字。在游戏中,玩家要避免拿到黑桃Q,从而避免重罚
在黑色皇后模型中,有机体会摆脱一些机体功能的基因编码。因为这些功能已经由其生存环境中的其他物种提供④。这是对更为知名的红色皇后假说的逆转,后者假设的是有机体会主动参与到进化这种军备竞赛中,持续适应新的武器和防御以避免灭绝。尽管演化经常被认为是更复杂的情况,但有机体确实会经常丢掉一些基因。生物功能是通过消耗新陈代谢来维持的。如果它们不是必不可少的话,最好还是把它们排除出基因组(黑色皇后假说借用了红心大战这个游戏的名字。在游戏中,玩家要避免拿到黑桃Q,从而避免重罚)。黑色皇后假说的一个权威描绘是在聚球藻属(Synechococcus)和原绿球藻属(Prochlorococcus)这两种漂浮的海洋蓝藻中发现的⑤。它们靠光合作用获取能量,但二者都会被过程中产生的有毒副产品过氧化氢伤害。过氧化氢酶可以中和过氧化氢,但酶的生产成本很高。尽管都需要靠它生存,但只有聚球藻属带有这种酶的基因。聚球藻属清除了环境中的所有过氧化氢,而原绿球藻属则享受这种保护。
像聚球藻属这种帮助者物种(helper species)可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中的拱顶石(keystone)物种。因为它们为许多其它物种提供公共利益(common good),由此也许能避免来自依靠它们的那些物种的竞争,就像发生在珊瑚案例中的那样。原绿球藻属的成功直接依赖于相对数量更多的聚球藻属。如果它的繁殖超过它的帮助者,那么它的数量将会被增多的过氧化氢限量消除(cull)。棋盘已经改变:生存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zero-sum game)。摆脱掉过氧化氢酶的基因,给予原绿球藻属显著的能量益处。同时,就像我们看到的,放松对于一个种群的自然选择也许能使它在其他领域探索新的功能。

演化的作用:使合作成为可能的科技,加速了我们种群的进化。
长期的和谐共存也许是真正共生关系的演进前兆。数十亿年前,另一种古代蓝藻目被一种植物的祖先吞没并“驯化”。它丢掉了为独立生存所需的绝大部分基因,成为我们现在所知的绿叶体(chloroplast)。为了回报所获得的安全环境,这些绿叶体为他们的宿主进行光合作用,给养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最终覆盖了大半个地球。这种劳动分工很可能就是多细胞有机体发展的种子。在此,演化并不是一场军备竞赛,而是独立国家间的和平条约。
如果不是因为有所松懈的自然选择,你和我也许永远不曾通过演化而来。人类已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全球生态龛。在此,我们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来自自然选择的伤害:农业抵挡饥饿,药物治疗病痛,文化规范促进群体和谐。我们的演化一直深受我们选择缓冲行为(selection-buffering behaviors)的影响。例如,一些现代人特质的出现似乎与能量消耗的增加相关,可以联系到肉类进入到我们的饮食⑥。我们的祖先直立人开始比它的前辈摄入更多肉类,然而当时它的颌骨及牙齿是为咀嚼难嚼的植物演化而来,并不适应咀嚼生肉。看起来这一物种不仅使用工具狩猎,还用它们处理肉类(或许,还会用火把肉弄熟)。富含能量的肉类使得针对我们新陈代谢和消化系统的自然选择松懈了下来,我们咀嚼蔬菜的时间比从前节约了10倍,为我们的现代生理机能铺垫出一条道路。我们的牙齿、颌骨和肠道变小,使更多能量可以分配到我们不断变大的脑部,二者不可避免地延长了童年的时间,并需要更多卡路里来使其充分发展。装备着粗陋却有效的手锤,直立人扭转了它的演化命运。在人类和其他具有社交学习能力的动物中,自然选择缓冲非常有力:有适应力的习性(adaptive habits),类似抱团取暖和用工具来准备食物,可以影响整个种群,而且比基因的改变要快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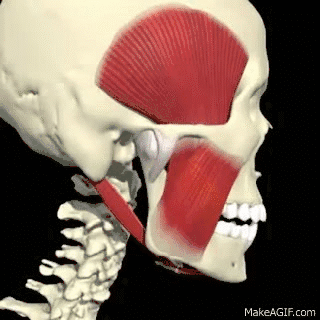
我们咀嚼蔬菜的时间比从前节约了10倍,为我们的现代生理机能铺垫出一条道路。我们的牙齿、颌骨和肠道变小,使更多能量可以分配到我们不断变大的脑部。
直到今天,我们的遗传物质持续不断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以乳糖酶基因为例,它是用来生产消化乳制品中乳糖的酶。然而它虽然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基因组中,但传统上来说,它会在婴儿期之后停掉,届时儿童就会断奶。但在相对近期的人类自然历史上,几个牧养牛的不同族群演化出了可以终其一生消化乳糖的能力,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有价值的营养形式。如今,这些群体的后代就是那些成年后也不会因为继续喝奶而生病的人。
随着人类聚集成为更大的群体,人类加速了对日益复杂的科技的探索。在高密度的聚居地,工匠和创新者专研他们的工具并交换灵感。对工具发展的选择,给我们在庞大数量中的和平共存能力施加了压力;当然,激进、不合作的个体或许早已被淘汰。时过境迁,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平和、更懂合作的物种⑦。例如,对比化石中祖先的眉毛尺寸,可以看出,我们的睾丸酮水平已经降低⑧。有些科学家认为复杂的人类文化的出现,相当于我们颇有成效地驯化了自己⑨。
经典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和“暴力即美德”可能有些过时,我想是时候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作者简介:
Kelly Clancy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此前,她曾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游历世界,并曾在土库曼斯坦服务于一个和平组织。她曾因设计无毒脑部治疗(drug-free brain therapies)获得2014年Regeneron奖的创造性创新奖项。
注释:
①http://rso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content/royopensci/3/11/160553.full.pdf
②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16-0057
③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62/n7271/full/462282a.html
④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15703/
⑤https://genomebiology.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gb-2005-6-2-r14
⑥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1/n7595/full/nature16990.html
⑦http://www.nature.com/nrg/journal/v11/n2/full/nrg2734.html
⑧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677209?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⑨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6/6208/405.full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合作联系:微信号 thegoatj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