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邰浴日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柏林封锁”与“柏林空运”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军队分别占领了德国东部和西部的领土。与此同时,各国也对德国原首都柏林的划分方案达成了协议,规定将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进行占领——柏林东部是苏占区,西部自北向南分别为法、英、美占区。虽然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ACC)在名义上享有对战后德国进行治理的权力,但是鉴于苏联与西方盟国很难在那些实质性的议题上达成协议,因此他们事实上只能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实现自身的有效统治,而其中的差别及其后续影响,也随即开始慢慢地呈现出来。
东西方两大占领势力实行统治的差别最为直观地体现在其不同的占领政策上。苏联因为在对德战争中损失惨重,因此斯大林的首要考虑就是要尽可能地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这使得苏军在德国东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将其大量工厂的先进设备拆卸下来,用船运回苏联,充当战争赔偿。根据统计,战后苏占区内总计多达30%的工业生产设施都被苏军拆除运走,此外被拆除和没收的还包括铁路铁轨以及其他一切能够作为战争赔款的财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美国政府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对于欧洲各国的吸引力,于1947年6月抛出了对愿意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支援的“欧洲复兴计划”(ERP),即所谓的“马歇尔计划”。随着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实施,西方占领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将于三天后开始在西占区德国实行币制改革,回收流通中的帝国马克,推行新德国马克,此后又于6月23日宣布将新德国马克引入柏林。此举意味着将在西占区德国重建起新一套的货币经济体系,这自然激怒了苏联占领当局,而他们手中也并不缺乏反制措施。因为柏林地处德国东北部,也就是说,它整个处于苏联占领区以内,同西方占领区并没有任何的领土接壤。西方占领国的人员和物资要想到达其在柏林的辖区,就必须得通过苏占区才行,而且苏联当局从一开始就给西方盟国规定了进入柏林的有限的航空、铁路和公路线。因此,苏联占领当局随即于6月24日宣布开始封锁柏林,切断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所有水陆交通,同时还停止了苏占区对西柏林的能源和食品供应。
苏联实行柏林封锁的目的在于迫使西方盟国知难而退,逐步撤出西柏林,进而将整个柏林拱手让给苏联。此时的西方盟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向苏联屈服,要么利用如今仅剩的“空中走廊”向西方盟国驻军以及200多万西柏林居民无限期地供应战略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最终采行了后者。
西方盟国此后立即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实施了所谓的“柏林大空运”,成功满足了西柏林的物资需求,使得柏林封锁的效果大打折扣,并最终迫使苏联占领当局于1949年5月解除了封锁。然而西方盟国的战略收获并不止于保住了其在西柏林的辖区,因为与其所提供的物资支援相伴随的,是人心的逐渐转向——其中一个最为直观的表现便是,当时参加柏林空投的西方机组人员全都赢得了西柏林人的欢呼与鲜花,不少飞行员甚至还因此成了名人。盖尔·哈尔文森中尉就是一个代表,他在空投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地面上有些小孩在望着他的飞机,一开始他只是不经意地将手绢里包着的糖果洒向那些小孩,后来便因此成了广受柏林市民欢迎的英雄。而此举带来的影响便是,自此之后西方盟国的飞行员在即将着陆的时候几乎都会向街道投撒一些糖果或巧克力。要知道仅仅在几年之前,同样是这些飞机,向柏林投送的可是致命的炸弹呀!可是现如今,它们已经被感恩的柏林市民亲切地称呼为“葡萄干轰炸机”(Rosinenbomber)。
可以说,正是经由此次的柏林封锁和柏林空运,很多西柏林人和西德人对于西方盟国的认识已然大为改观,原先的“占领者”如今在他们眼中已然转变为切实的“保护者”了。同样不出意料的是,此次事件也进一步推动了两部分德国的分裂态势——柏林市议会在此期间发生了分裂,随即于1948年9月被迫迁到了西柏林,并且于11月选举出了西柏林政府;而东柏林那边也同样建立起了自己的市政府,此外柏林市的交通系统也已经全都分了家。可以说,柏林东西部此时已然正式分裂成了拥有各自的立法体系、行政系统以及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了。而柏林又可谓是整个德国的缩影,如今建立两个德国的设想似乎已经成了某种不可避免的现实方案,不仅为两大占领势力所接受,同时也逐步为德国人自己所接受。于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RD)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分别于1949年5月23日和10月7日相继成立,其首都分别设在波恩和东柏林。
东西两个德国的正式建立,实质上意味着两种不同社会体制在东西德的确立和巩固,然而这种社会体制发展的不同走向却并非始于此时,而是从战争结束的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早在苏军刚刚占领柏林的1945年5月,原先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二号人物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就已经秘密抵达了柏林,他的任务是要赶在西方盟国进驻商定的辖区之前,配合苏联军管局(SMAD)抓紧着手重建柏林市的政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乌布利希确立了一系列用以维护共产党统治地位的政治策略——譬如所谓的“副手体制”,即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其副手必须是乌布利希的人;再比如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警察部门,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控其他的政府机构。乌布利希在此期间对其同僚讲的那句话可谓完美概括了共产党在刚被占领的柏林所实施的策略——“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

瓦尔特·乌布利希
可以说,苏联占领当局在战后初期所推行的所谓“联合政府”政策只是某种过渡而已,其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体制。果然等到了1946年4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KPD)便实施了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合并,合并后的新党改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虽然共产党主席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和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在合并大会上被共同推选为该党的主席,但是党的主导权实质上已经落到了其名义上的副手——乌布利希的手里。与此同时,苏占区德国内的其他小型政党如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及自由民主党(FDP)等也只能表示自己将接受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了。此后苏占区德国开始逐步确立起一党制体制,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与苏占区德国不同,西方占领区的德国体制却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即以英美体制为模板,经济上实行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则采行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而东西两种体制的优劣对比,也将很快得到呈现。
“6·17起义”与“用脚投票”
西德在推行了币制改革之后,实现了币值的稳定和市场的繁荣,其工业产值也得到了连年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东德的经济发展却很快显露出了某种危机,其1952年的政府预算已经出现了7亿马克的财政赤字,而它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也达到了6亿马克。更为严重的是,东德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跟1947年相比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很多企业也根本难以完成国家制定的生产目标。
东德人不仅要面对物质上的相对匮乏,同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权利保障。他们不仅无法行使西德人所普遍享有的包含选举权在内的诸多政治权利,而且也不能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和表达不满,否则就很可能会遭到来自秘密警察的一系列政治迫害。诸如农场主、商人、银行家等所谓的有产阶级,也都因为强制实施的国有化政策而成了“无产阶级”,其后他们还将面临政府出台的各项歧视性措施的种种困扰。而与他们一样承受着政治高压的,还包括知识分子、律师、以及神职人员等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社会群体。
可以说,东德的普通民众深切体会着国家体制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在其西德近邻的对比之下则显得愈发地突兀和难以忍受,社会上逐渐累积起来的不满情绪,终将借着某个由头一次性地爆发出来。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似乎就是某种征兆,仅仅几个月后,东德部长会议于5月28日作出决议,宣布要将公有制企业部门的劳动定额指标平均提高10%、但却不会相应地增加工资,以此作为向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60岁生日的献礼。该决议随即引发了建筑行业工人的罢工抗议。6月17日,东德境内更是进一步爆发了全面的罢工抗议风潮,随即又演变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街头民众的口号也从单纯提高工资福利的经济要求,扩展到了诸如释放政治犯、改变政治制度、以及实现国家统一等政治要求。与此同时,街头还出现了示威民众烧毁公共设施及攻击警察局的状况,统一社会党的旗帜以及苏联国旗都被人们扯下撕毁并付之一炬,情势正急速演变为一场对东德共产党政权颇具威胁的工人起义。此后苏联驻军立即出动坦克对示威民众进行了严酷的武力镇压,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迅速扑灭了起义的势头。以上便是东德历史上著名的“6·17起义”,它同时也是冷战时期东欧集团中第一起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事件。
为了纪念此次起义,西柏林市议会于数天后的6月22日便投票决定,将从恩斯特罗伊特广场(Ernst-Reuter Piazza)到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的夏洛腾堡宫大街(Charlottenbuger Chaussee)改名为“6月17日大街”(Strasse des 17 Juni)。此后,西德政府还于当年的8月4日将6月17日定为了国家的法定假日,其后又在1963年将这一天升格为国家记忆日。
作为柏林地标的勃兰登堡门由东西向的一条主干道贯穿而过,以该门为分界线,其东边一侧的那条林荫道便是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而西边一侧便是这条全长为4公里的“6月17日大街”了。其北边不远处便是那座有着著名玻璃圆顶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 Building),而顶端矗立着镀金胜利女神像(Goldelse)的“胜利纪念柱”则位于这条大道之上,它是为了纪念1864年普鲁士对丹麦战争的胜利而建造的。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德国土地上的第一座苏联纪念碑——苏联二战纪念碑(Soviet World War II Memorial)也同样坐落于这条大街之上。从勃兰登堡门出发,沿着这条大街往“胜利纪念柱”的方向走一小段路,右手边便是了。该纪念碑是由德国劳力在苏联红军的命令下修建的,落成于1945年11月11日。与其他纪念碑往往只是一个单体建筑不同,这是一个规模颇为宏大的纪念场所。它的入口两旁放置着两辆苏联T-34坦克以及两门加农炮,它们都曾在攻占柏林的战役中使用过。纪念碑的主体建筑是一排石柱廊,石柱上雕刻着当年在战役中牺牲的苏联士兵的名字,正中间那根最高的石柱上放置着一座苏联红军士兵的青铜雕像。在这座纪念碑的后面,还安置着将近2500座苏联士兵的墓穴。到了苏联的国家纪念日,苏联驻东德大使以及其他一些高阶苏联代表会在英国警察的保护下在此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即便在柏林墙建成后的一段时期内也依然如此,当然这是后话了。
让我们回到原先的话题,东德人在体会着自己国家的种种制度弊端的时候,当然也并非完全束手无策。除了参与危险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外,他们当时还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离开这个国家,到西德去!这其中的便利与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与其他东欧国家的人们不同,东德人穿越边境之后,其实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文化,他们不需要学习新的语言,也不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西德仍然可以生活得非常自在,不仅能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还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高的薪水。
而且当时的离开途径也可谓选择多多——他们既可以尝试直接穿越边界抵达西德,也可以保守一点先去柏林。在柏林,他们可以轻松地进入西柏林,然后再从西柏林的机场飞往西德的某个城市,这样就无需担心会被东德的边界巡逻人员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了。
形势的发展也不出人意料。根据统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民众离开前往西德定居。1950年离开的人数为19.7万人,1951年为16.5万人,1952年为18.2万人,1953年的人数更是达到了峰值,当年有将近40万人逃往西德,原因也非常明显,就是因为6月发生的工人起义及其后的武力镇压;1954年的离开人数为将近20万人,此后的3年为每年25万人左右,接下来的3年里又有将近100万人逃离。就这样,东德的人口从1945年时的1664万下降至1961年时的1314万,此间总计约有350万人逃离了东德!这些逃离的人口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也同样不容小觑,因为其中包括了熟练工人、小生意人、医生以及科学家等重要的社会群体,其所占的比例也绝不算小。现在的问题是,统一社会党的统治者们会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东德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橱窗”演变成“逃离的橱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正酝酿着一项孤注一掷的反制措施。
“玫瑰行动”
1961年8月13日凌晨1点,东德的边境警察、工人自卫队和建筑工人突然全面出动,开始实行上级布置的所谓“玫瑰行动”——他们用带刺铁丝网、坦克路障和新浇筑的水泥支架来封锁所有通往西柏林区域的街道,截至早上6点左右,东西柏林边境的临时封锁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夏季的周日,恰恰是很多柏林居民利用周末闲暇进行休假的时候,而这对于东德当局来说却无疑是个开展行动的最佳时点,这样等东德民众早上一觉醒来,就只得面对边界已然封锁的既成事实了。
在此之前,尽管东西德国已经存在了12年,柏林也存在着两个独立的政府,然而在很多方面,柏林还仍可算作是一个统一的城市。虽然市内有明确的标志显示各个占领区的边界,而且偶尔还会有检查站以及暂时或永久的边界限制,但是柏林市民还是可以在这个城市自由地通行,而且整个城市的电话线、下水道以及交通设施也还是共享的。然而在“玫瑰行动”实行之后,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此后东德居民如果要想进入西柏林,都需向当局申请特别批准才行,而且往往不会获得通过。而若是有人试图强行穿越边界进入西柏林,那么他们将面临被逮捕或是被枪杀的巨大风险。
在此还有一个花絮值得提及,就在边界封锁行动实行前不久,东德当局的最高领导人乌布利希还竟然公开提及了有关“修建围墙”的问题。1961年6月15日,《法兰克福评论报》记者安玛丽·道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向乌布利希提问:“照您看来,一个自由城市的形成就意味着要在勃兰登堡门设置国界吗?”乌布利希答道:“对于你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西德有人期望我们会动用东德的建筑工人来修建一道围墙。我并不知道我们有此类意图。我们国家的建筑工人现在正忙着修建家园,单是这些工作就已经让他们精疲力竭了。没有人打算建一道墙。”
然而问题在于,新闻发布会现场根本未有人暗示过这类企图是存在的,乌布利希如此急切地予以否认,而且内容还这么具体,只能说是恰恰表露了其心中所想罢了。的确,“玫瑰行动”中所临时设置的带刺铁丝网只是边界封锁的一期工程而已,此后它们将会被那些更为坚固的设施所取代,而这其中的主体工程便是“建一道墙”——即那道人们耳熟能详的“柏林墙”。
乌布利希当时予以坚决否认,如果计划提前泄露,肯定又将引发新一波的逃离风潮,届时封锁边界的效率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了。然而那毕竟是在公开场合发布的谎言,因此代价也一定难免。在柏林墙修建期间,西柏林这边很快便树立起了许多面向东柏林的宣传海报,那上面印着乌布利希当时答记者问的照片,以及回答的具体内容,海报上最突出显眼的内容自然是他的那句——“没有人打算建一道墙。”这些海报,配合其前方正日益树立起来的柏林墙,仿佛在宣示着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如今的东德政权,也许只能依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统治了。

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有名言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讽刺的是,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奉行共产主义理论的东德政权。具体到柏林的情境,或许可以表述为:“哪里有围墙,哪里就有逃亡。”然而在我们讲述东德普通民众的逃亡故事之前,也许首先应当提及一名围墙守卫者的逃亡故事。
1961年8月15日,东德边界部队的一名下士正站在东柏林贝瑙尔大街和卢平大街的交汇处负责守卫。这位名叫康拉德·舒曼的19岁青年几天前刚刚随部队抵达柏林,他随即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部队在柏林并不受到欢迎——不仅面临西柏林人的敌意,而且遭受东柏林人的猜疑。舒曼对此一直感到困惑不安,就连在执勤的时候也依然显得心神不宁——这名年轻的东德军士靠墙而立,肩上挂着自动步枪,他在不停地抽烟,偶尔会朝西柏林那边的抗议者们看上一眼,那些人正在对他起哄。那些西柏林人大多也十分年轻,他们似乎有点看出了舒曼脸上的疑虑和迟疑。于是其中有些人停止了对他的咒骂,转而开始鼓励他放弃。“过来!”他们对舒曼这样喊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西边的怂恿声也变得越来越大。后来有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停住,有人从里面打开后门,同样高喊着“过来!过来!”就在这时,舒曼突然扔掉了手里的香烟,奋力地跑向铁丝网。在到达边界屏障的时候,他扔掉了手里沉重的武器,一跃而跳入了西方。
当时在现场观望的人群中有一名来自汉堡的年轻摄影记者叫做彼得·雷宾,他见状迅速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记录下了这非同寻常的一刻——照片中的舒曼头戴钢盔、脚穿长筒靴,他年轻的脸庞显得全神贯注,正奋力越过那道人造的藩篱。这张照片在几个小时后就刊登在了西德《图片报》的头版,此后将迅速出现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成为了冷战时期最为经典的瞬间之一。

不管在那个时候还是在后来,舒曼都坚持表示他没打算向任何人开枪,而逃去西方,就可以使他摆脱那种道德上的困境。舒曼因此成为了东德边界警察部队中的第一个“叛逃者”——他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统计,在边界封锁的最初36小时内,就有超过9名边界守卫叛逃到了西方,他们有的是跳过铁丝网,有的是从底下钻过去,还有一个是爬过了工厂的围墙。而在边界屏障建立起来后的一个月内,总计共有68名特别警察部队成员叛逃到了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舒曼一样的单独逃亡,有24人是两两结伴逃跑的,另外还有3人和4人的结伴逃跑各一次。
逃亡悲喜剧
东德当局实行的边界封锁以及其后柏林墙的建立,可以说十分有效地阻断了东德普通民众去往西柏林和西德的通道。然而另一方面,这也让更多的东德人愈发地体悟到了自由的涵义——西柏林政府可从未禁止其公民去往东柏林!因此,即便如今边界已经封闭,即便私自跨越边界属于违法行为,东德人试图逃往西边的努力也从来不曾停歇,即便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在边界封锁的初期,首先集中上演的便是贝瑙尔大街(Bernauer Strasse)上的逃亡大戏。根据战后的边界划分,这条大街本身及其北侧的建筑属于西柏林,而其南侧的建筑则属于东柏林。这就意味着,东德人只要能通过大街南侧的这排建筑抵达贝瑙尔大街,逃亡就成功了。因此首先发生的一幕便是,原先居住在这些建筑之中的东柏林居民纷纷从自家的窗户跳到了贝瑙尔大街上。但是东德的边境警察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开始逐个进入这些建筑展开搜查,试图能够及时拦截住其中居民的逃亡行动。就这样,那些居住在较高楼层的居民们也来不及拿着行李走到下面的楼层再往街上跳了,因为警察们随时可能抵达他们的房间。此时的他们需要做出及时的抉择,这显然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与此同时,西柏林这边的贝瑙尔大街上也早已聚集起了许多围观的民众。他们在朝着那些站在窗台上正犹豫着是否要往下跳的东柏林人大喊,给他们鼓劲。西柏林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也都赶到了现场,他们迅速在建筑物楼下铺开充气垫,以防跳下来的人们摔伤。有不少住户通过这种跳窗的方式实现了逃亡,但其中也不乏惊险的案例。1961年9月24日,一位77岁高龄的老奶奶正打算从二楼窗户滑向地面,但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胳膊被房间里的东德警察给拖住了!而楼下街道上的西柏林人则在窗下死死抓住她的脚踝,拼命想把她拉下来。所幸的是,这位逃亡者及其西柏林援助者最终靠着地心引力的帮助赢得了此次拉锯。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此幸运。47岁的鲁道夫·厄尔本在从公寓楼的窗户跳到大街上的时候就受了重伤,他在西柏林的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之后,终因伤重不治而身亡。而59岁的艾达·希克曼也因为跳窗而不幸摔死。
当然这种逃亡方式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此后东德当局便将那些住在靠近西柏林边界的住户全部迁走,同时将所有临近边界建筑的门窗都用砖头给封了起来。然而即便如此,也依然有人试图从这些建筑的楼顶逃入西柏林。1961年10月4日,贝恩德·兰瑟便打算借助晾衣绳从贝瑙尔大街44号公寓楼的楼顶滑入西柏林。东德警察在获悉后便火速进入了这栋公寓,兰瑟见状只好赶紧跑向其他地方,而那些东德警察便追着他在楼顶上乱跑。兰瑟在奔跑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西柏林呼喊求救,此时西柏林的消防人员已经在大街上铺好了充气垫,数百名西柏林民众也聚在附近紧张地围观。眼见着东德警察在步步逼近,兰瑟最终只能纵身一跃,从楼顶上跳了下去。然而他却未能跳到气垫上,而是结实地摔在了地上。几分钟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当时年仅30岁。
在边界封锁的初期,东德人还可以尝试一种相对安全的逃亡方式,那便是装作滞留在东德境内的外国人,然后经由东德检查站“合法”地出境抵达西柏林。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取得相应的身份证件,而当时西柏林的一些逃亡协助组织就在致力于这项工作——其成员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国外关系借到外国或西德的护照,此外他们还能够通过外交圈以及官方人士获得一些空白护照。接着他们便会修改或是伪造出新的护照,再托人将之送到东柏林的逃亡者手中。逃亡者们在拿到这些假证件后必须熟记其上的信息以及护照持有者的生平。如果是外国护照,他们就还要学习一些该国语言的常用表达。此外,他们还需了解如何填写出境文件、以及如何应付东德边境官员的提问和刁难等事项。当一切就绪之后,他们就可以去尝试“冲关”了。该方法在最初的几个月内都非常有效,直到东德警方于1962年年初查获了一对打算逃亡的夫妻并制定出了应对方案为止。
1962年1月6日,东柏林当局宣布将针对外国人实施一项新的措施——此后所有通过边界进入东柏林的西方人都要在他们的护照中插入一个入境许可证,当他们经过检查站返回西柏林时则必须上交该证。这样,任何企图离境而护照中又没用这种许可证的人就一定是东德的逃亡者了。此举也随即宣告了护照逃亡方式的寿终正寝。
随着边界管制的日益加强,有些东德人开始尝试采用一种更为大胆、也更富戏剧性的方式来实现逃亡——即驾驶着重型机动车闯过边界!1961年9月20日,一辆卡车急速地冲过了特雷普托区和新克尔恩区之间由铁丝网和水泥柱构成的边界屏障,尽管边界警察迅速使用自动武器对其进行了射击,并致使车内一人受伤,但是该车还是成功越过边界线抵达了西柏林领土,车内有3人实现了逃亡。同一年的12月5日,27岁的火车司机哈里·迪特灵则是驾驶着一列定期的旅客列车全速冲破了阻挡在火车轨道上的边界障碍,其后又继续沿着尚存的铁轨行进了几百码的距离才停下车来,此时火车已完全处于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区域了。火车上的32名乘客中有24人对此次逃亡知情,其余8名不知情的乘客中有7人随后返回了东柏林,剩下的那名17岁的女孩当即决定留在西柏林。
除了上述逃亡方式,东德人在边界封锁初期还会尝试通过游过河流或湖泊、或是爬过下水道等方式抵达西柏林,而所有这些尝试也都面临着被东德边境警察抓获逮捕并判处长期监禁的风险。根据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统计数据,1961年8月13日至12月31日期间,因为试图逃跑而被逮捕的人数总计为3041人,其中试图徒步逃离的人数占比为73%,试图通过驾乘火车、汽车、及海运轮船逃离的人数占比分别为11%、8%和4%,此外试图通过游泳和爬过下水道逃离的人数占比分别为3%和1%。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在边界封锁实行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东德边界警察开枪射杀逃亡者致死的事件。1961年8月24日,当24岁的冈特尔·利特芬(Günter Litfin)试图游过洪堡港(Humboldt Harbor)逃往西柏林的时候,就不幸被边境警察的子弹击中身亡,由此成为了柏林墙历史上第一个被射杀身亡的逃亡者。几天后的8月29日,又一名年轻的东德人、27岁的罗兰·霍夫在试图通过泰尔拖运河游往美国占领区的途中也被射杀了。这类射杀行为非常直观地向外界表明了东德当局最新的“边界政策”,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此后当掌控着边界武装力量的国防部长于10月6日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为达目的可使用武力”之后,东德武装部队成员随意使用武力进行杀戮的行为就变得更加司空见惯了。
1962年8月17日,发生了柏林墙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起射杀事件。当天下午,18岁的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和他的一个朋友伺机跑向边界障碍试图实现逃亡。此举也随即引发了边界警察的开枪吓阻。他的朋友率先抵达了最后一道围墙并成功翻了过去,可是当费查跟着爬上去的时候,却被子弹击中滑了下来。费查躺在那里大声地呻吟呼救,然而却未能等来东西柏林的救援人员——东柏林警察也许是在等待上级的指示,也许干脆是希望以此来惩罚一下逃亡者,总之是拖延着迟迟不肯出动;而西柏林警察则根本无权进入东柏林领土,所以至多只能将急救包扔过围墙而已。可是费查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子弹打断了他的一条动脉,鲜血正汩汩流出,很快他也将失去呼救的力气。40多分钟之后,费查才被姗姗来迟的东德边境警察抬走,但在抵达医院时他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了生命。而费查躺在柏林墙下等死的照片,则将东德政权永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这位年轻人身穿紧身牛仔裤、留着时尚发型,绝望地蜷缩着躺在那里,从伤口流出的鲜血已然渗入了大地……

当时有许多西柏林人都当场目睹了整个过程。他们当天便在柏林墙的西边一侧献上了鲜花与花圈,这里从此也成为了一个简易的纪念地。到了1999年,在离查理检查站不远处的齐默尔大街(Zimmer Strasse)上,还树立起了一座纪念费查的青铜纪念碑。当然,这已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事了。
虽然东德当局努力阻止了多起逃亡行动,但那些偶获成功的逃亡案例依然会使东德的统治者们感到惶恐不安。因为它们证明了柏林墙并非无法逾越,为上千万身陷囹圄的东德人民带来了希望,同时也激励着世界各地同情他们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东德当局才不仅要推行最为严厉的边界政策,同时还将致力于把那些边界屏障建设得滴水不漏。
如今位于贝瑙尔大街的柏林墙纪念地(Berlin Wall Memorial Site),可谓是柏林分裂的主要纪念场所之一。这里不仅完整保留了一段当年的边界设施遗址,同时还囊括了诸如照片展示、雕塑陈列、受难者纪念墙、教堂、以及墓园等一系列纪念设施,从而尽可能完整地向人们呈现着那段历史。人们还可以登上位于阿克大街(Acker Strasse)的纪念地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的塔楼,从上面俯瞰全长一公里左右的纪念地全貌,而这时呈现在人们视线正前方的,便是位于塔楼街对面的那段边界设施遗址了。
这时你会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其实绝非是一个“墙”字就能完全形容得了的——它实际上包含了一整套的边境安全系统!
假设一个东德人想要越过边界逃亡,那么他首先要翻过的是一道由水泥板做成的腹地墙,这道墙上贴着措辞严厉的警示牌,提醒攀爬围墙将会违反法律,且可能遭受枪击;这道墙之后是一道由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柱制成的电子警报栅栏,其顶部的铁丝网是倾斜的,以防止人们攀爬,其下半部分也被加固,以防有人从缝隙中钻过,栅栏上还通了电,一旦触碰,便会引发警报,从而招致边界警察的追捕和射击;在这道栅栏后面,建造了警戒塔、探照灯以及警犬桩等设施,而且多数地段还设置了两排钢制的反机动车冲击路障,这样就不仅能阻止驾车闯关者的逃亡尝试,同时还能对徒步逃亡者造成新的阻碍;探照灯之下,是仅供边界警察部队使用的巡逻道路,再往外则是数米宽的经过了精心耙梳的沙区,这样任何经过这个沙区的人都会留下清晰的脚印或者其他痕迹;整个设施的最外头,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道顶端装有防攀爬圆管的柏林墙,这道墙的外边就是西柏林了。从巡逻道路到柏林墙的这段沙区,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死亡地带”——任何人胆敢踏足这一区域,都将立即成为边境警察的射击目标。
以上所有这些设施,在东德当局的嘴里竟都成了“防御”措施,而柏林墙的官方称谓居然也是叫做“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与此同时,东德当局还总是将那些试图逃亡的人——无论他们成功与否,统统都宣称为“特工”或者“罪犯”,以此来表明他们的罪不容赦。东德的宣传部门甚至还会处心积虑地编造出各种扭曲事实的报道,来对那些逃亡者予以污蔑和攻击。
然而问题的核心却是,遍观人类历史,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边界防卫系统都只是用来防止外国人进入的,而绝非是将自己的国民拘押于内。可是柏林墙所防范的却恰恰是自己的公民。
倒塌
事实上,东德人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逃亡尝试,又何尝不是在对柏林墙施加政治影响呢?到了1980年代末期,此类逃亡风潮更是由于受到其他社会主义邻国改革局势的影响而呈现出了愈演愈烈之势。
1989年5月,匈牙利共产党当局开始着手拆除奥匈边境的电子警戒系统及带刺的铁丝网,此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东德民众抱着有可能穿越奥匈边界进入奥地利、继而再进入西德的愿望陆续进入了匈牙利。截至9月初,为此滞留在匈牙利境内的东德公民已达到了6万人之多。到了匈牙利当局正式宣布开放奥匈边界的9月11日,一天之内就有6500名东德公民启程进入了奥地利境内,更多的人也已整装待发,这使得那道由各国共产党当局共同建立起来的有形“铁幕”突然之间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缺口还不只这一个,与此同时另一些东德公民开始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馆作为自己的避难地。他们向西德当局申请政治避难,在获准之前就一直呆在大使馆之内拒不外出。1989年9月30日,东德当局表示允许这些难民前往西德,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乘坐在密封的车厢内穿过自己的家园,而且途中他们国籍将被撤销,身份证也将被没收。东德当局希望以此来羞辱他们,并且表明他们是国家的叛徒。10月2日,共计1.2万名东德难民挤在8节火车车厢内离开了布拉格。可是出乎东德当局意料的是,当列车路过东德各个城镇的时候,难民们非但没有遭遇人们的回避和羞辱,反而还得到了成千上万普通东德民众的夹道欢迎和欢送!当列车开到东德第三大城市德累斯顿(Dresden)的时候,难民们也开始有所反弹。一如当局所料,他们拒绝交出自己的身份证。可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却并非出于留念,而是出于厌恶——他们干脆把证件撕碎,和随身携带的东德马克一起,从火车车窗扔了出去!因为那些东德马克在进入西德之后也便没了用处。这辆列车最终抵达了巴伐利亚州北部的霍夫,这里属于西德,难民们再次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欢迎和庆祝。可以想见的是,以上只是故事循环的开始,因为不久之后,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馆又将再次聚集起新一批的东德难民……
随着政治局势的演进,东德国内的反对派组织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而与此相伴的则是范围越来越广泛、声势越来越浩大、频率也越来越密集的集会示威抗议。以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Leipzig)为例,其民众每逢周一都会例行发起一次抗议政府的游行示威,参与人数从10月2日的1万5千人,逐级增加至9日的8万人、16日的15万人和23日的20万人,到了11月6日则是达到了惊人的50万人!
来自国内外要求实行改革的压力最终促发了东德保守派领导人昂纳克的下台、以及东德当局在公民自由流动这一议题上的实质性退让。1989年11月9日,在东柏林莫尔大街的东德内政部大楼内,一个由4名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正在根据政治局的指示抓紧起草着一份法律草案。该草案最后规定,只要东德公民持有护照和签证,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实行私人访问或永久移民。当天晚上,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来到莫兰大街的国际新闻中心,对着媒体宣布了东德当局的这一最新决定,即将来“东德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东德的过境点离开东德”。
此消息一出,东柏林的人们便开始涌向各个边境检查站尝试过境。在伯恩霍莫夫大街检查站(Bornholmer Strasse Checkpoint),已有大批人群聚集在网格围栏的后面。他们开始缓缓向前推进,威胁着试图维持秩序的少数边防警察。晚上11点30分左右,有一批东柏林人推开了边界过境点的网格围栏,致使人群大量涌入了检查站区。此时的检查站指挥官哈拉德·加各中校也不打算冒险搭上自己和士兵们的性命,于是他命令部下停止护照检查,全面开放边境,让人们过去。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抵达了西柏林。当他们畅通无阻地跑过桥或者越过边界的时候,或许不曾想过,这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之前都还是必死无疑的行为。到了午夜时分,所有的边界检查站都已被迫开放,而柏林墙也随即遭到了街头民众的自发拆毁。说来确实有些奇怪,正如它的建造一样,柏林墙的倒塌居然也是在一夜之间便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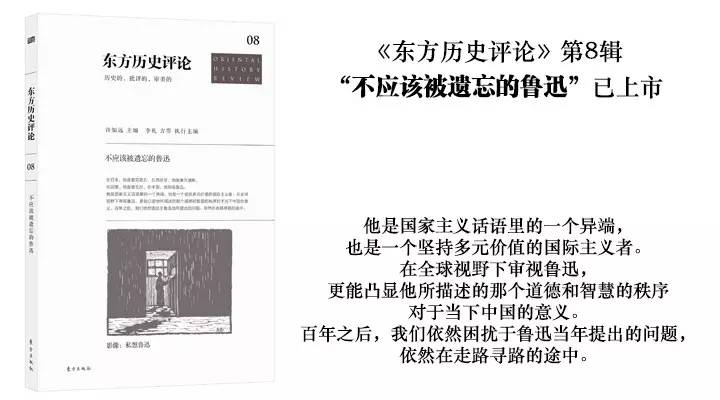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
|
李鸿章
|
鲁迅
|
聂绀弩
|
俾斯麦
|
列宁
|
胡志明
|
昂山素季
|
裕仁天皇
|
维特根斯坦
|
希拉里
|
特朗普
|
性学大师
|
时间
|
1215
|
18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