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522个故事

矿区回忆
——逝去青春期和荷尔蒙
by 张樯
遭遇“黄书”
去年在香港旺角的一家楼上书店,竟意外发现了《少女之心》。我不敢相信,当年这本竞相传阅令人心惊肉跳的手抄本,居然堂而皇之地印刷出版了。我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下。
回到家中,摩挲着这本封面设计得颇为羞答答的书,我并未急忙打开,而是回忆起了与这本书相关的种种往事。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刚刚上了高中不久,与一个叫陈卫星的家伙有关。陈卫星当时可说是个知名人物,不但在整个矿区无人不晓,就是矿区以外也是大名远扬。原因倒不是他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他的奇装异服和他屡屡出位的行为。他是作为正式工特招到煤矿的,一到煤矿,他就因一身全套的海魂衫衫引起了轰动。想想看,大冬天的,别人都是棉衣棉裤,他也不是什么海军,不知在哪弄了一套海魂衫竟不畏严寒地穿在身上招摇过市,雪白的衣服,加上水兵帽的飘带在风中不停地飞舞,让他在着装非黑即蓝的人群里异常扎眼。我跟着他走出矿区,上街道,山沟里的人没见过世面,干冷、灰扑扑的公路上,他就像接受行人的检阅似的,走到哪里,行人的目光就跟到哪里。
我还在上学,照理跟他走不到一起。他衣装出位也就罢了,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使奸耍滑,我的妈妈是矿医务室的医生,掌握着为全矿职工开病假条的大权,陈卫星三天两头就跑到矿区医务室软磨硬泡。之前陈卫星谎称胃痛,紧皱了眉头,妈妈给他开了好几次假条,但他贪心不足,时不时来要休病假,妈妈不理他,他就直接上门来泡。寒假里我正好在家,他就“曲线救国”,向我套近乎,还不时小恩小惠一番,幼稚的我,哪能识破他的花招。看他来自城里,见多识广,又好玩,我就跟他在一起玩了。靠了我,他还真在妈妈那里多泡到了几张病假条。
我就是在认识他不久后看到那本手抄书的,一天我跟着穿着海魂衫的他,从街道回来的路上,途经水泥厂,他要我陪他去找一个人。
到了水泥厂,敲开了职工宿舍的一扇门,才知道他要找的是个女工。那女工很年轻,尚算俊俏,却带着几分冷漠,她独自一人住在这间单身宿舍里,看来尚未婚嫁。刚刚坐下,陈卫星就像对接头暗号一样,忽然问:“看完了吗?”那女工也不言语,沉下脸,起身走到床前,拉开床垫,从底下抽出一个本子,递给陈卫星。陈卫星接过来,赶紧揣到怀里,我们便马上告别了那位女工。
回煤矿的路上,陈卫星突然神秘地将这本皱巴巴的手抄本交给我,并叮嘱:“借你看吧,这是《少女之心》,手抄本,千万不能借给别人,更不能让你爸爸妈妈看见。”
揣着这本沉甸甸的书,顾不上多想,回到家后,趁爸爸妈妈还在上班,我开始偷偷翻开这本火烫的书。这本书抄在笔记本里足足有几十页,我不可能一下读完。不过,我一打开,就吓了一大跳。这本书讲一个叫曼娜的女大学生暑期回家,邂逅表哥少华后,在引诱下失身的经过;后来回到体育学院又与体同学林涛谈情说爱……书里充斥着赤裸裸极为露骨的性描写。
天呐,我一个中学生,跟女生多说几句话都会害羞脸红,哪见过这阵势!我承认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内心起了化学反应,也许应该讲是中毒了吧。那段日子,我沉溺于书中劲爆的描写里,无心功课,也无心读闲书,做任何事都无精打采,我甚至想象着能遇到一个像书中的那个女大学生就好了……我的爸爸妈妈当然不知道这个秘密,我表面仍旧若无其事,不过一有机会,我就会从床底下翻出这本藏起来的禁书,偷偷读上一段。
我现在想,当初这本书一定是在那个禁锢的年代一个备受性压抑和煎熬的家伙写出来的,然后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又经过了无数人添油加醋的再加工再创作。虽然“读书无禁区”,可我真是不该在懵懂无知的年龄里早早接触。好久我都没从这本手抄本里挣脱出来。“近墨者黑”大家说的没错,陈卫星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我突然想到,陈卫星当初将这样一本书借给那位女工,分明就是在引诱人家。
这本烫手的书没在我的手中保留多久,就被陈卫星要走了。因为妈妈不再给他开病假,终于惹恼了他•,便索性与我翻脸了。后来他经常性地无故旷工,矿上就将他开除了。某年我从学校回家后,听说他又因调戏猥亵妇女,被抓起来判了几年刑。
我第二次看到这册手抄本已临近高中毕业了。彼时我已转到县一中,却不幸因为严重偏科,数理化分数过低,被理科尖子一班刷了下来,“下发”到了文科二班。这个二班虽谓文科班,却是一个集合了各种“差生”的大杂烩班级,眼看面临高考,教室里却整天人来人往,乱哄哄一团糟,谁也无心坐下用功,都想尽快拿到一纸毕业证,好早早走出校园端上一个饭碗。
就在这群同学中,我认识了谢玉窑。谢同学五大三粗,极其憨厚,红红的大脸盘上经常挂着腼腆的笑。他是来自距县城几十里路乡村的农家子弟,得知我来自矿区,父亲还是什么矿长,就极力讨好我,想到煤矿当一名工人,借机会能跳出农门。谢同学不怎么爱学习,我也一样,知道自己高考无望,索性“破罐破摔”,三天两头无故旷课,不是往家里跑,就是在小城的街道里转悠。那几天回到教室,却发现邻座的谢玉窑突然变得用功起来,整个人趴在课桌上,一直在抄抄写写,即使教室里吵翻天,他也不为所动。在好奇心驱使下,我走了过去,发现了他左边一只手捂住,正在一个本子上异常认真地誊写着什么。见我站在身边,他赶忙起身,涨红了脸,送上腼腆的笑,嗫嗫嚅嚅道:“还没抄完。”
“这么用功,抄什么呀?”
他显然对我并不设防,马上从实招来:“黄书!”
我接过来一看,名字是《曼娜回忆录》,翻开本子里却出现了少华林涛等名字,正是多年前陈卫星曾偷偷借给我的那册手抄本。本子上的字迹,就像谢同学本人一样“五大三粗”,但显然他的这本要比当年的那本清晰多了,他几乎是一笔一划,异常卖力地在抄写着。
那些日子,谢同学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趴在课桌上进行着这项浩大的工程。然后到了放学时间,就装进那只业已发黄的军挎包里,估计回去以后还要接着埋头苦干。一天终于大功告成,他居然第一次就借给了我。
因为早已从陈卫星那里经过“启蒙”,神秘感尽失,也没这么认真研读,只大致翻翻,也不知随手扔到了哪里,没及时还给谢玉窑,后来竟不知所终。
谢同学毕业后,到底如愿以偿,进煤矿当了一名工人,不过非我的功劳,而是煤矿原本就有不少他的亲戚,大力推荐他进了矿区。后来,我在矿区也经常看到谢同学,我们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谊,但他从未向我讨要过那本被我丢失的他异常卖力才抄写完成的手抄本。
现在回到手头这本新买的港版《少女之心》。翻看着,忽然廓清了我长久以来存在心中的一个谜团,当年这部在地下传播四方的黄书,原来由两部书构成:《少女之心》和《曼娜回忆录》。前者叙述的是以杨永红为主角的三角恋及性经历自白,其咸湿成分明显不及后者,而我们当年传阅的那本恰恰是内容更为刺激和火爆的《曼娜回忆录》。
美女王君秀
一直想说一说王君秀。这不仅因为她在那个年代是个美女,还因为她或者说围绕她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
那时候,坐落在山沟里的矿区,本来女人就极其稀少,更别说是富有姿色的女人了。王君秀的到来,无疑改变了这一现状,也从此紧紧抓牢了矿工们的目光。与此同时,矿工们平时的闲聊中也多了话题,多了内容。
乍看王君秀的容貌算不上惊艳,她的眼珠有些发黄,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平素也是一副慵懒、漫不经心的神情,可也许正是她的这些特点,使她与山里来的女人们区别开来,有了独特的风韵。其实她原本就不是当地人,她的家远在省城兰州,只是因为出身原因,随父母才被下放到了邻近的乡村。
漂亮的女人总是机会多,在哪个时代哪个偏僻的角落都如此,对于王君秀也不例外。在乡村做了知青几年后,她先是被抽调到公社的宣传队,然后遇到招工,她抓住机会,又进了矿区。
煤矿本来属于男性王国,虽然深入百米的井下挖煤这些高强度的工作,唯男性专属,不过,适合女性的工种也有不少,比如绞车司机、充电房、话务员等等。
王君秀最初分配在充电房上班,这是个不算辛苦的岗位,每天上班就是通过小小的窗口把充好电的矿灯交给将要下井的工人,然后收回从井下上来的工人交来的矿灯。她穿上了煤矿统一发放的蓝色工作服,头发高高盘起,可这遮掩不住她的妩媚。工人们被她吸引着,总爱往她这里跑。那时候即使一个极为普通的女工身后也跟着一长串追求者,王君秀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工人们很快发现,王君秀与他们有着不小的距离,他们高攀不起。
其实,与那些喜欢与矿工们嘻嘻哈哈打成一片的女工不同,王君秀文静,不怎么爱说话,即使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语,不怎么喜形于色,看不出情绪的变化和起伏,可以说她的性格颇为内向,甚至有些冷漠和高傲。可是她来了不久,矿区却渐渐风传起了她的绯闻和闲话。
有人说他和某个司机好上了。那个司机是县运输队的司机,平时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在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汽车是稀罕物,司机也无形中成了一门吃香的职业,虽然开着的是一辆解放车,可有很多人求着他。除了领导,平时矿工们要搭车回家捎东西,都要央求司机。一天下午放学路上,我还真看到王君秀和那个司机在一起了。也许王君秀刚刚搭那个司机的车回了趟家,正从驾驶室里下来,他们开始告别,那个司机穿着当时流行的的确良军装,极其殷勤地帮她提东西。
很快矿区又传起了他和县城某个头头的公子交往了。但这些传闻就和她与那个司机的一样都停留在捕风捉影的层面,也许当时有人看到了她和某个男人正好走在一起,然后再经过一番想象和虚构,其真伪始终无法证实。
不过,他和邓书记的绯闻却坐实了。
说来话长,这个邓书记虽然能力强水平高,却英雄难过美人关,屡屡在作风问题上栽跟头,走到哪里,绯闻都与他如影相随。他从县法院院长的位置调到煤矿担任书记,就带有被贬的性质。他到了煤矿也是故态复萌,已经屡屡传出了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闲话,那么他与王君秀又是怎么得到证实的?因为王君秀——怀孕了。而我们家最先获悉了这一消息。照例邓书记贵为一把手,致使王君秀怀孕这么私密敏感的事情是不可能公开的,更不可能让我们家知晓。但那天我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要送王君秀到距煤矿四五十公里远的土谷堆军区医院做手术。
我的妈妈是煤矿唯一的医生,她以前曾在土谷堆一带做过医生,在那里有不少同事,那时做人流手术绝非小事,没有关系根本做不了,他们让妈妈送王君秀去也是想走走后门,并将事态的影响限制到最低。当时因为我年纪尚小,这一切当然都蒙在鼓里,我是过了很多年才揭开了秘辛。我只记得那个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正吃着饭,就被他们叫走了,她转身向爸爸交待了几句,就脸色凝重地坐上煤矿的汽车,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里。
几天后,妈妈回来了,随她一起回来还有王君秀,只见她脸色煞白,仿佛大病初愈。也从那天起,王君秀就成为我家的客人,住在了我家。因为她的父母不在身边,她孤身一人需要静养,无人照顾,住在我家接受我妈妈的照料,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不知道这是邓书记的刻意安排,还是妈妈自告奋勇的结果。但看到王君秀落得如此境遇,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的父母本是善良之人,这时候自然是愿意向她伸出援手的。
于是一段时间,王君秀俨然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每天与我们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我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更要命的是她还与我同居一室。我们家当时有两间房子,爸爸妈妈住一间,我和姐姐住一间,各有一张小床,姐姐那时因为到外地求学,不常回来,这样王君秀就睡在了姐姐的床上。
每当夜深,爸爸妈妈在隔壁房入睡了,这边寂静的房屋里就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也许因为我还是个孩子,不谙世事,那时候的她比白日里似乎显得更加安静和冷漠,往往和我说不了几句话就沉默了,脸上极其沉静,猜不透她究竟在想什么。
她慢悠悠地将烧热的水倒在脚盆里,就开始洗脚了,当看见她雪白的双脚泡在水里,来回搅动着,当时我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也不觉怦然心动。洗完脚,她就穿着睡衣睡裤躺在了姐姐的那张小床上,盖好被子,就不再说话。半夜里,我曾偷偷地打量过她,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可以看见熟睡的她就像她平日里一样平和,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哪怕一个翻身的动作也没有,也不曾发出一丝声音,像完全熟睡了。有时候因为上了夜班,隔日一早她还会回来补觉,那日如果恰逢我没有上学在家,为不打扰她,妈妈就会叫我不要再进那间屋里,于是那间房就会拉上窗帘,关门闭户大半天,我就在门前温习功课,或到外面玩。
不久一个叫石宗琪的天津人将他妖里妖气的老婆李玲从外地调回矿上,接着还有一个颇有姿色的女知识青年牛海琴也被招来了,善于拉关系的她们很快抱成一团,与生性风流的邓书记打得火热。因为有了新的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见邓书记再来骚扰王君秀了,
王君秀也依旧在我家吃住。看着她每天三班倒很是辛苦,正好医务室就妈妈一人,忙不过来,爸爸妈妈就要求将王君秀调到医务室,也许是为了补偿,书记大人恩准了。从此以后王君秀就与妈妈形影不离了,上班跟着妈妈,下班也跟着妈妈。王君秀虽然没学过医,上了班穿起白大褂,跟着妈妈很快就掌握了打针和简单的护理;回到家里,她俨然就是我们家中一份子,帮着妈妈收拾房间、做饭,她还会擀面条。这时候我想妈妈一定将她视作了她的一个女儿。
李玲她们的到来,很快将煤矿搅得乌烟瘴气,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仗着他们一家与邓书记非同寻常的关系,她开始觊觎医务室的岗位,妄图将做了多年医务工作的妈妈取而代之,背着爸爸妈妈逼迫邓书记偷偷下了一纸调令,决定将妈妈调离医务室。但在爸爸的据理力争下,加上李玲又不懂医术,邓书记也不想做得太过分,只好收回成命。看到无计可施,恼羞成怒之下,李玲有一天午后居然提着一把菜刀找上门来。叫不开我们家的门,就在房门上砍了几刀。为了息事宁人,爸爸妈妈没有报案,但无论如何李玲一家已经成了我家的仇人。
一段时间里,他们挑唆矿区的的女人们,甚至一度还想将王君秀也拉拢过去,以便彻底孤立妈妈。王君秀却不为所动,平时也不怎么搭理那一伙人,依旧与妈妈在一起上班,依旧住在我家。因为总受李玲一伙的滋扰,妈妈心情烦闷。那时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对煤矿发生的一切懵懵懂懂,自然无法开导妈妈。但因为有王君秀陪在身边,妈妈也算得到了一些安慰。但王君秀因此也惹恼了李玲一伙,他们制造了不少王君秀的谣言。不用说,这些谣言都是不堪入耳的。
一晃几年过去,我因为到外地求学,很少回家了。难得遇到节假日回家,得知煤矿已发生不少变化,邓书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了县法院,也算是归队了。因为失去了依傍,李玲一家消停了不少,矿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以后不久,改革开放了,一时之间知识青年开始纷纷返城,此风很快也刮到了煤矿,因为符合条件,牛海琴等人便着手准备调回省城了。突然间煤矿中有此背景的青年走了不少,唯独剩下了王君秀。
她的情况似乎有些特殊,因她属于随全家从省城迁往农村的,只能算是回乡青年,不在落实政策之列。那段日子,我也看见了王君秀,还是漫不经心的神情,外界的变化对她似乎没有多少冲击和影响,她依旧在医务室上班,不过,早已搬出我家,到集体宿舍去住了。
我在做着高考最后的冲刺,一次偶尔回家却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王君秀走了,嫁给了地区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儿子,直接调到了地区。她走得如此突然,似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像一部电影里的末尾,急转而下的结局,让你为之吃惊和突兀。听说专员儿子来到煤矿,一眼就看中了王君秀,马上提出嫁给他,她当即就同意了。虽然这个副专员的儿子是个跛子,但因为他有显赫的家庭和出身,这个缺陷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王君秀嫁给他,不言而喻意味从此将嫁入豪门,栖上高枝,成为许多人羡慕的阔太。事实上,没多久,王君秀就调到地区,到一家银行上班了。无论如何,这个选择,对于王君秀都是最好的归宿。
也是凑巧,没过两年,我们全家也随父亲的工作变动迁往地区。某年上了大学的我从外地回来,听说王君秀也曾来过家中。提及他的丈夫,那个专员的儿子,她只淡淡说了一句:连畜生都不如。她的语气平静,仿佛在说着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她没有透露更多的情况,我的父母也不便打问,心却悬了起来。
不知道她究竟过着怎么的生活,以后她和我父母的来往也渐渐稀少了,她依旧在那家银行上班,偶尔会在上班的路上与她相遇。在父母的印象里,岁月似乎没有改变她的容貌,她常常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映衬得她的脸色越发苍白。即使见了面,也绝口不提当年的事,只略略寒暄几句,就匆匆道别。我常年在外,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可以想象,在小城那条每天必经的上班路上,她慢悠悠地走着,许多年就走过去了。她的神情依旧漫不经心,好似昨天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午夜捉奸
当年批判林彪的一大罪状是他吹嘘自己是一个天才,脑瓜非但灵,而且是特别灵,是爹妈赋予的。我的印象中,那时在煤矿,有个叫关林的人也堪与林彪一比,他自信心爆棚,牛气冲天,夸耀起自己来没有界限,而且他最为骄傲的也是他的脑瓜,夸了自己不算,还忘不了要夸夸自己的宝贝儿子如何聪明,或者夸了儿子,总不忘捎带也夸夸自己。
实际上这个关林也的确有些值得炫耀和吹嘘的资本。他来自县城,读过书,有文化,脑子活,见识广,写得一手好字,加上身材高大,篮球打得漂亮,还吹拉弹唱无一不通,这使他在矿区那些大部分来自于乡村的“大老粗”中似乎算得上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也许正是他所具备的这些长处,他被矿部安排当上了工会干事。这虽不是个什么大官,却也算得上轻松风光的岗位,无非管管职工的吃喝玩乐,诸如放放电影,组织打一两场篮球赛,借借图书之类。
煤矿当时的工作,被工人们笼统地称之为“井上“和”井下“两种。所谓“井下”指的是下井挖煤,穿上工作服头顶矿灯,在漆黑深邃的巷道里作业,不但异常艰辛,而且极端危险;而“井上”指的则是在办公室里的工作,每天无非看看报纸、开开会之类,免去了下井之累,既体面又轻松。而关林的工作相信在井上的诸多岗位中都是叫人眼红的,不但好玩,还常常在人前出尽风头,而且一次井下都无需去——须知即使煤领导也少不了要时不时下井去检查工作的。
那时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极为单调,没有电视和其他娱乐节目,多半职工家又在乡村,与家属分居两地,八小时之外无处可去,于是关林那间小小的办公兼卧室的房间便挤满了人,成为矿区的一个中心,有的来打探今晚有无电影要放,或者来看看试片先睹为快;有的来借乒乓球或羽毛球拍子;有的来借书……
而关林似乎是看人下菜,如果不是煤矿的头头脑脑,或者与他沾亲带故的同乡,他一般都没有什么好脸色,有时遇见那些无所事事纯粹来串门的,他还对人家不客气地下逐客令。关林的办公室就在我家平坡下的一棵苹果树旁,有事没事我也去凑热闹,最吸引我的是他房间里的那个小小的书柜,里面装满了书,但关林看我是个孩子,根本没将我放在眼里,一次我发现书柜里上了几本新书,其中一本《电影歌曲选》叫我心醉神迷,就忍不住想拿出来翻阅,根本不敢奢望能借出来。但书柜却上了锁,我近乎是用乞求的口吻让他拿出来,他却死活都不答应,敷衍我等书等编号后再说。
也许因为手中拥有的“实权”助长了他,关林变得更牛了,平素也总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久而久之有几句话便成了他的口头禅:“还真没什么是我学不会的”“我的脑瓜就比就是别人好”诸如之类。他还逢人夸奖他的儿子惠义如何聪明:全部课文都能背下来,数学题一看就会。听到这些话,叫我这数学低能儿恨不得脚下有个地缝马上钻下去。那时候还没有基因一说,否则他肯定会说他聪明的儿子是植根了他的高智商基因。
他还不止一次向人炫耀他对女人们的吸引力,有多少女人曾向他投怀送抱。因为他早已成家,而且还有那个聪明的儿子,对于他的这些话,就像他无数次说过的那些话一样,大家相信都不过是他习惯性的“吹牛”而已。
一天煤矿机电队长高珍良来我家,我听见他对我爸爸说:“这个关林可真把牛皮都能吹破!看着吧,他迟早会出事的!。”
一语成谶,他果真出事了,但谁也没料想,他居然载在了桃色事件上。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矿区放映朝鲜反特电影《原形毕露》。通常矿区放电影是件大事,一有电影要放,消息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早早传遍了小小的山沟,前来观看的不限于本矿职工,还会将周围厂矿企业和乡村的人们一股脑吸引过来,更何况那晚放的还是朝鲜反特片。晚上等我从学校上完晚自习回来,发现家门前偌大的矿区大院早已是人山人海。好在因为近水楼台,妈妈早已搬了家中的靠背椅,占据了中心位置,只待我进去就坐了。
晚上电影场中最出风头的自然是关林,一卷拷贝放完,换片时银幕黑了,放映机前的灯一亮,这时大家都会将目光齐刷刷投去,关林遂成为全场的焦点。这时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女人高高的个子,似乎模样还过得去,好像是她的助手一般,在帮他递拷贝。大家都不认识那个女人,她当然不会是本矿的。但那女人前一阵子我似乎在关林的办公室见过一眼,混杂在一群人当中,他那里经常人来人往,因此当时我也没多加注意。
电影很精彩,人们第一次在银幕上见识了狡猾的女特务马桃花居然可以通过整容,假扮“好人”,来欺骗善良的人们,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机智勇敢的侦查员马国哲最终揭开了她美丽的画皮,从而让“美女蛇“原形毕露。
电影散场了,人们沉浸在惊心动魄的剧情里,走在回家的路上,也仍在议论回味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银幕下,关林和那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却上演了另一部“原形毕露”。
电影散场后,三三两两的矿工帮助关林收起挂在矿区大院的银幕,并将电影器材搬回去。在这些忙碌的人群中,还有那个高个女人。问题就出在这里,等到忙完了,人们马上都散了,那个女人却钻进关林那间狭小的屋子,再也没有出来。
也许他们过于张扬了,也许他们早就被哪个细心的矿工盯上了,一发现有了“情况”,便马上报告给了矿部,于是在政工科王干事的带领下,几位干部迅速出动,在下半夜将关林和那个高个女人双双“擒获”。
尽管当时矿工之间常常免不了开开带荤的笑话,看到某个矿工的媳妇来了,也会瞎起哄一番,但是,一个有妇之夫与一个陌生女人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几乎是公开留宿,乱搞男女关系,却是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底线,也触碰了那根阶级斗争的神经。
据说在现场关林是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由于天晚,那个女人回不去了,便留下来跟他学习放电影。哪为什么要关着灯?因为在王干事他们前来捉拿他俩时,敲了半天门,房间里的灯才亮的。关林解释,因为学累了他们才一起躺下了。
据关林交代,那个高个女人来自邻近的石沟煤矿,不知她后来去了哪里,自从那晚以后似乎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不过,关林却难逃一劫,不几天,煤矿就召开了他个人的批判大会,他在会上要面对几百号职工公开做检查。我自然没资格参加大会。
会后听大人们透露,关林的检查一点也不深刻,虽然承认自己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在检查中却时时流露出炫耀的口气,似乎是因为个人的魅力太大,那个女人缠着他,他实在没有办法脱身才与她发生了关系。我想这倒符合关林一贯的脾性,无论什么他都能扯到他的“本事”和“魅力”上。
后来,矿部做了处理,关林被打回原形,调离工会干事的岗位,回机电队做电工,也即从“井上”调到了“井下”。
平素我在矿区常常还能见到关林,那多半是他刚从井下上来的时候,蹬脚黑色大雨鞋,着一身褪色的工作服,肩上挎着沉重的工具箱,脸上还沾着未及清洗的煤灰。一旦站下,与他聊上几句,他又会不忘告诉别人他的儿子最近又考了100分,脑瓜如何聪明,继承了他这个做爸爸的遗传等话题。但感觉他的气势已不如从前,那多半是因为听众已借故离开了。
但关林仍旧是关林,也许是为了发泄对他处理的不满,一旦牛脾气上来,他会怒气冲冲地闯到领导家中,大闹一场,领导虽然头痛不已,也拿他没办法。
关林自然是再也无法从井下调到井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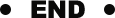
作者: 张樯,资深媒体人,发表作品近百万字,现供职深圳特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