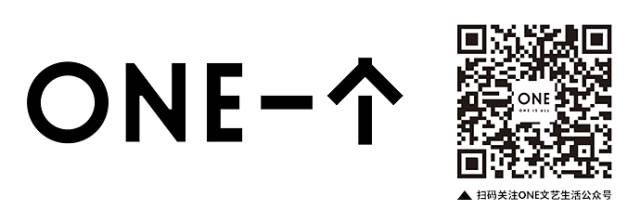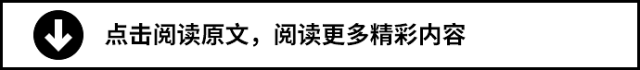两手空空。我们就这样迎向了未来。


李菁的故事从80年代开始。
关于自己跟世界的联系,李菁最早知道的是:自己出生的那一天,马丁·路德·金在一个旅馆的阳台上被射杀。
这是父亲告诉她的。从北京被下放到河北某县城的终日郁郁寡欢的父亲,40多岁时因为微不足道的小病死去。留下她和小五岁的妹妹,还有异常焦虑的母亲。除此之外,他还对她说:“你不属于这里。”这既是祝福,又是咒语,令她的青春期过得很不顺利。经过堪称残忍的竞争之后,她于1987年顺利考上北京大学,中国最好的学府(之一)。
那几年人们焕发了新的激情,这种激情是那么生动又盲目。李菁读文学系,坚信能改变世界的唯有文学:小说、诗歌……她齐耳短发,面部线条硬朗,是契合时代的美好女性。交的第一个男朋友也是时代之子:打篮球、理科优秀生。两个人相识于火车上。就像顾城和谢烨也相识于火车上。火车从河北途径北京开往上海,他在上海读大学。在她下车的之前,他搞清楚了她的名字和通信地址。两个人当时都是20岁。
虽然也可以打电话,但写信是每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阅读、写作,几乎是最高的品德。每个人都写很长很长的信,诉说和谈论,目的是为了寻找。寻找真理。
两个人假期在河北见面。在小县城里两个人都显得过分耀眼,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做。分别回到学校之后,依然只是写信,写信。如果这算是恋爱的话,恋爱的时间大概持续了一年多。
“为了一件事关价值观的事情,跟男朋友写信吵了几个来回,现在听上去很傻,但当时却相当严肃。总之是关于诗歌,或者哲学,或者什么思想。吵得不能和解,就提出了分手。”
人生中的第一次分手,带来的感受非常恍惚,或者说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伤心是难免的,或许更多的是失望。对于爱情,他们都想得非常伟大,实现起来却又这么微不足道。正是这一点让她觉得自己愚蠢、脆弱。接着,爱情,或者说关于爱情的信仰,再次战胜了一切。她想把爱情寻找回来。就像那个年代所推崇的一样,爱情和自由,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而他们迟早都会拥有。
又一个暑假即将来临,李菁收拾了一点行李,坐上了从北京途径重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三峡非常美。而她回忆起三峡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那份美变得难以形容,也难以诉说。天气很热,人们不愿挤在船舱里,不分昼夜地跑到甲板上放风,陌生人之间互相交谈,一起抽便宜的烟,分吃各自的食物。空气里都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味道,人们既希望早点到达终点,又希望旅程永不结束。
李菁穿了一条浅色的裙子,在她记忆中那是一条白色的裙子,纯白的。后来从仅存的照片上看来,那其实是一条浅米色的棉布裙。她靠在栏杆上,努力想摆脱一个没完没了跟她搭讪的供销科科长。他那年29岁,为了卖厂里产的医疗器械,其实就是针管和血压仪之类的,走南闯北,见到漂亮姑娘就拿烟,“船舱里还放着酒呢”。李菁既好奇又有点害怕,也感到不耐烦。她皱了皱眉头,忽然身后有人喊她:“李菁!”
竟然是同校同级但不同系的女生,非常面熟,但一时想不到名字。这一点并没有产生什么阻碍,她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那个女生身边还带着她的男朋友。“志强”,她介绍说。志强则喊她小丹。她想起来了,那个女生叫罗丹。
她们在一些所谓的舞会上见过,虽然没有什么交集,就像一个漂亮女生永远会知道另一个漂亮女生,她们对彼此的了解比表面上多很多。
罗丹是个上海女生,娇滴滴的,烫了卷发。志强也是上海人。可以说,上海男生超过了李菁从小生活中对男人的认识范畴,作为一个北方女生,她被上海男人这一群体给震撼了。他们都很干净、温和,喜欢洗衣服,白衬衫的领口不会泛黄,去到餐馆很会点菜,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北方的菜肴充满了失望。
志强又高又瘦,瘦得离谱,但眼神发亮。他是李菁见过眼睛最亮的男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相识于水上。或许在水的映衬下,每个人的眼神都会更亮一些。谁知道呢。李菁对他的好奇也仅仅是一个漂亮女生对另一个漂亮女生男友的好奇。
他们一起站在栏杆旁边,连绵的群山绵延而过,江水翻腾。
李菁和罗丹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学校里的事情,考试啊,老师啊,同学啊。他站在一边,穿着一件灰色衬衫,不是广受欢迎的颜色,大部分时间都垂着眼睛,闷闷不乐。
“下面的汽油味很重。”他说。
“我喜欢闻。”李菁说完又继续跟罗丹说话。
对于未来,她们都很乐观。
“志强想出国。但我觉得未来就在这里。”罗丹说。
“嗯,当然。”李菁毫不怀疑这一点。刚刚打开的视野让她对一切都目不暇接。
志强抬起眼睛看了看她们,什么都没有说。
罗丹和志强住在上一层,就是更贵也更好的那一层。是觉得无聊所以下来玩。楼上一层是有餐厅的,罗丹邀请她上去一起喝茶。她跟志强讲话时说英语,他们都是英文系的,平时互相锻炼口语。即使李菁的英文非常差强人意,她也能听出志强标准的英式口音,他的口语比罗丹好上十倍不止。当他说英语的时候,仿佛是另一个人。李菁几乎是不得已的,无法自控地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看。
他们讨论的东西,即使过了很多年,对于李菁来说依然是个谜,是遥远的,不可思考之物。很多年前她跟另一个阶级的人坐在一起,不知道那是什么隔在他们之间,那条隐约的河流还没有被劈开,双方均茫然不知。
他们在船上玩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她偶然从一本书里翻出三个人的照片,才想起这段滑入时间缝隙中的旅程。才想起有一天晚上,她上二楼去找罗丹,在楼梯口碰到志强正要往下走。“给你送蚊香。”他说。除了蚊香还有一本书,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下船之后你本来要去做什么?”志强问她。
不知道为什么她撒谎了。“只是随便玩玩。”
好像沉思了很久,他才字斟句酌地说:“可以一起。”
窄窄的楼梯上,风吹得她的头发横了起来。
到了上海之后,李菁住在一个高中同学的大学宿舍里,究竟是什么阻拦了她。她没有去找男朋友,仿佛她把此行的目的全部忘记了。她去了几个景点,百无聊赖。大部分时间她都躺在长风公园树荫下的草坪上看书。
有天黄昏,她回到宿舍,志强正站在楼下,他一定已经站了很久很久了。
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了。李菁发现自己对感情这件事,既天真又惶然,既真诚又过度。她一点疑惑都没有。他象征性地摸了摸她的头发,然后说第二天中午再来找她,带她出去吃饭。
2
我跟李菁认识的时候,她已经37岁了。我刚刚到报社实习,24岁。高中时我因为读了杨澜的《凭海临风》,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象,立志要去当记者,采访有趣的人。
杨澜与李菁同一年出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与志强同一学院。然而等我毕业的时候,记者这个职业已经风光不再,豪情壮志也付诸东流。我们那代几乎都成了犬儒主义者。大部分同学都进了政府部门做宣传工作,小部分去了报社或者电视台,也不是做新闻,有些做综艺节目,有些跑政府条口。我索性当了编辑。
工作非常悠闲,我经常在办公室晃荡,看到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转悠了几天后,李菁才出现了。她很时髦。表情很犀利。我有点害怕。但她出乎意料的和蔼。我向她借书,她随手抽了一本给我,《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写得一般。”她顿了一下,仿佛有点抱歉,又接着说:“但你可以看到一个被摧毁的女性如何重建自我。”对于这样书面化的语言,她并没有表示出不适应。与其它人的反应完全相反,我被她严肃的腔调吸引了。
她是另一个部门的编辑,主要负责阅读板块。那是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就是网络刚刚兴起,传统媒体依然活跃的几年。烦恼也不是没有,但更多的好像是平静,是不知前路的好风景,午后的昏昏欲睡。无非就是高高兴兴做完当天的版面,一起吃饭聊天喝咖啡。四季分明,空气清新。慢慢的,我跟她变得很亲近,有点奇怪但也并非不可想象:我们成了朋友。
她并不适应南方。冬天对她来说太冷了,室内没有暖气,我们都冻得发抖。夏天又太热。她对北方食物依然有依恋,经常找我一起去吃。她的同学大多在中央电视台或者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而她却在这里:南方一个小城的市级报纸。
于是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会来南方,而没有留在北京。
“因为恋爱谈得不好,逃过来的。”她笑笑说。“以为一切都是暂时的。我迟早还是要回到北京去。但没想到,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我哪儿都没能再去。”
她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丈夫。求婚的时候,丈夫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走,我都会放你走的。”
就是被这句话打动的。结婚的时候她已经30岁了,也就是1998年的事情。
因为工作闲散,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混在网络论坛里。李菁建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俱乐部,叫“星期六读书会”。每个周六大概会来10个人左右。我们爬山、吃饭,偶尔谈论一下各自在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
那时我还相当无知,尽读一些流行的东西。村上春树当然读,还读亦舒,读麦卡勒斯,读朱天文。没有概念,乱读。新闻报道越来越难做了,我们躲进书里,装作一切跟自己没有关系。就像很多人躲进钱里。总之,这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因此我们也没有什么不适。
我喜欢读书俱乐部里一个男生,她当然也知道。我们试图分析他对我到底感不感兴趣。李菁经常特意安排他送我回家,吃饭时让我们坐在一起。
两三次之后,她说:“这种事真是没办法啊。”
就是那段时间,她从家里翻出了一张旧的合影,在《月亮与六便士》那本书里,夹着她跟罗丹和志强的一张合影。怎么会有这样一张合影?她百思不得其解。她已经完全不记得曾经拍照这件事了,谁拍的?为什么拍?毕竟已经接近20年时间过去了。
“他要来接你吃午饭,然后呢?”
她笑了笑:“我们当时,对于一切都太绝对了。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绝对的东西。包括真理都未必是绝对的。但后来我们领悟这一点之后,又做了太多太多的妥协。”
我们在夜色之中,在树影下,没完没了地走路,那是属于我的20多岁。当时我喜欢的作家,如今已经不喜欢了。当时我喜欢的衣服,如今已经不穿了。当时看得热泪盈眶的电影,现在已经觉得厌恶。就是这样。可能所有人都是这样。
有一天我独自逛街回来,筋疲力尽地拎着一条破洞牛仔裤和条纹T恤,幻想即将到来的夏天,我将既时髦又颓废,既快乐又伤感。说不定可以约喜欢的男生去海边。我坐着公交车,中途毫无预兆地在一个小公园下了车。我像喝了酒一样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无穷无尽的欲望折磨着我,却都无法达成。我盲目地在公园里面走着。然后就看到了李菁,和一个看上去比她年轻一点但好像又不是那么年轻的男人,以半米远的距离正在散步。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让我困惑的东西。后来我意识到是一种全然的陌生的气质,外来者。应该是一个长期旅居国外刚刚回国的人。
李菁非常自然地跟我打了招呼,就好像我们早就约好要见面一样。我就是这一刻才忽然意识到她一直是这么的亲切,这么的让人放松。我不禁想象她曾经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女生,而这种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为强烈。她有一种冬日太阳一样自然和煦的天赋。
她向那个男人介绍我:“一个很不错的小朋友。”
又向我介绍:“一个老朋友。”然后她停了一会儿,仿佛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又担心失礼一样。她看着我说:“他叫段志强。”她有点紧张,而我知道她是担心我的反应过于过度,但我很明白,只是笑了笑。
那么,就是快20年了。他们再次见面了。
遇到他们俩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终于向送我回家的男生发出邀请:“要不要上来喝点东西呢?”
在渐渐降临的暮色中,他犹豫地说:“……还是算了吧。”
也并非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我在第二年咬牙去了北京的一家网站。
3
再见到李菁,已经差不多是3年之后了。她40岁,而我27岁。我们很高兴地约好了在北京见。这之间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刚开始是MSN,后来MSN死掉了)维持着最低程度又波动型的社交。波动型是指我们在彼此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聊得很多,甚至打很长时间的电话。网站的工作我不喜欢,但这份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升职很快,收入变得越来越高。相反的是:她所在的报纸,运营则渐渐变得有点困难,令人焦虑。记者和编辑不再有优哉游哉的心情,读书俱乐部早就不办了,有些记者开始领了广告任务。但也仅此而已。大家感到的压力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这个行业依然屹立着,有人乐观地写道:报纸百年不死。
我们在北京的“雕刻时光”见了面喝咖啡,当时这是很热门的一家咖啡店。她心中火苗还是那么炽热,导致她的形象并没有随着时间衰老。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觉得她更年轻了。也可能是我老了。
我们聊了一些各自的现状。我跟做程序员的男朋友过着无滋无味的同居生活。对于未来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本来就是没有未来的城市。”她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方,人们的命运大浮大沉。”
她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20年过去了,这算是初期的一批名校大学生,时代骄子,无一例外,统统成功了。当然是指在现场的。有些人已经消失了。有些人在更早的时候就消失了。
然而激情。激情是这一代一直在怀念并且假设永恒存在于自身的东西。他们喝酒,忘记自己已经发胖、打着官腔、头发掉了大半。中途有人爬到桌子上念诗。
气氛昂扬。李菁关心的却只是原来班上一对金童玉女。男生当时是班长,现在已经是一个斯文体面的官员,身上有一种被长期吹捧导致的矜持和自得。女生当时是班花,非常美丽独特。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李菁为之伤心难过。就好像是自己的缪斯死去了。就好像一个时代死去了。在她眼中,那两个人是不折不扣爱情的化身。最后却分道扬镳,划出了两个时代。
女生迟迟没有出现。快结束的时候,一个打扮非常干练,将西装袖子挽上去的女人急匆匆地来了。她还是那么美,简直更美了。还有她拿着酒杯的姿势,就好像是专门就这一件事认真练习过但这种练习终于变成了她习以为常的东西,一种优美的体态。她去法国学了艺术,后来做过豪车代理,赚了很多钱,现在开画廊。她与自己的初恋,呈对角线站立,她没有看他,但她的余光一直看着他。而他也一样。这一幕或许只有李菁注意到了。她天真地观察着他们,期待自己能看见一幕令人唏嘘的重逢。
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两个人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对视。围绕他们的仅仅李菁炽热的目光,一个时代的微不足道的旁观者。
之后李菁去了一趟加拿大,探望志强和罗丹,据说罗丹身体不好,病得很严重。“当年是因为要出国才跟我分开,回到了罗丹的身边。闹得很厉害,我逃到南方来……然后几年前他回国来找我,好像很有悔意,但都已经过去了。”
并没有唏嘘多久,又说道我曾经喜欢的那个男生,他最近调了职,进了地区的政府部门。
“肥差。跟建设有关,就是跟房地产有关。你也知道房地产是怎么回事了。”
她斟酌说:“还以为你们这一代,80年代出生的人,你们会得到另一种幸福。可能就是我们幻想过的那种幸福。然而并没有。”
也不是。也不能这样说。我想自己毕竟是拥有了,或许是一点点无用的自由。我小心翼翼地买了一间小公寓,在房价还能承受的时候。我建立了自己的城堡。
喝完咖啡之后,我们在北京街头走着。北京跟南京大不一样,是一个不适合散步的城市。我们走了一会儿,无计可施,各自打车离去。
4
从机场回城的路上,我被堵在了三环。据说北京现在雾霾很严重,但这一天却万里无云,蓝得透亮。就像我曾经无数次看过的那个天空一样。我几乎出神地看着,根本不在意时间的流逝。司机越来越焦躁,但装作没脾气的样子,跟我聊起天来。
“到北京来干嘛的?”他问我。
“卖房。”我诚实地说,7年前买的那个小公寓,价格已经翻了很多倍。
“哎呦有钱人哪竟然在北京有房。最近价格又涨了,哎呦。您不再等等?”
“不等啦。我在美国买房也需要钱。”
六年前说起我要出国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当回事。互联网正在迎来新一波的机遇和热钱,机会很多,钱也很多。后来我的朋友们,纷纷出去创业,动不动谈的都是几千万上亿的生意。
我决定出国读书,一个没有什么用的学位,艺术策展。也并不是说我喜爱艺术,只是恰好有机会申请,读起来也轻松。总的来说只是想离开。我在美国遇到了我的第二任丈夫,并不重要,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出国跟离婚也有点关系,说不清楚是为了离婚才出国,还是为了出国才离婚。总之那一年,就是我30岁的时候,我准备把一切都抛弃得干干净净的。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菁了吧。她到北京来跟我汇合,去听崔健演唱会。
等我们真的再见时,她的变化令我吃惊,仿佛衰老一下子到来了,头发灰白,皮肤干燥,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是那团火熄灭了。
“别惊讶。别忘了我已经快50岁了。”她笑起来,“半个世纪呢。”
我们夹在人群中,跟着往里走,人们嘻嘻哈哈,拿着荧光棒。然而间或着,里面夹杂着几个仿佛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上了年纪的人,过分稳重的人,从来不看演唱会的人。或许这是全中国观众平均年龄最大的演唱会。
我们既陌生又亲密。几年前出国时,她帮了我很多忙,帮我求助了很多老同学。她的老同学们对她别有一番尊敬,或者说是,怜爱。仿佛她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作品。唯一的婴儿。报社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而挣扎也没有用了。她被在各个部门间调来调去,盼望着可以提前退休,然而仿佛遥遥无期,挫折和失败把时间拉长了。
志强经常给她打电话,天天想要回国,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他独身一人,离退休还有好些年,眼看国内形势倒转,有点慌张。做了一辈子的异乡人,逃脱了很多东西,包括本来应该得到的。“但在国内的我,也并没有他以为的那样,得到时代赐予的什么好处。每个人都落空了不是吗?”
她带着很严肃的表情。她并不是来享乐的,可能是来告别。这令我想起多年前我陪她特地赶到上海去看罗大佑的演唱会,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好像赴一个迟到了很久的约会,一生仅有一次的约会。然而之后他开了一场又一场,一场又一场。
崔健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蓝色骨头》。他把《假行僧》献给已经去世的鼓手三儿。
可能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等我发现的时候却已经又过了几首歌了:李菁在人群中无声的流泪。也可能是大声的流泪。但周围那么吵闹,她的声音无人听见。
演唱会结束后,她跟我回到北京将要出售的房子里。租客已经搬走了。只剩一片狼藉。我从储藏间里翻出了已经变色的那套《光荣与梦想》。
我在20多岁时喜欢的那个男生,当时还在报社工作。我喜欢他是因为有一天他说:“迟早我也会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多么天真啊。我在那一刻喜欢上了他。
我翻出来,让李菁带回去,探监时给他。
从记者到受贿被捕……这几乎是个人不可抗拒的命运,是时代给与的奖励与惩罚。
爱情与自由。金钱与梦想。最终并没有人得到。
而我们俩,作为各自时代的逃兵,我们身上既缺乏诗意的部分,又缺乏坚强的部分。
两手空空。我们就这样迎向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