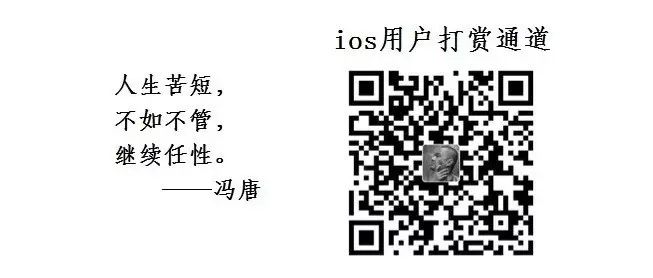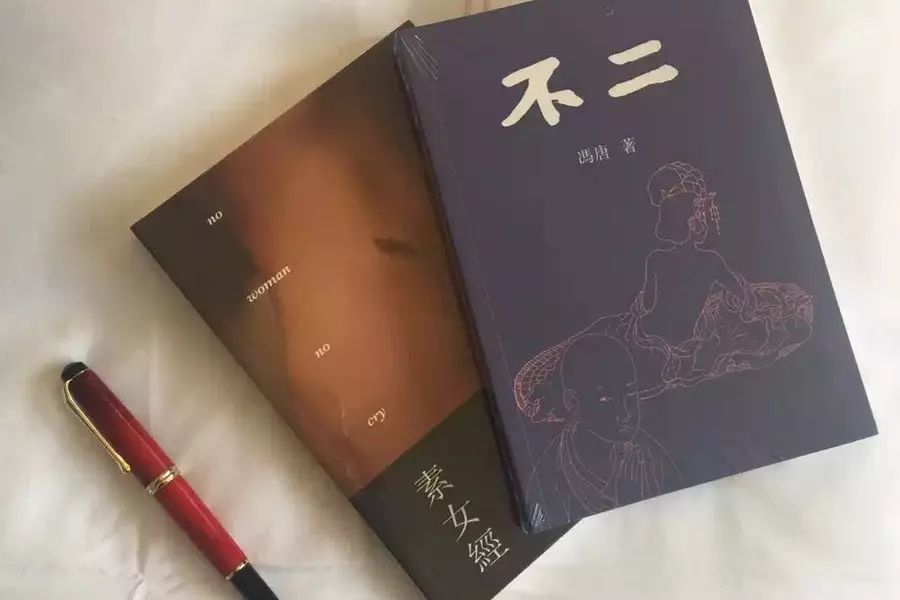
说明:颜纯钩先生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前总编辑,是《不二》的编辑,是我敬重的编辑。经颜先生授权,现刊发此文,以志纪念我们的文字之缘。
冯唐是我退休前合作最多的内地作家,五六年了,出版了他几本新作又几本旧作,其中《不二》成了两岸三地出版界的一个话题。
冯唐最近在他的专栏里写到和我的合作关系,似乎对我的印象还不坏,当然,整篇文章读下来,发现他的感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而是因为和他合作过的其他编者和出版商都不那么好,相比之下,似乎我和我服务的天地图书,就成了这个他说的“末法时代”的稀有动物了。
想起和冯唐的合作,也是一个人结人缘的故事。先前内地有个牛博网,那里聚合了一批内地思想新锐又放言无忌的文化人,我于是经常在那里流连。有一段时间发现有不同的作者在那里谈论一本叫做《不二》的书,那么多人兴致盎然,应该有点看头,于是我到处寻找《不二》,想看看究竟。结果当然找不到,因为这本书根本还没有在内地出版。
后来我就到处去找冯唐,网上数据显示他是内地中青代有代表性的作家,据说在某次全国性的评选中,还得到最受欢迎作家排名第一的席次。我想找到他,请他将《不二》的原稿给我看看,如果合适香港市场,也可以考虑出一个繁体字版。
上海出版界的老朋友王为松、陆灏两位,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冯唐的手机——原来他竟然在香港,而且写字楼在湾仔华润大厦,从他办公室步行到天地图书门市部,走快一点十五分钟可到。
我打电话给他,说明来意,他惊奇地问:“天地图书不是在台湾吗?”我说我们门市部就在电车路,靠近修顿球场,你中午吃饭后散步过来,到门市部看看书,先了解我们都出版了什么书,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把文档给我。
后来他大概真的来门市部走过了,打电话给我,一起饮了茶,《不二》也就来到我手上。
看了稿,我真正倒抽一口凉气:这是什么书?简直胡闹!把唐朝时代的几个大名人:韩愈、唐高宗、禅宗六祖“炒埋一碟”,中间穿梭一个妓女鱼玄机,外加一个小和尚。一个妓女把文化、政治、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都搞上床,搞得天昏地暗,不亦乐乎。说它是历史小说,中间没有什么家国大义、起承转合,说它是淫书,写性爱也只是就地正法,招来招往,这种书出版有什么价值?
稿子放着,不敢拍板,过几天突然想通:这不是淫书,这是一本奇书,它把世间高人都拉下来了,文化、政治、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也不过就是寻常人一个,五情六欲齐全,人所具有的劣根性他们都有,他们都没有败在自己的事业上,但都败在一个女人手中。
有了“奇书”这个定位,我的心也定了。《金瓶梅》不就是奇书吗?《红楼梦》《西游记》都可入奇书行列,《不二》当然不在这个层次上,但既属奇书,也必然会有好奇的读者看,香港是出版自由的地方,只要不违法,理论上什么书都可以出。
签约前有一个小波折,原来冯唐和内地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是好朋友,大概听说了天地要出版他的《不二》,李银河好心地提醒冯唐要小心天地图书。冯唐写电邮给我,委婉地提到李银河与天地合作中间的一些龃龉,大概想看看我会有什么说法。
我回电邮给他,说和李银河之间的确是有一些不愉快,不过那都是在出版行业不规范的年代发生的,现在公司的管理都已计算机化,一切有数字说明,不必担心。
于是赶紧签约,赶紧发排制作。冯唐对香港市场不了解,也没提出什么特别要求,初版也就是最基本的条件,他的想法是能出来就可以了,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反正都没抱多大期望。
书出来后惹了一点事,《亚洲周刊》一位书评编辑,有一次和我一位同事说:你们天地图书怎么会出这种书?言下之意“天地”颇不堪。同事赶紧回来报告,董事长赶紧招我去问话,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们说明了,同事问,那怎么答复他?我说你就说已经把他的看法转告给责任编辑了。
此外基本平静,香港人见惯古怪物事,也没有人会来兴师问罪。但后来,《不二》开始受到两岸三地读者的欢迎,当年香港书展就把冯唐作为书展特邀作家邀请来了,他在书展做了一场演讲,观众坐满一个三四百人的大厅。书展作家讲座就是由《亚洲周刊》主办的,老朋友江迅没有受到他同事负评的影响。
《不二》很快再版,而且一版再版,加印到我们不敢想象的数字。每次加印我都会写电邮通知冯唐,书出来后即计算该版次的版税给他,他的版税率也因版数增加而不断提高。
后来他的其他新书也相继由天地图书出版,新书未写出来,就梅花间竹地出版他的旧作,这些书当然都没有《不二》的销售盛况,但因为《不二》,冯唐广受港台两地读者欢迎。
作者与编者,本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天地图书因为冯唐,当然也赚了不少钱。作者与编者,好则双赢,坏则互伤,如果不能建立理性、健康、互信、恒久的关系,双方最终都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理论上说,谁没有谁都活得下去,天下有多少作者,天下又有多少编者?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但如果一个作者或编者,都如此不在乎对方,如此自私任性,那你的砒霜,很容易就变成他人的熊掌,你眼睁睁看着自家煮熟的鸭子飞了,岂不要捶胸顿足,吐血而亡?
作者与编者,最值得重视的是互相之间的信任感。作者把稿子交给你,他自然期望你好好经营,用心筹划,不负他汗血精神;书出来了,他要相信你用心发行推广,让更多读者知道;书卖出去了,他要相信你能依合约支付版税,版税多少是另一回事,但隐瞒销数是不可接受的。
这方面我有深刻教训,做出版不只是成功时的开心,出纰漏时的沮丧懊恼,也真是不足为外人道。
上文提到的李银河,是内地著名社会学家,应该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那时她就是内地研究同性恋文化的先行者,她写了一本通俗性的研究报告叫《中国同性恋群落》,这本书当年在内地也出不来。忘记通过什么管道,书稿来到我手上,我一看“惊为天人”,马上与她签约出版。
一两年后,李银河来香港,我陪她饮了茶,带她到天地门市部走走,走到天地图书书台前,李银河突拿起一本书来说,这不是我的书吗?怎么已经换封面了?那就是再版了吧?
我一看登时呆掉,我完全不知道书再版的事,连封面都陌生,剎时间脸孔发热,两只眼睛不知朝哪里看,只恨自己不能像《封神榜》里的土行孙那样,脚一跺就遁地而逃。
当年香港民间出版都还在后草莽时期,公司执行董事负责印务、发行和财务等,我在前边编书,编好了交给他去制作,之后的再版、计算版税等等都不关我的事。上司加印旧书,内心窃喜,钱哗哗流进来,早就忘掉那个在前边编书和作者打交道的编辑,也不觉得有义务向作者报告。公司出的书多,每日案头工作堆积如山,去门市转一圈都要小跑,如此也就很难发现书海中有一本自己经手的书被悄悄再版了。
此事的结局,当然是道歉补付版税了事,但因此就给李银河留下很不堪的印象。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次,那是一本以志愿军战俘命运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书名叫《厄运》,作者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钱钢的夫人于劲﹙她刚刚在不久前不幸因病离世﹚。有一次钱钢来香港,我又陪他到门市部走走,他在天地图书的书台前又拿起一本书,说这不是于劲的《厄运》吗?换了封面了。他抬起狐疑的眼光看我,我又心里一凉,脸又不知往哪里放了。
时间太久了,我已忘记两件事的先后次序,或许李在前于在后,或许反过来。发生第一次后,我已向执行董事抗议过,他“咿咿哦哦”,事后又不了了之,压根儿不管在前方与作者打交道的编辑,如何承受那种好像做了小偷被人当场捕获的憋屈。当然,“厄运”又一次落到我头上,我又一次厚着脸皮向钱钢认错,公司又一次补上版税。二十多年过去,事过水无痕,但我一生无法放下自己职业生涯中这两次巨大的羞惭。
欺骗作者版税,表面上是一种利己的行为,想深一层,其实是害己的蠢事。一个作者能让你骗一次,不会让你骗第二次,不但如此,你骗人的行径会因为一次次暴露而使你在江湖上声名狼籍,那时除非愚蠢的人,否则大家都会离得你远远的,你想想,你还想打什么好作家的主意?
因此,直到我负责编辑部的事情后,我就和董事长陈松龄先生商定,从今以后一切照规范来,合约可以定得紧一点,但付版税必须认真。此外,有任何再版的书,应该实时通知责任编辑,由编辑向作者报告。陈先生完全支持我的主张,这个制度也就基本上确定下来。
作者写一本书不容易,出版社若没有诚意,何必和他合作?作者把书交给你,对他来说是一种风险,你接受了作者的书,对你来说也是风险,互相分担风险是合理的事,互相分享所得就是应份的事。一本书再版,出版社已经赚钱,作者的版税只是把出版社赚的钱分出去一点而已,付作者版税不会付得让公司亏本,因为双方所得的总和全部都是利润。出版社骗作者稿费,往小里说是贪婪,往大里说是丧失职业道德。克扣作者所得,这是奸商的行径,不是现代出版人应有的专业操守。
收到冯唐的电邮,才想起多年来与作者打交道的苦涩,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只是想让年轻的图书编辑们明白,曾经我们也没弄清楚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而那些关系的准则,应是我们职业生涯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