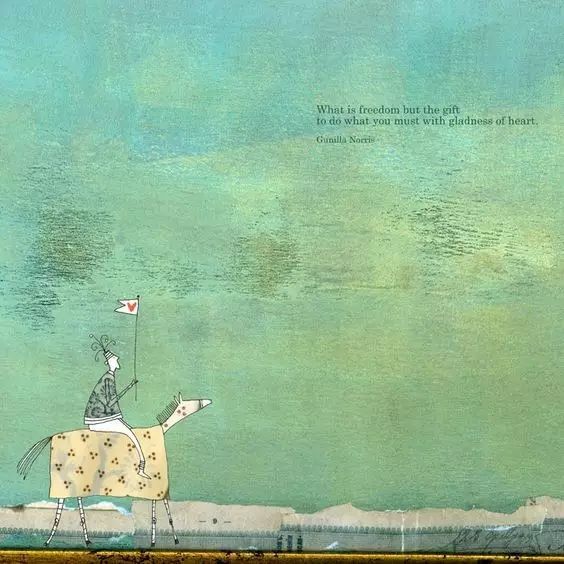你跑了那么远的路,只是为了摆脱怀旧的重负。

我想:人到生命的某一时刻,他认识的人当中死去的会多过活着的。这时,你会拒绝接受其他面孔和其他表情:你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印着旧模子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佩戴了相应的面具。

时间流逝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感觉和思想稳定下来,成熟起来,摆脱一切急躁或者须臾的偶然变化。

记忆也是累赘,它把各种标记翻来覆去以肯定城市的存在; 看不见的风景决定了看得见的风景。

时间的维度被打破了,我们只能在时间的碎片中爱和思考,每一个时间的碎片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在瞬间消失。

记忆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来:这才是你在旅行终点的发现。

“在梦中的城市里,他正值青春,而到达依西多拉城时,他已年老,广场上有一堵墙,老人们倚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当初的欲望已是记忆。”

波罗说:“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

“有时一个人自认不完整,只是他还年轻”——我们都是由不完整在寻找自我完整的过程:最初的自我分裂——自我否定——自我斗争,直到最后,自我和平,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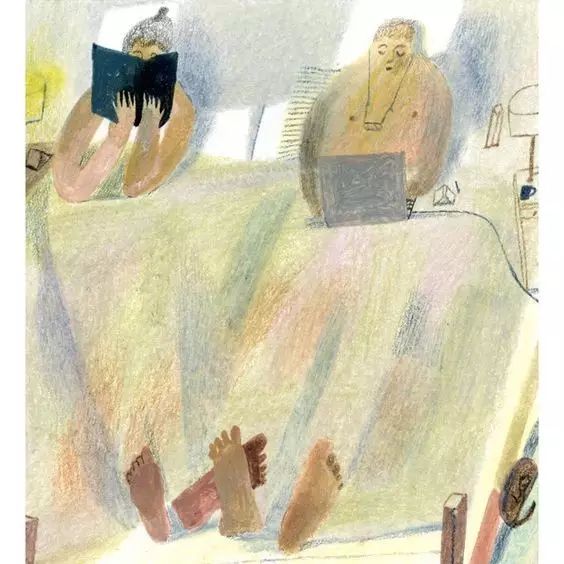
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绵延不断,比生命更长久。

那天早晨家中的各种气味与声响都拥向我的身边,仿佛要与我告别。至今我所熟悉的这一切,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它们,可能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样了,我也变样了。

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沿着这些白线向前或向后奔驰。没有出发点,也没有目的地,这些白线只是不断逼近,里面挤满了情感,最终从填满了我们的人、声音和状态的厚度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些发光的标志,成为让需要的人用来辨别没有在嗡嗡声中变形的话语的存在,让我们以及其他人的存在变成我们所说的话。

当然,代价是高昂的,当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不能在这条路上众多的标志中辨识出彼此,每一个人的意义都变得隐蔽并难以捉摸,因为在此之外就没有人可以接收到我们、理解我们。

这座城市不会诉说它的过去,而是像手纹一样包容着过去,写在街角、在窗户的栅栏、在阶梯的扶手、在避雷针的天线,在旗杆上。在每个小地方,都一一铭记了刻痕。

我经历的一切往事都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毛毡,毛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

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人难免天生有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每人都有别人不知道的创伤,我们战斗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创伤。

波罗善于顺从皇帝的恶劣心境。“是的,帝国染上了疾病,并且还在努力使自己习惯于自身的伤口,而这是更糟糕的事。我探察的目的在于:搜寻尚可依稀见到的幸福欢乐的踪迹,测量它缺失的程度。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

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最好的愈来愈难满足,我在提前品尝年华老去的无比喜悦。

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又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

总有一条路你必须走,总有一条路你必须放弃,选择根本就是放弃的同义词。

人们无法判断谁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因为每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和秉性来定义幸福。
从生命拥有者的观点来看,生命不能以质或量来评估,也不能与其他生命做比较。它的价值就在它本身,以至于期待或恐惧来生都是妄想。
随着死亡而来的是不存在,这种不存在与出生前的不存在是等同且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