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
通常
那些开头低调舒缓的作品往往是最优秀的。
作者开门见山的那句话也许语不惊人,不过后面的内容却没有让我们感到上当受骗或者失望。所以,无论开头是什么情况,你都要做到持之以恒。

有些作品开门见山的数行文字势大力沉,你绝对会手不释卷地把它读完,这就是人称“钩子”的东西。
大部分优秀
作家都要使用某种形式的钩子,从梅尔维尔的那句
“叫我以实玛利
”、“社会公敌”,(《白鲸》),到加缪的“马曼今天死了;或者是昨天,也许吧,我不知道”(《陌生人》),再到卡夫卡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变形记》
),莫不如此。
尽管公众多有误会,但钩子却不仅仅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如果运用得好,钩子不仅是一枚推进情节发展的火箭推进器,而且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醒目地昭示在下面的内容中读者可以期待的精彩。它既可以确立人物的形象、叙事者的态度,也可以烘托整体的氛围,或者传递令人震惊的消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必须把这么多东西浓缩为一句话。由于可供腾挪转圜的空间有限,于是乎钩子就变成了博弈的游戏:施展拳脚的空间越小,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创新精神。所以文学史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名句就是由钩子构成的,这一点根本不意外。
不过,人们很少谈论钩子的重要性。它不仅仅体现于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而且体现在开门见山的第一段话;不仅仅体现于第一段话,而且体现在第一页;不仅仅体现于第一页,而且体现在整个第一章。换句话说,适用于开门见山第一句话的那种思想强度和专注程度不应该仅仅限于第一句话——人们对此普遍存在误解,而且同样也适用于整个作品。
这需要耗费极大的耐力、聚焦与专注。在这种强度下,哪怕要写出一个段落,甚至都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你可以看看自己作品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想一想你在其中倾注了多少心血。你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聚光灯下,所以这第一句话你必须写好。这一句话你曾经反复改过多少次?如果对于作品里每一句话你都以同样严谨的态度反复锤炼,那么作品的其余部分会是什么成色?或许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锤炼个没完没了的,啥时候能熬出头啊!
那么想一想吧:
瓦格纳花了36年创作《帕西发尔》(
Parsifal
)
。玛格列特·米切尔花了十年进行调查研究,创作出了《飘》。罗马诗人奥维德说过,一个人完成作品之后应该再等九年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
由此,我们还要讲到普通作者和优秀作家之间的另一个区别:
我们能否通过一句话感知钩子的强度?还是要通过一段话,乃至一页的内容才能感知到?或者整部作品是否都维持这一强度?当然,开门见山的那句话肯定是特别的,而且其强度也几乎不可能在整个作品中得到始终一贯的维持。
不过,我们至少还要再看看才知道后面的内容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这个强度,看看这个强度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奇怪的是,我通常看到许多作品开门见山的那句话都是非常精彩的,开篇的内容普遍都很扎实,而到后面这个强度就没有了。确实,第一句或者最后一句中表现出的那种强度在整个作品中都始终如一,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
有一个不错的例子,这个例子属于现代文学,摘自伍奥瑞的短篇小说集《裸浴》中的第一篇小说“金色”
:
在遥远的北方的冬天死去,就是要给冷藏尸体制造一个难题。一座不舒服的房子,只是稍微有点暖气,能让逝者在春天举葬的时候保持新鲜,尽管有钱人可以选择炸药和(有伸缩挖掘装置的)锄耕机的方法在冬天里埋葬,可是真正古老的墓地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这样开门见山的段落,如此奇异而且详细,读罢之后,谁还能把它放下?“钩子”是一个恰当的称谓,因为它的作用确实就像一个鱼钩:假如你刚刚钩住一条鱼,比如钩子挂住了鱼唇的尖吻部位,那么鱼还是有机会脱钩溜掉的。但是假如钩子扎得很深,比如穿透了鱼的整个腮部,那么鱼就是你的了。
大多数作者认为钩子需要做得很强大,足以吸引眼球才行。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而且往往会导致夸张的写作手法,出现过度补偿的现象。恰恰相反,有关钩子的问题你要牢牢记住一个关键所在,即钩子的功能是为整部作品定调子的。假如你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是强有力的,那么就给自己后面的写作备下了一块难啃的骨头。
在读者眼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并不在于最初的强度,而在于如何维持这种强度。作品要证明长远来看作者具备那种持久的耐力、耐心和专注。它表明一部作品是精心策划出来的,而不是作者拍拍脑袋、一口气写出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通常发现那些开头低调舒缓的作品往往是最优秀的。作者开门见山的那句话也许语不惊人,不过后面的内容却没有让我感到上当受骗或者失望。无论开头是什么情况,你都要做到持之以恒。
同样重要的是,作者要在一段、一页或者一个章节的结尾处使用钩子。在此处使用钩子至少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很多作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疏漏)。作者的成就在于创造出一篇强有力的作品,其强度足以使读者在章节停顿处把作品放下来(通常读者都是在此歇口气)之后,还想回到这个地方,重新进入小说的世界中。其实,读者这是要投入精力再从头读一遍。
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
要么在结尾处安排一个强有力的钩子,要么在理想的情况下,使用一个能够促使读者直接进入下一章的钩子,或者至少也能让他产生息息相关的感觉,以至于他不得不回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那些约略知道这个道理的作者认为,假如他们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尾钩,那就万事俱备了。这是另一个比较大的误解。我们必须牢记,作品里的一切都是累积性的。即便你的最后一句话非常强大,甚至最后一段话都是强大的,假如它们前面的内容是空洞乏味的,那么读者仍然会把它放下。这样的作品就像一场糟糕的肥皂剧,其本身是缓慢迟钝而且平淡乏味的,不过其结尾却是戏剧性的或者令人震惊的瞬间。
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个瞬间内部或者就其本身而言力度是不够的。我们不会再看下去,因为虽然那个瞬间可能很吸引人,但我们对于它前面的内容丝毫不会关心。另一方面,电视剧《蝙蝠侠》完全是另一种典型:这部电视剧编排得很好,以至于我们没办法不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并不单单是因为蝙蝠侠在剧终时发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更主要的是因为前面发生的事情,前面和缓的铺垫让主人公最终抵达逐步累积起来的巅峰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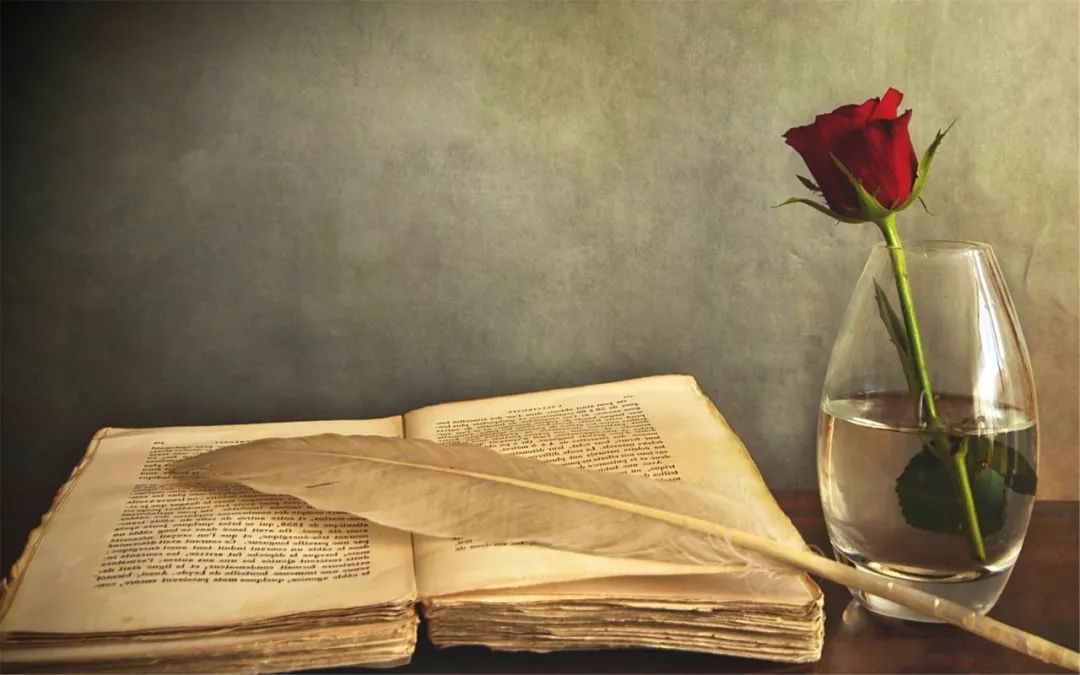
误用钩子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不过,通常其危害性还不足以让我把它放到探讨起步难题的那一部分。这是在糟糕的情况下不足以造成巨大的危害,但假如作者运用得当却可能对作品大有裨益的问题之一。
●最常见的问题是:往最糟糕处说,钩子是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正文似乎完全是另一篇作品,而且回过头来看,钩子似乎更像是一句俏皮话或者骗人的噱头,目标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已。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钩子和正文脱节,实际上并不是正文的一部分。因此解决办法是填补其间的鸿沟,把钩子和正文融为整体。
要做到这一点,你要么重新从钩子开始,由此出发创造出全新的作品;要么逆向写作,保留已经写出的文字,经过反思之后再写出一个钩子。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在提倡乏味的钩子。这里的挑战在于,你要有深具诱惑力的钩子,而又不能出现那种脱节的情形。这同样适用于章节结尾处的钩子。
●这个难题的一种变形是,钩子与正文是融为一体的,不过在强度和夸张程度方面则不成比例,也就是“过度激动人心”。这是危险的,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内容超出了我们的期待。
●另外一个常见的毛病是,使用对话作为开门见山的钩子。这是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而且几乎从来都不济事,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如此。主要的问题在于构建一部作品的内容需要有展示部分,而且必须逐渐把这个对话跟文本的其余部分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