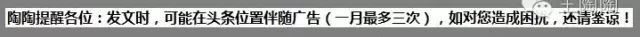法国大革命中,最残酷的恐怖暴政始于哪里?
在1792年的8月10日,那一天,法国的道德开始凌驾于法国的法律:
革命领袖雅克·丹东以“爱国道德”的名义,不顾基本的宪政法律框架
(此前国民公会不断在天主教问题上以公民道德的名义,挑战曾经与保守派达成的共识)
,向巴黎暴民们发出进攻王宫的呼吁,“法国的公民们,居住在那个宫殿里的人,没有一颗和我们一样的
爱国之心
,所以他必须受到人民的惩罚。”从此,法国的法律威信一败涂地,国家进入了动荡不安、以道德审判他人的恐怖政治阶段。
在法国大革命中,恐怖政治的最高潮在哪里?
在1794年3月30日,那一天,法国的
道德完全取代了法国的法律,公民道德的最高标榜者
罗伯斯庇尔在抓捕并处决战友
雅克·丹东
的时候,给出这样的理由:“美德一词曾让丹东发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自由的捍卫者?
(丹东曾与圣鞠斯特辩论,嘲笑了后者公民美德的论断)
”
而雅克·丹东也沦为了他自己所开创之道德审判的牺牲品
。
很多时候,道德的偏执往往意味着道德的乱政,尤其是道德淹没了法律的情况下。
道德审判之所以乱象重重,并非她的本性不善,而在于她的评判标准是如此的多样化,以致于极易沦为被有心者操控的工具。
评价一个人道德好坏的视角往往是多方面的:家庭的道德、公共的道德、职业的道德、国家的道德,皆有不同的标准和内涵。
某个偷窃的女人很可能是一位为了喂养自己孩子的慈母;某个贪污的官员很可能是一位为了回报父母的孝子;某个突然抢劫的土匪很可能只是
一位
为了孩子学费而苦恼的好父亲。
在实际生活中,上述案例数不胜数,我相信每一个阅读新闻的人,都能看到这样的故事,也在内心之中泛起过同情的涟漪甚至宽恕的冲动。
如果媒体在报道上面提到的偷窃案例时,仅仅谈到了偷窃,那么民众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个人有罪;如果媒体在报道偷窃时,强调这个女人偷盗是为了孩子,那么民众就会对这个小偷产生同情;如果媒体在报道偷窃时,还陈述了孩子的无助,那么民众很可能会给这个小偷捐款;如果媒体在报道偷窃时,还提到了被窃超市的冷漠无情和为富不仁,那么民众甚至就会认为这个小偷是无辜的
(因以前工作的关系,此案件中的舆论转变,本人就亲历过)
。其他案件同样类似。
事实上,由于缺乏在灰色边缘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民众往往
对完美的道德
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向往,其情感既敏感又脆弱,他们常常因震撼人心的感动瞬间而痛哭流涕,或者为了那些令人愤慨的只言片语而义愤填膺,却极度缺乏对法律规则的基本坚守。
这种单纯又愚昧的政治特性,往往使得那些舆论优势者能够轻易支配他们的情感。就像上述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舆论上取得优势地位者只需要在讲述案件过程的时候,刻意放大或者缩小某些细节
(考虑到现实人物和故事的复杂性,并不缺乏这样的素材)
,就能轻易煽动起民众的道德情怀,并主导案件的审判:
事实上,大多数现代专制或者暴民政权的构建,就是从以道德凌驾法律开始的。

2004年9月26日,陕西籍男子姜云春怀揣炸药进入兰州市东岗东路省文联家属院676号西单元503室向房主暴力讨债,由于担心姜引爆炸弹伤害周边居民,当地警方在姜出来以后,将之击毙。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在报道中普遍强调了
姜的农民工身份
,不断渲染故事的悲情,最终激起了舆论的巨大愤怒——却完全忽视了
当时周边居民的安危
,这恰恰是现场警方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
现代文明的先贤,为何要以法律而非道德来判断是非罪无?就是因为经过无数前人经验的积淀,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完善了可能被扭曲的细节,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努力维持最大程度的公正。只要法官对法律的尊敬,能够严格防止个人
(亲情友情)
或者公众道德
(平等、博爱、多元文化)
的侵蚀,就可以确保不出现最糟糕的结果,并保证国民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因为,真正的法治是最不容易被扭曲的制度。
实际上,那些最糟糕的行政措施、最严重的社会灾难、最恶毒的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超越法治屡屡出现,所依托的恰恰是舆论操纵下的道德力量。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违背基本的法律常识,将大量非法移民堂而皇之的合法化,将是通过媒体不断鼓吹“平等博爱”,以道德的名义最终迫使最高法背叛了自己本应维护的法律,这反过来激发了美国国内的白人民族主义,造成了国家的不稳定;
在2015年,西方政府之所以能够违背基本的难民法律,大开国门,不顾后果地吸纳了数百万难民,靠的就是媒体对一张难民儿童照片的不断渲染,掀起了道德的海浪,淹没了西方社会的法治堤坝,最终导致了极右翼政治的崛起,并使得整个欧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窘境;
 难民危机始于道德压制了法律
难民危机始于道德压制了法律
同样,国内东北、山西等地,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屡屡以“为富不仁”、“瓜分国有资产”等道德借口,制造群体事端或者撕毁契约,最终使得投资者将这些地区视为雷区,再也不敢轻易涉足,这些地区的经济也一路破落
(
俄罗斯、拉丁美洲类似,充满道德狂热的地区,往往不尊重法律和契约,也很难发展起来)
道德破坏法治最糟糕的恶果集中体现在暴民和专制政治上。罗伯斯庇尔恐怖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就在于1792年
雅克·丹东以“爱国道德”号召巴黎的暴民,摧毁了法国的立宪法律体制,为后续血腥至极的道德暴政铺平了道路;列宁在俄罗斯的红色恐怖之所以得以构建,就在于他以平等道德为旗帜,摧毁了该国的宪法会议(1918年1月);而纳粹政权摧毁德国《魏玛宪法》的时候,恰恰是以“拯救德国”道德旗号,在国会通过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令(1933年3月)。
“让立宪会议见鬼去吧!没有平等就没有一切!……苏维埃将拿出国家拥有的一切给贫农和战壕里的士兵。资产者有两顶帽子,那就要拿出一顶给战壕里挨冻的士兵。你有暖和的靴子?那就在家呆着吧,工人兄弟需要你的靴子……”
——1917年10月,在涅瓦河右岸人民宫,托洛茨基要求
彼得格勒
士兵发动革命(随后彼得格勒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以致于列宁不得不封锁讯息和人口流通稳固体制)
“就我个人看来,法国、俄罗斯、南美洲相比于英美,之所以在现代化中动荡不安,就在于他们的国民和知识分子,崇尚道德而不是法律,缺乏对宪法的尊重,没有维系共识秩序的宪法权威,这种国民享受动荡和专制乃是其天生特性决定的。”——王陶陶《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论法治》
事实上,一部真正维持公正的现代法律,必然是不近人情的,也必然是凌驾于道德之上的。
她的威严不仅仅要超越私人的道德
(亲情友情,腐败的来源)
,更需要超越公共的道德。只有这样,国家的治理才能维持法治的根本,至上而下的公权力才能得到真正的限制
(专制政治)
,至下而上的民权利才能不超越应有的极限
(防止福利政治、暴民政治)
,各阶层的利益才能得到基本均衡,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保证。
 美
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痴迷于公共道德名声,缺乏对法律威严的尊重,她的出现恰恰反映出美国法律在左道德面前的不断溃败,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美国法度败坏的肇因之一
美
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痴迷于公共道德名声,缺乏对法律威严的尊重,她的出现恰恰反映出美国法律在左道德面前的不断溃败,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美国法度败坏的肇因之一
我从不认为法律能够带来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完美和绝对的满意,毕竟现实世界就是不完美的,但是我相信真正的依法行事可以带来最均衡、最稳定、最持久的相对公平。中国缺乏法治观念,不仅仅在于手握权力的政府,也在于民众自身的认知,更在于那些标榜法治和文明的知识分子。
就像1792年的布里索、雅克 丹东(律师出身)、1917年的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1946年的黄炎培、马寅初、储安平一样,知识分子们往往口头标榜追求法治,内心却充盈着不可遏制的道德冲动,无时无刻不以理想国的标准苛求现实,将民粹鼻祖布里索、丹东式的道德腔调置诸于法律的威严之上,却不知,这只是鼓动暴民政治的蠢举。
 据传记作家描述,“他(雅克 丹东)的身形高大,他的性格活跃,他的五官鲜明,粗旷,和令人不快,他的声音可震撼大厅的穹顶,他曾是人民心中公认的道德代言人”——前律师丹东最终死于不道德的罪名之下
据传记作家描述,“他(雅克 丹东)的身形高大,他的性格活跃,他的五官鲜明,粗旷,和令人不快,他的声音可震撼大厅的穹顶,他曾是人民心中公认的道德代言人”——前律师丹东最终死于不道德的罪名之下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真正热爱这片土地,那么不如从尊重法律的权威
做起,少谈点道德,多讲点法治,一步步改善当前的现实,使之成为一个尊重契约、权限分明、不做蠢事的国家。这或许不是一个让人完全满意的选择,但却绝不会是一个让人悔恨的错误。
++++++++++++++++
至于于欢的先生命运,交给法律裁决就好,聊城的案件,不幸的不仅仅是于欢一家,还有银行的储户和其他借贷人,以及另外五个不幸的家庭——与其他事情一样,当舆论的焦点聚于某一个瞬间时,就很难不出现偏颇,这就是为何法律的威严更为重要。(我极其同情于欢,但我更尊重法律)
个人分答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