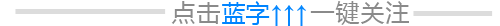

原载于《北京日报》2009年4月21日,经公众号“北京日报纪事"(微信ID:bjrbjishi)授权转载。
黑龙江省东北,萝北县。这是一座距离北京1600多公里的边陲县城,位于“北大荒”的腹地。
也许人们并不知道,新中国诞生以后,最早走进这片亘古荒原的志愿者,是67名来自首都北京的青年人。
1955年秋天,在萝北县附近布满草甸和森林的荒原上,这67名青年组成的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用马拉大车、肩挑背扛的方式,开垦出一片片耕地,并建起了一个浇灌着青春和热血的集体农庄:北京庄。

在他们之后,10万转业官兵、54万知识青年陆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大荒,拉开了中国垦荒史上的壮丽一幕。
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不仅用言词
而且用行动
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长几寸,
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
正向我们飞奔!
1955年11月,当著名诗人郭小川满怀激情写下这首长诗的时候,他触碰到了时代的脉搏。
就在诗人落笔的2个月前,一支由67名北京青年组成的志愿队早已开始“向困难进军”。杨华、庞淑英、李秉衡、李连成、张生,是这支队伍的5位带头人。

1955年8月30日,杨华率领垦荒队登车北上
2009年,5人中唯一健在的杨华老人已经77岁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成了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鲜明记忆。
1955年,杨华23岁,是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兼团部书记,庞淑英是门头沟区石门营乡的团支部书记兼妇女队长,李秉衡和李连成是南苑区团干部,张生是东郊区团干部。
作为青年干部的优秀代表,他们被安排到团中央集中学习,几个原本不大认识的年轻人在一次小组讨论上聚到了一起。小组讨论的内容在当时极具感召力:如何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
杨华提出个建议:“干脆组织一批人志愿去黑龙江垦荒。不需要国家出钱,完全靠自己的双手打出粮食,把荒原变成沃土。”
这个浸染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动与血性的建议,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另外4位年轻人的赞同。他们很快商量出一个大致方案。由杨华汇报给了组织培训的一位秘书。
当时,全中国有16亿亩耕地,但在一些地广人稀的边远地区,还有15亿亩荒原在沉睡。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但在社会领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粮农产品短缺的现象不断在全国各地出现。所以,“一五计划”写下了雄心勃勃的规划:完成1亿亩荒地的勘察工作,完成4000万亩到5000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了实现“一五”垦荒计划,早在1955年4月,团中央就组织代表团赴苏联学习,想参照苏联共青团垦荒的经验,寻找优秀青年去边疆垦荒。
杨华作为垦荒队发起人代表,提出了垦荒队的三条原则:一,必须做到绝对自愿;二,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三,去了就不回来,决不做逃兵。同时,也提出了第一批垦荒队优先吸收一部分会种地,懂农业的郊区青年为骨干,城市青年和女同志要稍后些等建议。
5个青年人以发起人的身份正式向团中央递交了志愿书,表达了开赴边疆垦荒的愿望和决心。1955年8月16日,《北京日报》全文刊登了杨华等人的志愿书,并从即日起开始接受青年报名。
在那个如火的年代,青年们的激情被点燃了。10天之内,前来报名处报名的北京青年多达587人。随后,来自全国19个省、16个大中城市青年的239封报名信寄到了报名处,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们将自己的履历、毕业证书、成绩单、身体检查的证明等直接寄给了团组织,希望能获得批准。
“半夜还有人找到我家要求报名参加。”杨华回忆。老人年岁已高,但依然能够一字不差地将当年志愿书的原文背诵出来:
我们是北京郊区的5位共产党员,我们正式提出申请,请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为祖国多做贡献,当我们知道黑龙江的北部有十几亿亩的大荒原闲着睡大觉,我们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北大荒去,让那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全都翻过来,不许长草,只准长粮食。我们不愿过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悠闲的生活,我们愿做一名拓荒者。
申请人:杨华、庞淑英、李秉衡、李连成、张生
老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因为这封志愿书改变了他和许多人的一生。
杨华的队友、2009年已经75岁的王进明老人记得,看见报上登的志愿书,他想也没想就报了名。凭借的是改天换地的万丈豪情,至于究竟要做什么,要去哪里,那是在入选垦荒队以后的培训课上才了解到一二。
当时,北京团市委已经在众多报名者当中选拔出了67名青年,包括男队员48人,女队员19人,其中,党员11名,团员42名,组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由于对东北的环境和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团中央特地在出发前给大伙集中培训了三天。
第一堂培训课先由团中央的老师介绍当地的情况。“老师说当地很冷,到处都是草原和树林,有狼群野兽出没,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地,条件很艰苦。”王进明这才从老师嘴里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萝北县。
老师没有危言耸听,萝北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毗邻俄罗斯,是黑龙江省五大荒地之一。全县75万公顷土地,却只有16000人。当地有句俗语:六十里地是邻居,三十里地是南北炕。这句话形象而生动,足以在人们眼前形成一片人烟稀少,地域荒凉的荒原。所以,人们惯常称之为“北大荒”。
但是,那里以小兴安岭为天然屏障,气候温和,有霜期短,土质肥沃,适合种植春小麦、大豆和玉米等作物。人们常用“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来形容那里的富饶。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等着热血青年们的到来。
王进明他们人在课堂上,心却早就飞到那里了。终于盼到了出发的日子,1955年8月30日。
为了帮助垦荒队实现“不要国家一个钱为国家作贡献”的口号,团市委在全市青年中掀起了捐钱捐物活动。短短十余天,全市青年就捐助69698.4元。团市委用这笔钱为垦荒队在当地准备了35匹牲口、10副新式农具、2辆大车、3000亩耕地的种子,以及全体队员一年的口粮。
考虑到东北天气寒冷,条件较差,临行前,又特地为每人购置了一件老羊皮袄。
出发那天,北京各界青年1500余人及队员们的亲属在前门火车站为垦荒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
火车开动了,前方是建设一座“北京庄”的理想,身后却是抹不掉的牵挂。
杨华的老父亲年迈有病,哥哥在首钢当工人长年不在家,妹妹尚未成年,妻子还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
庞淑英父亲早亡,姐姐嫁到了河南,北京的家中只有一个刚成家的哥哥。参加垦荒队的事她只和兄嫂通了气,母亲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但是,车厢里的垦荒队员们深信,有一个地方更需要他们,他们的青春热血将与共和国的富强连在一起。即便多年以后,这样的情怀仍然支撑着他们在那里贡献着余生。

垦荒队举行“开荒第一犁”仪式,萝北县委书记阮永胜为仪式剪彩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到了萝北县城,目的地却还没到。
垦荒队员们要去开荒点,距离县城还有30多里路,坐汽车还要1个多小时。载着垦荒队员的汽车行驶在起伏的“路”面上。
从县城到开荒地点本来没有路。为了迎接北京来的志愿者,萝北县团委特意组织青年团员们,愣是用镰刀割出了这样一条草路。沿途必须经过一条河,萝北青年便在河上搭起了两座木头桥,汽车过桥时,嘎吱嘎吱直响,车上的队员们听得个个提心吊胆。
垦荒驻地终于到了,它设在一片桦树林里。说是营地,迎接队员们的,其实就是一根棍子上绑着一面红旗,以及当地青年支援的干草和木头,一捆一捆地堆在木杆旁边。这就是开荒者所能拥有的生活和生产物资。
驻地四周没有一户人家。周围全部是交错在一起的树林和草甸子。树是抗寒的桦树,大腿粗细;草是大小叶樟,齐人胸高。漫山遍野的绿色,不时传来阵阵兽鸣鸟叫。再往远处,北面是小兴安岭支脉凤鸣山,鸭蛋河从山下蜿蜒而过。西边的嘟噜河,是黑龙江的一条支流,河上搭起的那两座简易木桥,日后还将成为队员们往来县城的必经之路。
一切要靠他们自己了。队员们竖起垦荒大旗,清杂草,砍树枝,在刚刚清理出的平地上支起了鹤岗矿工赠送的大棉帐篷。女队员用木头支床,男队员用小树枝铺地,垫上茅草当被窝。
由于纬度高,北大荒一带天黑得特别早。才下午4点多,太阳就落山了。
这是队员们在荒原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帐篷里的马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
虽然只是初秋,但荒原里的夜风依然刺骨。尽管舟车劳顿,疲惫不堪,但所有人在那个晚上都失眠了。
远处的阵阵狼嗥终于消失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亮了。
9月4日,正式开荒。动工之前,有一个仪式,简单而又隆重。垦荒队书记陈启彬和队长杨华带领大伙排好队,站得笔直。他们面对茫茫荒野,庄严宣誓。“我们宣誓:第一坚持到底,不作逃兵,要把边疆作家乡。第二,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成乐园。第三,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决不玷污垦荒队的旗帜。第四,完成计划,争取丰收,为后来的青年们开辟道路。”
宣誓完毕,全体队员在那张写有誓词的红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杨华从萝北县委书记阮永胜手中接过火把点燃第一把火,又传给陈启彬书记点燃第二把火,就这样接力式传下去,最后一名队员接过火把,走向荒地点燃了面前的干草堆,火苗一蹿而起,很快映红了北大荒的天空。
在火光的照耀下,队员们在烧过的地方摆好了4副开荒犁,杨华、陈启彬、庞淑英、李秉衡各扶一副犁杖,对头前拉犁的牲口喊出了第一声吆喝……
两三年以后,被划为右派的诗人艾青也来到北大荒。他用笔真实地记录下人们烧荒的激情:“好大的火啊,荒原成了火海……野火烧不尽,禾苗起不来!快磨亮我们的犁刀,犁开一个新的时代!”
荒原飘起了第一支青年垦荒队的旗帜。

老垦荒队员杨满、王进明、荆焕峰(从左至右)
一片又一片焚烧过的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翻出了丰腴的黑色肌肤。
在一次次地跌倒爬起后,这些城里来的姑娘小伙竟也成了扶犁开荒驾车伐木砍柴打草的行家里手,他们在艰苦的劳作中享受着改变大自然的乐趣。但大自然自有它的手段。
开拓者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们遇到一种当地人俗称“小咬”的小昆虫,“小咬”会追着人猛咬,被它们咬过的皮肤会很快泛起红色的疹子,痒得难受。而到了中午,成群的瞎虻又接着骚扰大伙儿,直到傍晚。晚上迎接垦荒队员的,则是数不清的蚊子,连续轰炸到第二天早晨。周而复始,大伙这样调侃说:“一天三遍咬,蚊子瞎虻和小咬。”
女队员想了个辙,用布蒙住头,只在眼睛、鼻孔、嘴巴处挖几个洞。男队员则自己发明了防蚊虫“面罩”。“早上起来,先洗完脸,然后拿泥巴把脸、脖子、手臂都涂严实了,不然一天都得和蚊虫作斗争了。”王进明老人回忆说。
进入10月份,天气很快转凉了。每天只有中午太阳高挂的时候还有一点暖和气。为了加快速度,赶在土地上冻前多开垦一些土地,开荒由原来的四副犁增加到了九副犁,县里又给送来一些马匹。每副犁八匹马排成分列式,犁过之处用不了多久就结了一层薄冰。一天活干完,浑身上下都是泥巴,鞋子也湿得直滴水。但晚上睡觉时,谁也不敢脱鞋,脱了第二天鞋子就冻得和冰坨一样,根本没法穿。很多队员手脚指甲都冻坏了,队员周俊的鞋和脚冻在一块,脱不下鞋就去烤火,烤化了一脱,十个脚指甲盖全掉了。
进入11月份,土地已经上冻,这时,吃饭开始成了问题。
因为天冷,一锅水架上干柴,一连3个小时也烧不开。蒸窝头时,下面一屉已经熟了,上面一屉却冻成了冰。
每天除了早饭能吃上热的窝头,另外两顿就只能把窝头揣怀里,边干活边焐着,用身体的热量保持一点点热气。但杯水车薪,窝头总是冻成冰疙瘩。说是窝头,其实就是一个大面坨,每个都有1斤半左右,中间捏出个比牛眼还大的窟窿眼,蒸好后塞上咸菜。男队员一天三个,女队员一天两个。
“刚开始都不会做饭,窝头捏得太扎实,根本蒸不熟,拿着砸墙都不碎。”杨华说。后来只好请来县里的张大婶手把手教队员们做饭。吃饭的时候,一口雪水,一口窝头,艰难下咽。没有热菜,只剩下冻萝卜,用刀根本切不动,只能用斧子砍。砍下几块放些盐,用水煮煮就着窝头吃。
这样的苦日子后来被总结成了顺口溜: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
除了冷,还有狼。垦荒队到达后的第二天夜里,大伙正挤在帐篷里有说有笑,突然一名女队员一声尖叫!大家一看,两个窗户外都整整齐齐地趴着几只狼,绿莹莹的眼睛直盯着众人。紧接着,就听到帐篷一角被狼撕咬的声音。
队员杜启发和孙敬贤各抄起团中央发的两支“三八大盖”,两波子弹分别朝两个窗口打去。狼被枪声吓跑了,撕咬帐篷的声音也没有了。但外面马号的马群被野狼刺耳的叫声吓惊了,一个个高昂着头,跃起前蹄,奋力嘶鸣。
杨华指挥着队员们在帐篷四周点上火堆,以保护大家的安全。狼群近了就打一阵枪,直到天亮狼群才撤走。第二天夜里,狼群又来骚扰营地,比第一天来的还多,叫得更凶,杨华带着几个队员端着枪,在帐篷外站了一夜岗。打那以后,大伙都多了个心眼,会把枪和子弹放在明处,睡觉前都仔细检查门窗。
多年以后再回忆起当年的艰苦,杨华老人说,最可怕的不是残酷的环境,不是凶残的狼群,而是人心不稳。垦荒队到达北大荒才1个半月,队伍里就出现了“逃兵”。
10月中旬是荒原上最好的伐木季节。垦荒队派出先遣组套上六挂马车进山伐木。就在先遣组离开的那个晚上,呼啸的北风不期而至,整整刮了一夜,气温骤降达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大雪把帐篷门都堵住了。
当队长杨华赶到伐木地点时,听到了意外的争吵。
“我要走,回北京,谁也别拦着。”这两句话杨华记得很清楚,因为字字都像大铁锤,砸在他的心上。
说话人正是先遣小组组长,他的耳朵、脸都冻起了泡。看到杨华出现,小组长大概有点尴尬,蹲在地上不说话。
回到营地,队友们轮流做工作。但无论怎么劝说,这名同志死活不愿意留下,收拾好包袱,当天就回到县城,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是垦荒队中第一个离开“北大荒”的队员。
垦荒队出了“逃兵”,所有垦荒队队员们既难过又不安。夜里开会讨论时,杨华咬破手指在一块木板上写下鲜红刺眼的八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并把这块木板树立在营地门口。这8个字正是离开北京时胡耀邦同志送给他们的。
多年后谈起这件事,杨华只说了一句:“当初组建垦荒队时第一要求自愿,吃不了这份儿苦,绝不强留。”
祸不单行。1956年3月,第二批垦荒队员到来时,一直为垦荒队作支援服务的萝北县农民秦大哥为了制止两个毛躁的新队员打鱼,不慎踏入漂筏甸子(沼泽地)。大伙悲痛地把秦大哥的遗物安葬好。墓碑前,书记陈启彬沉痛地对杨华和庞淑英说:“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牺牲,一定要照顾好同志们。”
但他的愿望却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碎。195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第二批队员中的麻友和六个队友去山下割草。天空中的云层很低,突然一个闪电,紧接着几个炸雷,像连珠炮一样在地面上炸响。
队员们都被震倒了,好一阵子才站起身来,唯独麻友没起来。队员们扑了过去,抚去他脸上的头发,呼喊着他的名字,却再也没有唤醒这个活泼的小伙子。麻友是最小的垦荒队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小秀才”。他会吹口琴;会把他们的经历编成有趣的快板书;会在晚上为大家阅读报纸和书籍;也会躲在帐篷外学鸡招呼大伙起床。
闻讯而来的队员们哭成了一团,几个队友流着泪帮麻友换好衣服,把他平时喜欢的口琴装进上衣口袋里,还有一支金星钢笔别在胸前。
麻友是垦荒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牺牲的北京队员,队友们将他安葬在通往凤祥镇的路边,不远就能看到垦荒队的宿营地,远眺是蜿蜒流淌的嘟噜河和荒草丛生的平原。
“每到他的祭日,大伙都会去坟上祭奠,坟头总是干干净净,没有一颗杂草。”王进明说。1985年,杨华带着大伙将牺牲同志的墓迁入现“北京庄”的后山山坡上,麻友的墓里只剩下了当年他用过的口琴、漱口杯和金星钢笔。杨满在麻友生平中写下四个字:“永垂不朽”。
从1956年开始到1962年,整个萝北垦区有7名来自不同地区的男垦荒队员病逝或牺牲,他们有的没来得及恋爱或结婚生子就离开了人世,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他们热爱的北大荒。这都是后话。
“小秀才”麻友牺牲后,整个队伍开始蒙上了一股悲观的色彩,再加上繁重的工作,乏味的生活,所有的压力压在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身上,反复拉扯着他们紧绷的情绪,任何一个小小的刺激都有可能让人崩溃。
“我们到底来干什么,为了什么。所有人都开始反复地问自己。”王进明回忆。晚上讨论时,总有人会说起北京的种种优越,然后就有人开始叹气,抽泣。一个人哭,两三个人哭,最后整个队伍都哭了。虽然第二天仍然坚持劳动,但压抑的气氛始终盘踞。
开荒的岁月一点点流过,留下的是一片片新开垦的土地。从1955年9月初到11月初土地上冻,第一批垦荒队员一共开垦了1200亩地。第二年3月,随着第二批垦荒队员的到来,垦荒的速度得到了提升。到1956年5月初开始播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4200亩。
“绝大部分种的大豆和萝卜,一小部分是玉米。因为东北气候适合大豆生长,当时的老玉米都是外来种,不太适应环境。”第二批垦荒队员之一的杨满清晰地记得。
播种用的是专门的马拉播种犁,4匹马拉,一个人负责前面赶马,一个人中间把着操纵杆控制方向,还有一个人在后面跟着检查播种情况。
“黑土地几乎不需要太多打理,庄稼噌噌地往上长。大伙都忙着开垦新的土地。”杨满老人回忆说。
麻友牺牲后的那年秋天,他的队友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丰收。
地里的玉米和大豆一层压着一层,密密麻麻。“望着这么多粮食,大伙都非常振奋,觉得一年多的苦没有白吃。杨华他们年纪大,在地里干过。我们这些年轻的没见过,觉得很新鲜,没事就在地里数粮食,可怎么也数不清。”杨满说。
丰收的喜悦让大伙开始鼓足干劲,抓紧时间赶在天气变凉之前把粮食收入粮仓。每天凌晨4点多天刚亮,队员们就扛着镰刀、赶着马车去下地收粮食,一直忙到太阳下山,光收割粮食就花了1个多月时间。
玉米数量不多,手掰也比较轻松,收大豆则是一项苦差事。大豆秆都是1.1米左右,必须先用镰刀割倒,放在地里晒干后,再统一装车运到专门的场地压豆。一亩地连秆带豆六七百斤,全靠人力收割,一天下来,腰都伸不直了。
当时,垦荒队一共有15辆车,平均一台拉3000斤,光运粮食就用了半个多月。拉到加工点,玉米装好,萝卜放进早就挖好的地窖,大豆秆则堆成了一个一百多米长、五六米宽、四五米高的小城墙。等土地开始上冻,就用水泼地面结冰,在冰面上铺好1米多厚的大豆秆,用石磙子把大豆从豆荚中压出来。“白天一拨人,晚上一拨人,24小时连着干。”杨满说。
豆秆能当柴火烧,豆皮还可以喂牲口,一举三得。装大豆的麻袋都不记得用了多少个。幸好,队长杨华的记事本上完整保留了当年的数据:1956年秋,大豆约20万斤,萝卜30万斤。此外,队员们还盖了57间住房和一个容纳300多人的饭厅,饲养100匹马。当年上交国家粮食74000斤, 收入15600元。
1957年秋,开地600公顷,养新疆细毛羊40只,猪40头,黄牛40头,盖房子1460平方米……
1957年,杨华的妻子梁淑凤来到了驻地,她积极给大家牵线搭桥,团中央也很“体贴”地拨来了女队员——北京的垦荒队员们迎来了哈尔滨亚麻厂女工30名,“北京十大建筑女工”4名。
这年冬天,九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杨满的爱人就是同一批到来的垦荒队员徐春华,同样是第二批队员的荆焕峰也娶了一位山东省来的支边女青年。紧接着,名叫“垦荒”的小队员出生了。昔日的荒原上终于听到了“鸡叫、狗咬、孩子哭”。

曾经的“北大荒”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
从1955年9月进入北大荒之后,垦荒队内一直都很团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1957年为了商讨北京庄搬迁的问题,队里第一次出现了分歧,这在垦荒队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围绕的核心问题是,该留在最初的驻地,还是搬走另起炉灶。
当时,队员们已经离开了原先的驻地,搬到了萝北县镇西26里的北山上。这里背靠小兴安岭余脉,避风御寒,山下就是肥沃的土地,适宜耕种。这里最初也是荒原,只有一根木杆,上面竖着一个写有阿拉伯数字“34”的牌子,作为这片地域的界标和名称。
垦荒队用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将所有的荒草和树林清理干净,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建起了一排宿舍,马厩,操场,还有青年之家。按照萝北县政府的统一规定,这里成了一座农庄,定名“北京青年集体农庄”,简称“北京庄”。
随着队友的陆续入住,位于“34号桩”的北京庄逐渐暴露出了致命的缺点:水源不好。此地所处的北山是一座岩石山,没有现成的水源,必须打深井取水。打上的水发浑,味道发涩。雨季来临后,由于雨水无法下渗,积水成灾,形成山洪冲毁作物。
面对这种情况,杨华等人经过反复考虑协商,不得不作出决定,另辟新址。
这一次,杨华所面临的阻力是他记忆中最大的一次。“大伙们都挺支持我,做决定很少听到反对声音。但这一次开会商讨,第一次有人直接提出了反对。”杨华说。
“我同意王进明的决定,换地方。咱们既然能够建起这么好的家,就一定能再建一个更好的。”
在第一天的队内讨论中,副队长庞淑英第一个站起来表达意见。她的话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但也有一些人激烈反对,表示应该继续在这里扎根。
大伙并不是看不到利弊,但“34号桩”从第一天开始就完全是垦荒队用手一点点建起,突然说要放弃,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好比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拉扯大,突然说不要了,大伙都没法接受。”队员荆焕峰回忆。
接连两天,队里不停地争论,留与不留分成了两派,各抒己见。最后,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才勉强同意换址。
第三次选址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大伙一致决定,将驻地建在北山南边、离萝北县城西北7公里的白云石山下,庄前是凤鸣河,后面是鸭蛋河,依山傍水,土质肥沃。
这个庄址一直沿用了半个世纪,就是现在的“北京庄”——萝北县共青农场7队。
这个庄子里一共住了3批队员。头一批就是1955年9月到达萝北县的杨华等人;第二批是1956年5月22日到达的,137人;第三批是1956年11月初来的,32人。加起来一共236人。
后来,32名队员因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不同,集体迁回或调出。到1958年11月共青农场和萝北县合并时为止,坚持下来的北京青年垦荒队员尚有185名,只有个别队员请假不归或私自外流。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之后,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和哈尔滨市的垦荒队员也纷纷来到萝北,最后一共来了2600多人。他们先后建起了8个以自己城市命名的农庄,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青年集体农庄,号称“萝北八大庄”。
第一代拓荒者撒下的星星之火,不久便形成了燎原之势。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军垦移民。从1958年3月到5月,复员转业到北大荒的部队官兵多达8万人,包括7个建制预备师,4个部队医院,其中排以上军官6万多人,加上部队非军籍人员和家属,一共有10万人,号称10万转业官兵。
就在这年4月,垦荒青年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第1师、第7师、信阳步校部分转业官兵和家属5000多人。复转军人们带来了大量机械化工具。以杨华他们开垦的数千亩土地为基础,新垦耕地的面积呈几何级数地扩展开去,绿色的麦垄向着天际不断延伸。后来的拓荒者在“八大庄”的基础上扩建了农场,取了一个响亮又贴切的名字:“青年农场”。
又过了10年,54万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的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他们踏着前辈留下的足迹,改天换地的豪情一如当年……
如今,当年意气风发的姑娘小伙都已年逾古稀。
几乎所有老人的子女都非常不理解父母当年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来到这片荒原,扎根一辈子。
“我的母亲在扫盲班夜校念的书,文化程度不高。每次问她为什么留在这,她总是回答不出来。她只告诉我们,多开垦几块地,多产几亩粮食,就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庞淑英的大女儿张丽云回忆。
副队长庞淑英不是没有机会回北京。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考虑农场靠近中苏边境,团组织曾经出面找过杨华和庞淑英等人,询问是否把垦荒队先撤回北京看看情况再说。杨华等人和队员们商量了一阵,毅然决定,留下来。
上世纪70年代末,庞淑英身患重病,不得不回北京治疗。她原先工作的大队领导也找过她,询问她是否愿意调回北京工作,她当场就谢绝了。无论怎么劝说都不听,病刚好就收拾包袱返回了农场。
直到现在,仍然留在共青农场的还有8位老人。由于是志愿前往,一直到退休,他们都只享受1968年知青的待遇,但没有一个人为此抱怨过。
1992年,杨华从副场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1995年,退休后的杨华回到了北京生活,在老家石景山安度晚年。当年的5位发起人中,李秉衡、李连成、张生早已辞世。庞淑英则于2009年2月底离开了人世。庞淑英的二女儿张丽莉为纪念母亲写了一个十二万字的剧本,名字叫《挺进荒原》。
在张丽云的回忆中,身患脑干萎缩的庞淑英在弥留之际已经不记得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提到1955年的垦荒,她仍然能够清晰地回答:“我们到的是萝北县,家住北京庄。”
侯亮平唱了三次的《智斗》背后有哪些真实历史:胡传魁、阿庆嫂有没有原型?刁德一到底姓蒋还是姓汪?
《人民的名义》开播以来,侯亮平唱了三次《沙家浜·智斗》,阿庆嫂到底怎么不寻常?刁德一到底姓蒋还是姓汪?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点击图片,查看所有往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