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鲁 回声系列 2022 布面丙烯 240 x 320 cm 2022
本文图片,由艺术家和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提供,此致谢意。
本文是一篇关于马可鲁个展《回声》的展后评。展览于2024.11.16-12.16在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展出,现已闭幕。
马可鲁的展览标题,《回声》,也是一系列画作的题目,“声”之名,在绘画里意味着某种否定:据了解,它回应着一段历史的不可言说性,只是绘画又是视觉的,所以如同涂成单色的覆盖隐迹一样,“声”字,也意味不可见者。大历史过后的残心情念,隐迹者的高来高去、不落实处,若非情到至沉郁的地方不堪说,便是性格清净空疏、一时佞禅、旋而又逃禅。是这样的。
但另一方面,我怎么可能说服自己相信,一幅抽象画的主旨,是对具体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回应。大部分时候,一幅画虽然只是区区一幅画,但它站的位又总比具体的历史要高一些。一件所谓的观念绘画,要讲求语境关系大于作品的形式本体;但一件趋向完善/纯粹的抽象画,则讲求绘画系统所确定的封闭自律性,透过视觉的直观感受,诉说着超历史的普世;可这或许也是一种偏见,因为另一方面,艺术家此时此地的“普世”三观,以及自觉被这种“观”所塑造的审美情致,无疑又二度指向大历史。最终,它们可能还是一种同构。
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说话就是,红墙的颜色本就是一种象征,它通过层层叠加,覆盖了底层的厚重、朴素的灰色基底,只留一系列凹凸笔触,在细看下是不可抹去的留痕;而总体上,这又是处在一种高度超然
(或故作冷静)
的调性下。这种“通俗”,过于看图说话;但不可否认,我们从视觉直观中体认的感受,与之颇有相似——尤其是稍稍了解那故事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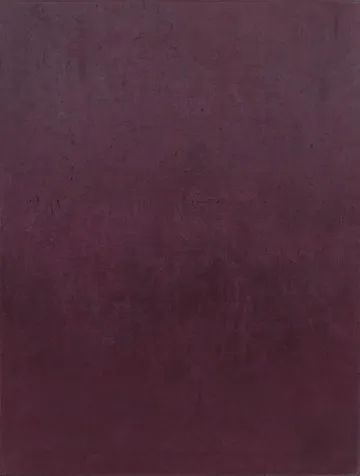
马可鲁 Ma Kelu 《红》( 2.1 )系列《Red》( 2.1 )series 1989-1992 布面油画 Oill on canvas 172.5x131.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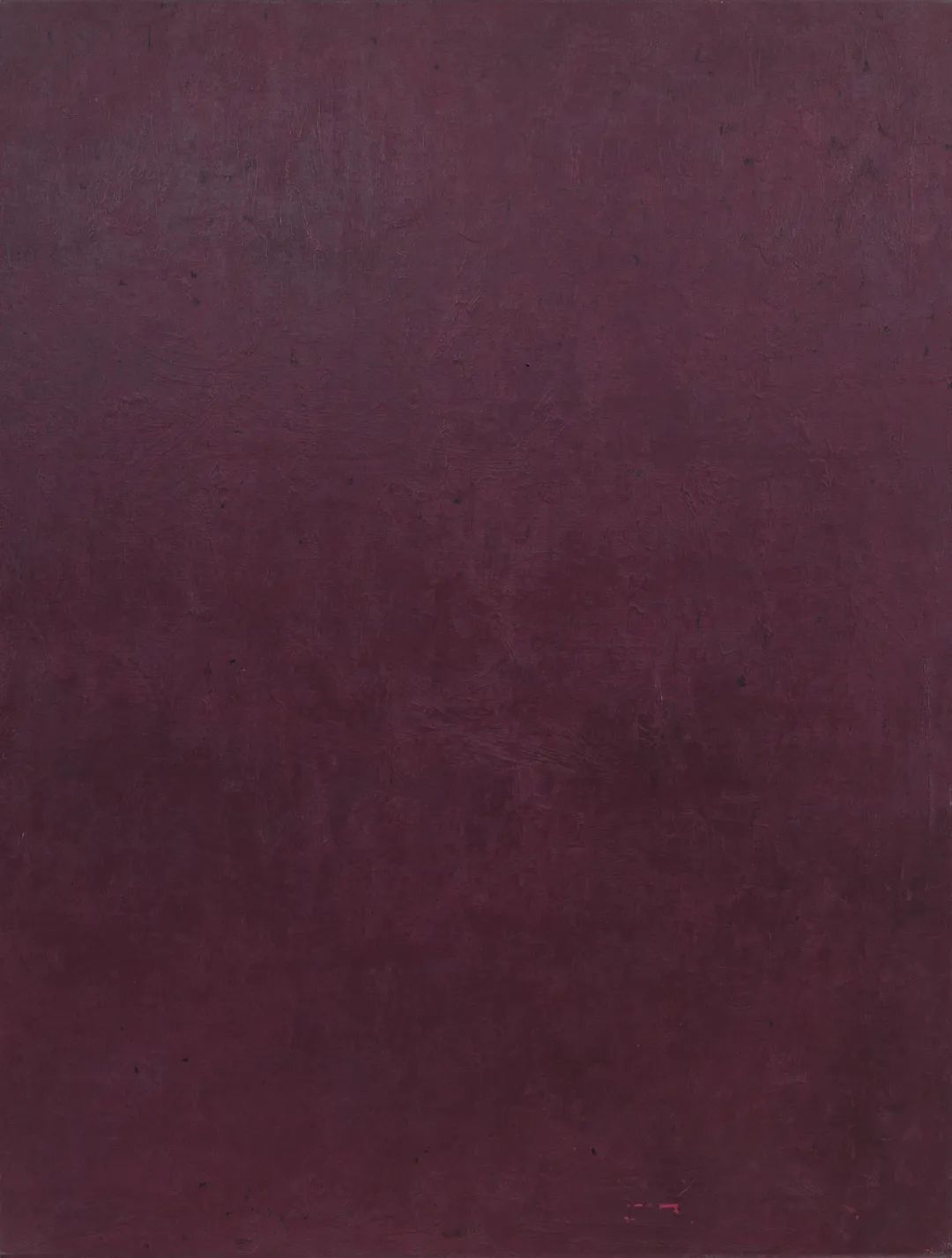 马可鲁 Ma Kelu 《红》( 3.1 )系列《Red》( 3.1 )series 1989-1992 布面油画 Oill on canvas 172.5x131.5cm
马可鲁 Ma Kelu 《红》( 3.1 )系列《Red》( 3.1 )series 1989-1992 布面油画 Oill on canvas 172.5x131.5cm
《红》系列x3 现场图
细读马可鲁的绘画,我们不免要再拾起三个老话题的:第一个是,他的抽象画与禅的关系;第二个,抽象画与所谓绘画本体论的关系;第三个,他的抽象画与“书写性”的关系。这三个话题其实是连贯的,完全可以看作一个话题的几个方面。
于是,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或许可以围绕几个更具体的问题来讨论:
1,禅式的淘空,和历史情思的隐心之迹的淘空,两者在画面的生成中,如何可能构成一个连贯性的脉络?
2,绘画本体论式的画面“做减法/破题”,和禅式思维的“减法/破题”,融到一个画面里的时候,它们在哪些地方是汇合的,在哪些地方是分离的?
3,从当下年轻人的角度,回看老一代人,在持有对“绘画本身”的建构式信念底下,做“减法”/解构意识的时候,他们是怎样一种差异的时代性格下的状态?
4,和“做减法”的终点,紧密相连的,绘画中的“书写性”,在什么程度上,其实仍脱离不了制作性的基础?以及作为一种西化杂交的“书写”,它和我们现今更时髦的“临时性”之说之间,有何相似和相异?
这几个提问也不完全像是提问,倒像是本就含着某些立论。

马可鲁
得大篇 之一 Enlightment of the Tao No.1 布面油画 120x90cm 1985年

马可鲁
回声系列 2024 Echo Series 2024 布面丙烯Acrylic on canvas 300x240cm 2024
也许从马可鲁本人的角度来看,《啊打》系列比《回声》系列更适合作为展览的主角。《啊打》是个达达式的无意义名词,但它和达达式的虚无感没关系
(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
,用艺术家周围人说多了、不想再提的说法,它是禅式的消解。
和抽象绘画发生最直接联系的禅,出自一种和西化交织的杂糅语境:从日本辗转过去的美国禅,依托于文艺“系统性”自身的反身性,捻出了消解行为的仪式性。如果说,戒定本是为了解脱的目的,那么公案/仪式,便成了对解脱那一刹的反复表演,来反映一种美学品味。它也不是时时常拂扫的修持,只是把一次性的倒空仪式,在重复。
这是马可鲁的抽象画发生谱系源点的背景语境之一。在经过那年头之后,游学到大洋彼岸,反思文化原乡时,实际已是杂交的原乡。在这里,两个“空”糅合成一个:一个是心灵的,一个是绘画语言本体的。也就是,绘画语言本体的“空”,意味着对“极简”的另一种诠释:依据绘画话语系统的形式终点,和放任“物”自身的超然之审美智趣,合而为一。
但是,马可鲁的”简”,或者说绘画“做减法”,和通俗直观上的“极简”,又并不总是相同。有时,一些“减法”,在绘画实践的局外人看来,已然是系统建构的产物,或者说,基于娴熟手法基础上的四两拨千金。而马可鲁基于绘画形式本体的破格,在早已对绘画性没有传统式的执着情节的年轻人那里,又更像是绘画传统系统基础上的二次建构。
或者换一种说法,那一代人绘画话语中的“空”,和现在年轻艺术从业者眼里的“空”,是有认知差异的。心灵类型有着时代背景,艺术作为一种修持拂扫,所对抗的是什么,作品中的“空”,就不一样。一方面,源于匮乏无法填补的人,无法体味源于伤痕需要弥合之人的“空”境。另一方面,绘画性的传统标准,究竟是做艺术的一根临时拐杖,还是被几乎等同于艺术本身,得出的取径通路,即使半路或有相合时,但终途却是抵牾的。

马可鲁
回声系列 2022 布面丙烯 320 x 240 cm 2022

马可鲁 啊打 Ada 纸本油画 86x66cm(画芯),109x88cm(含框) 2021

马可鲁
啊打 Ada 纸本油画 86x66cm(画芯),109x88cm(含框) 2021-2022
在具体的画面上,马可鲁的作品,有几种最典型的“简”:
书写性的墨色笔触
(或者确切的说,是基于经历书法的绘画性转向后的书写观之上)
,在行布章法之间互相做着节奏呼吸,并与素色的基底对话。
经过多次制作性叠加,保留大量痕迹的满幅单色,在一些作为视觉重点的亮色行笔、皲裂漏底,诸如此般的,发生互动。
单色在绘画过程中反复运笔叠加,最后成为了满幅单色,最后,除了色域之外,看点集中在了细看的笔触肌理,而这些笔触肌理,是顺势于底层凹凸,不断地互动,时而对先前进行消解,时而对先前进行就势自然的增益。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但都有是在上述几种的连续性样式矩阵变化中。
在其画作的具体施行中,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以实际的制作性为基础的反制作性观念,或者说,受反制作性意识渗透了的制作。而这种反制作性,优先体现在
不经意
和
顺应材料
上。
不经意间,听马可鲁说了句老话,“呼吸,透气,表现光。”来自他的风景写生。另一个偶尔听到的信息,是他年轻时候,有幸得到一本《印象画派史》,大部分插图都是黑白的,他如获至宝,不停临摹——这可能是触发他绘画中后来喜欢用素色(接近黑白灰的颜色,或最简化的纯色对比关系)的生平契机,当然,颜色的文化传统习性,也就是认为素色是更正、更有份量的颜色,这一点或许是更深近根本的原因。
简也好,素也好,刻意安排的自然而然感,属于一种顺应材料本身的绘画理念。顺应材料的观念,可以是格林伯格式的材料形式本体论,可以是物派禅式“物本身”,也可以是类似海德格尔“上手之物”式的中国趣味。
上手性是简、是纯粹性的一种写法,但不仅仅是形式语法提炼,也是对“不经意”的趣味性。
马可鲁这里的“不经意”,不是像行动绘画、抽象表现主义那样,先不经意地挥洒、再靠无意图指向的霸气来收拾画面;而是小心翼翼地在为“不经意”做安排。
墨色就势画出了画框龙骨压出来的痕迹。哑光和皲裂。瘦肥交错产生的浅浅裂痕。半干不干时被推开的画层,破了皮、漏了底。薄涂黑底,就着布纹出现的画痕,但偏又有入画的经营性。和布色接近
(从画侧面可看出布色)
的米色,用大笔刷强覆盖地画在黑底上,产生一种留白的错觉;另一些时候,可能真是用负形把基底压出来一个像画上去的形;这两者互相呼应。
显然,这里面的种种痕迹,不仅仅是绘画性,也是掺杂了制作性的过程痕迹。痕迹总让人联想到不经意流露的气韵,因而和马可鲁作品的另一特点,“书写性”,连为一体,替后者作背景,两者浑然一体。

马可鲁
香山樱桃沟 Cherry Valley of Fragrant Hills 纸上油画 1974 26x19.3cm

马可鲁
夕阳倒影 Sunset reflection 纸上油画 1976 24.5x18.5cm

马可鲁
秋 Autumn 布面油画 76×76cm 1991

马可鲁
无题 布面油画 183x208cm 2013

马可鲁
啊打 Ada- 2018 画布油画 200x200cm 2018

马可
鲁 啊打 Ada 2018 200x200cm 布面油画 2018
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绘画中的“书写性”,是井上有一之后的书写性——也就是书法变得绘画化了的“书写性”。那么,这样的“书写性”,意味着什么呢?
“书写性”:一次性“书写”;画面结构明显地分为小局部结体和大整体章法两个层次;结体是线的节奏;总的来说,是直给的、横向的平面关系,在规定性的经验范式基础上修正,获得一种部分是临时生成的势动结构。
在《啊打》系列里,可以看到,明显含有平移自书法章法排布的画面构成意识。当然这章法却也不仅仅是一种对书法章法的模仿,它同时也是类似Twombly的、有着稍许偏移的等距平均化排布,一种平面化的风格意志,避免空间深度错觉的典型画面布局。在这种意义上,“章法”的形式意志,和绘画“减法”的形式意志,在一个终点汇流。
但就如前面所述,马可鲁画作中的平面关系,是受纵向的绘画层级步骤所影响的,相应的,他的“书写性”中,有时也有着制作的成分。看似一笔一刷的率性效果,是需要大量铺垫的。
而如上述所述这样的“书写性”,或许也可以视为,老一辈人,对现下流行的“临时绘画”理念的回应。两者都是对绘画形式的极限本体的一种理解
(在极简主义,实在绘画的同一条脉络上)
。经典的极简主义,是学科本位意识,所赋予的一种绘画本体论精神,自我要求着一种作为“本质”性的“纯粹”;而“书写性”对“最小限度的绘画”的理解,受到中国传统化的影响,笔墨的四两拨千斤,实是通过语法的纯化,来达到表达的以简御繁,获得一种好理解的清晰和力度;“临时绘画”则是最彻底的生成-反设计的,一时一刻随机碰出来的暂时性画面平衡,被视为绘画性中的“最小限度”。

马可鲁 回声系列 2022 320 x 240 cm 布面丙烯 2022

马可鲁
啊打 Ada 53x53cm 布面油画 2023

马可鲁
无题01 Untitled No.1 66.5x90cm 宣纸水墨 ink on rice paper 1988

马可鲁
无题02 Untitled No.2 66.5x90cm 宣纸水墨 ink on rice paper 1988

马可鲁
无题 Untitled 200x270cm 布面油画 2015
这个时候,笔者会想起一个词,那是笔者在马可鲁面前,形象笔者自己的状态的。马老师很喜欢这个词:半吊子。现在,笔者把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来形容,他在追求绘画纯粹性的路上,所不愿意割舍的复杂性。对纯化、绘画的本质性有情节,而这本质性则又和绘画学科的自律系统性有关;对传统有情节;对绘画以外的文化身份有情节;对现实历史的关怀有情节。当这些都汇为一体,形成一个看似同一性的同构表达的时候,他的绘画完成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特色的复杂性执着=“半吊子”性,也完成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所有抽象画都是有潜在模仿物的,只不过,它所模仿的,是一种结构:或是一种心态的结构,或是一种情感运动的节奏,等等,被用黑白灰、虚实、冷暖等一系列最基础的绘画因素,搭建出了复杂的形态同构体。正如看图说话式的具象画不是真绘画一样,在绘画中,同样也没有全无潜在故事性的纯抽象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