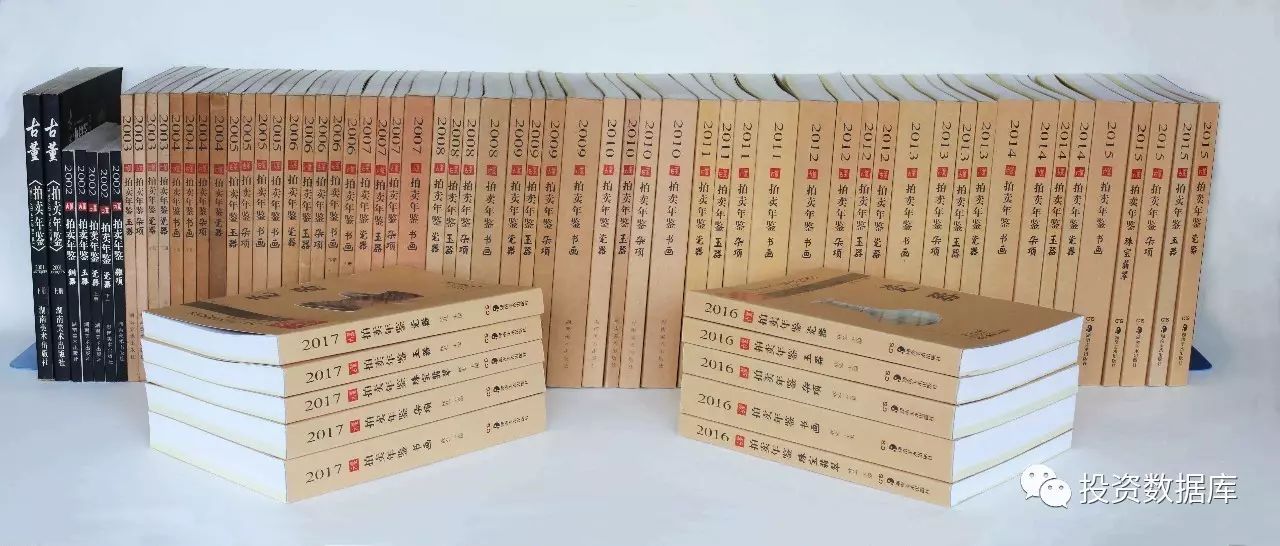莫砺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专注于唐宋文学研究,著述等身。作者与莫砺锋共事近四十年,尽管有同事之谊,却一直以为莫先生是位“书斋式”的学者,难以亲近。但在阅读《浮生琐忆》回忆录的过程中,作者逐渐发现莫砺锋的温文尔雅、沉默寡言背后辛酸的成长经历,遭受的不公命运以及在厄运面前坚韧不屈的伟大人格。时代大变动中的共同遭遇,让作者感到与莫砺锋的心贴近了许多,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也不再陌生,成为了作者心灵的挚友。
📖
悲见生涯百忧集
——莫砺锋《浮生琐忆》
读札
文 | 丁帆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5年第1期
在每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中,往往会忽略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使之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几十年的同事,第一次听到莫砺锋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猜想,他一定出生在诗书世家,父辈给他起名字是鼓励他成为一座学界的高峰。所以,在我一九九二年开始使用的电脑里,就错把他的名字写成了“莫励峰”,后来纠正过几回,但是只要打出“mlf”三个声母,“莫励峰”就跳将出来,于是,我一直就在“莫励峰”和“莫砺锋”之间犹疑徘徊。直到近年陆续在网上读到他的一些自传体散文,才猛然醒悟,“莫砺锋”才是他人生的隐喻和人格的暗示,其隐在的刚烈性格一面,往往被温文尔雅的书生气所遮蔽。
尽管我与莫砺锋有近四十年的同事之谊,但自以为与这个不苟言笑的老夫子真正结交成为挚友,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我俩的性格相差太大。他与人交往,寡言少语,礼貌有加,一丝不苟,是一个十足的好好先生,除了工作上的事情外,与一般人推心置腹地畅谈几乎是罕见的。在我过去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冬烘”式的严谨学者,一个只读圣贤书的古典学究。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我只有一次看到过他怒发冲冠的情状,那让我惊讶不已,不得其解,温文尔雅的莫兄,竟然也有如我这般俗人一样的冲动之举。莫砺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直到读了《浮生琐忆》,一切便了然也。
互联网时代到了,莫砺锋是文学院同事中一直坚持不用手机的人,直到近几年,莫砺锋突然有了手机,并用起了微信。我看到他在群里转发的帖子,便认其为同类。后来我俩相互添加了微信,交往才逐渐多了起来,其实真正能够彻夜交谈的机会仍没有出现,而每天网上新闻交互,便可见他心迹之一斑,尽管他偶尔只是用海明威式的电报体发几句话过来,我也能触摸到价值观的温度。
我不断留意他在各处的演讲文字,更加注意他的散文创作,尤其是谈及自己家世和读书生涯的文字,触发了我窥视他的灵魂的欲望。读到他那篇二〇二四年七月七日在太仓图书馆的演讲后,我知道他在二〇〇三年曾出版过一本《浮生琐忆》。但遍寻不得,莫砺锋知道后,便让学生带了一本给我。这是二〇一二年一月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再版本。此书由一百三十三篇散文组成,共计三十五万字,从他记事开始,一直写到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是他踏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的时刻,也正是我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做进修教师的时候,但是,他九月份进校时,我恰好离校,直到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南大中文系,我们的人生轨迹才开始交叉。
看到书名,首先想到的是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的名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可谓曹操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注解,而“浮生若梦”却影射出了《浮生琐忆》作者在悲苦读书生涯中人性和人文的激情慨叹。
当然,我也会联想到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陈寅恪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不注重家庭亲情所言:“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唯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莫砺锋的《浮生琐忆》虽然不是写缱绻的男女之情,但其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却跃然纸上。现代文人林语堂评价《浮生六记》认为“读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我却不以为然,那是他没有遭受过如莫砺锋这一代读书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折磨,在温柔乡里读书,才有别样的体验。设若他被投入莫砺锋那样的痛苦逆境之中,恐怕早已变成了鲁迅笔下的“狂人”了,哪来的文化自负呢?
我倒是十分赞赏书呆子文人俞平伯对《浮生六记》艺术特征的高度评价:“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以此对比《浮生琐忆》倒是有几分相似,不事雕琢乃《浮生琐忆》渗透到骨子里的文字语言的浮现,而精微之处却是刀锋插入骨髓的人文意识隐现,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当然,只有历经那个时代的人,方可意会。
作为一个与作者近距离接触的阅读者,《浮生琐忆》给我的震撼,远远超过许多优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因为它是一部非虚构的散文作品,且均为碎片化的叙事,我从这些碎片化的历史叙事中,看到了血与火的历史年轮;窥见了人性微光的烛照;看到了一个在读书的道路上不屈挣扎攀登的孤魂幽灵;更看到了那个爱憎分明、敢于抽出磨砺得锋利的刀剑的“熟悉的陌生人”抽刀断水的模样。
我是流着眼泪看完这部散文集的,尤其是他与半生遭受肉体与灵魂涂炭的父亲情感交集的描写,让我想起自己与父亲的交流史,太多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交集,让我看到了自己在书中的“倒影”,不觉从灵魂深处发出了同辈人的由衷慨叹。
假如我早早读到这本书,我会在二〇〇三年编选苏教版《高中语文》和《初中语文》教材时,建议在《浮生琐忆》中各选一篇范文,让教师和学生们知道,在语文教育中,人性教育是第一位的,只有保有人性的底色,人的成长才是健康的,才会有真善美的高尚品格——这是文学的力量与无用之用所在。
我之所以用杜少陵的《百忧集行》中的诗句来做题目,实乃莫砺锋既是唐宋诗词的研究大家,亦是一个从骨子里透着现代人文傲骨的清醒者。
《浮生琐忆》基本上是按照作者人生行迹的时序来书写的痛苦经历,而非《浮生六记》按四个门类来设计的人生快乐描写,“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均为人生快意之作,即便第三个题目似乎是痛苦的,读来却也是浪漫情事里的淡淡哀愁而已。立意不同,人文的取向也不同,这倒是应验了鲁迅对悲剧和喜剧的看法:“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同样是浮生的记叙,《浮生琐忆》的悲剧震撼力让我不能自已。
一开始,这部书的笔调是蓝色浪漫的,书中充满着童趣的描写,让人沉浸在喜剧的浪漫情境中。少年时代那些有趣的生活描写,让你讶异另外一个莫砺锋形象,即使是家庭的变故,艰苦悲凉的愁滋味,也没有磨灭一个人对顽童岁月的思恋。到了高中时代,他渐次成熟的青年内心世界,便开始与一般的青少年不一样了,那种“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前途不是为莫砺锋这样的读书种子准备的,成名成家才是他的追求。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为家庭承担起责任而发奋读书,试图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走白专道路”的勇者形象,这才是莫砺锋读书的真正动力。与于连不同,与高加林也不尽相同,莫砺锋的人生,是共和国教育史倒影中的一个特例,他的人生为这一代人充满着曲折的读书历史,画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问号。
我曾反反复复地叩问,莫砺锋是从那个极寒年代的石缝里,艰难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苗,怎么会变成一棵大树?正是读了他在太仓图书馆的演讲稿《我的曲折求学路》,才有所顿悟。演讲的开头,他讲了南朝南京城里的思想家范缜与萧子良争论因果报应之事的故事,然后说道:“范缜的意思就是说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你自己没法掌控。风往哪边吹,花瓣就往哪边飘。一朵花瓣能够说我要往这边飘,我要往那边飘吗?不能,它没有选择,是客观造成的。……我的曲折求学路,我一生命运的转变,最大的一个拐弯,就是发生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是的,命运是一个时代和体制造成的外在客观原因,它可以抑制住许多人的成长和发展契机,那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挣脱的锁链。但是,对于时时刻刻都在与命运抗争的人来说,他要死死地扼住命运的咽喉,一刻都不放松,从而降伏命运,最后实现自身的夙愿和家族的荣耀。或许,这才是个人英雄主义读书人的最高境界,是那些高喊响亮口号与大词之辈望尘莫及之处。当然,这样的读书人凤毛麟角,莫砺锋作为一颗曾经在暗隅天穹中寂寞运行的小行星,最终发出了自己明亮的光辉,这或许就是上苍给一个在苦难生活中坚持不断读书人的特殊眷顾吧。
安徽大学外语系77级七班师生合照,前排右三为莫砺锋
(出自《浮生琐忆》)
所以,我认为,除去稍纵即逝的机缘,天赋和不懈的努力,当是莫砺锋对这个世界发起的挑战,终身的韧性品格,请世界为自己的决心让路的豪情,铸就了他坚如磐石的读书心,成为我阅读此书的最大体会。
首先,《浮生琐忆》是一部非虚构的长篇自传体“成长散文”,与许多文学史上界定的散文笔法不尽相同,比如无论是写活着的人,还是逝去的人,作者一律都是采用真实的姓名,其描写的事件,毫不顾忌当事人的心理,尽量回到历史现场,尽力用白描手法去还原人物形象。当然,这并不影响作者对人物爱憎分明的判断与表达,以及对历史事件的人文价值判断。从艺术加工的角度来看,也许你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并不被作者平淡如水的叙述所吸引,然而,当你细细咀嚼时,你就会被其叙述背后的人文情怀,以及其中独立人格的魅力所吸引。以我对现代读者心理的浅陋揣测,人们希望满足的是对一个著名学者真实生活经历的窥视,以及他对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也许,这就是最纯正的非虚构作品别样的风景。
其次,《浮生琐忆》在细节描写上有其独特风格,与其他非虚构的自传体作品不同之处是,作品的细节描写在一个“情”字上下足了功夫。这部看似形散的作品,用“情”串缀成了“神不散”的珍珠项链。尤其是许多描写父子之情的段落,让我不得不在不断拭擦眼泪时,中断了阅读。共同经历过的时代和相似的命运,以及相同的人性和人文价值观,将我们的心紧紧相连。
我阅读前三分之一部分描写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篇什时心情是轻松的。比如看到其中《风筝》那篇,我立马就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一百年前写就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诗《风筝》。鲁迅的“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是用成熟的中年人的眼光去回忆童年的放风筝的感受,而莫砺锋则仍然以童年视角和感受来摹写历史现场的风景和人物,更符合历史真实的再现。这种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在什么人生阶段说出什么样的话,呈现什么样的思维,这样的意识伴随着传主的成长历程,按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成熟,一直贯穿在作品始终,这不能不说是对现有的非虚构散文的一种形式方法上的挑战。
这部作品书写人和事的故事,可以切割成几大板块: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高中时代、插队时代、流浪与高考时代。《浮生琐忆》之所以让我每读一篇都会产生共鸣,就是因为在莫砺锋的人生成长道路上,同样有着我亦步亦趋的足迹,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脚印,我在这部书里找到了亲密的兄长,他似乎从小就在与我促膝长谈,神交了七十年。
莫砺锋从小就在苏州长大,而我恰恰就是出生在苏州阊门的苏南公署家属宿舍里。他父亲是璜泾供销社的一名会计,后来我才知道作者将璜泾改成“琼溪镇”的缘由,那是此书唯一虚构的地名,作为他生命起锚的港湾,那里却也是他和他家庭的伤心之地。我父亲当年是苏南公署供销合作总社的一名干部,经常到基层供销社调研。他有无到过璜泾,不得而知,倘若去过,说不定认识莫砺锋的爹爹莫兰薰先生呢,因为调研工作非从会计那里不能得到可靠的数据。作为中原河南籍的莫兰薰先生在旧时代里,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年方十六就投笔从戎,在军中磨炼,最终成为旧军队的校级军官。这让我想起自己十六岁投笔从农时的境遇,与此等父辈相比,我所经历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莫兰薰先生把读书成才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子女的身上,营造出了良好的家庭读书氛围,或许这才是莫砺锋和弟妹在逆境当中奋发图强的驱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莫老先生本人的不幸遭遇,将一个天才少年置身于困境之中,反而磨炼出了其子女在逆境中励志的性格,用优异的读书成绩,回报这个不幸家庭,成为家族的骄傲。
莫砺锋一九四九年四月生人,我比莫砺锋小三岁,在“老三届”当中,按正常年龄入学;他应该是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如果早读一年,六岁入学,也就是一九六七届高中生。我是六岁入学的,一九六七届初中毕业。然而,莫砺锋却是一九六六届的高中生,我想,他是不是跳级生?后来才知他早慧,五岁就上了小学,这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现象。五岁上学,尚未发蒙,就在学校和班级中成绩拔尖,初二就以满分的成绩获得了全县数学竞赛第一名,这样的学生,在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前报考大学,当然首选的是清华大学的理科。然而,命运给我们这一代人开了一个大大的历史玩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把成绩优秀的一九六六届高中生的美梦彻底粉碎了,却把那届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以及我们这一代懵懵懂懂的初中生,送进了“革命”狂欢的殿堂。殊不知,阶级斗争的那根弦早在前几年就在“政审”中更加绷紧了,高考“政审”是讲究血统的,成绩再优秀,“政审”不合格,未必就让你填写一流志愿。
工作认真,温文尔雅的莫兰薰先生,是最早一批被定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所以,在莫砺锋头上悬着的那柄达摩克利斯利剑,一直笼罩着他二三十年的读书学习生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之前,莫兰薰先生还“算是琼溪镇上较为有名气的文化人”,他喜欢诗歌,经常与莫砺锋一起探讨唐诗,也许从那时候起,喜欢数理化的莫砺锋就在无意识中,埋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种子。
莫氏父子深厚的感情从莫砺锋出生之时就牢牢地建立起来了,强烈的责任感,使莫兰薰先生把更多的爱和希望寄托在莫氏家族这位长子的身上,这是我们那一代多子女家庭中所鲜见的。
在“爹爹的故事”系列中,莫砺锋写到,因家庭变故,在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境遇中,家里实在无法养活刚出生的第四个女婴小毛,就想将她送给朋友寄养,犹豫再三的莫兰薰先生最后流着泪说:“再穷再苦,孩子还是在亲生父母家里过得好!我们就是讨饭也要一家人在一起!”读到这里,我泪如雨下,这比我童年读胡万春的自传体小说《骨肉》更伤心,因为故事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身上,过去我却毫不知晓。活生生的非虚构文字,字字戳进了我的心窝,文章最后写到爹爹被关进“群专”黑牢里,遍体鳞伤的父亲回家后大哭道:“要不是扔不下你们这些好儿女,我就死在里头了!”“原来爹爹熬刑不过,曾想打碎暖水瓶用玻璃割断喉管,但是想到我们兄妹四人,他终于挺过来了。……没想到七年之后他还是没能逃脱自杀的命运!”一家人抱头痛哭,苦难让出离愤怒的莫砺锋仰天叩问苍天:“为什么喜爱孩子也会成为人生的一种罪愆?为什么我们兄妹的存在就是一重罪愆?”这里的抒写,究竟是少年时代的童真的不解之惑,还是后来觉悟的一种佯谬和反讽的修辞手法呢?恐怕没有经历过那种境遇的读者,是无法体会到其中的甘苦的。
莫砺锋全家,摄于1963年。
前排左起:
姆妈、小毛、爹爹
(出自《浮生琐忆》)
这种在悲剧苦难中诞生的父子之情是无法言说的。莫砺锋在前文中写到,父亲一九六五年去苏州看望高二的儿子时,二人在拙政园附近的小馆子里,爹爹只叫了半斤米饭、一碗杂烩汤,还不停地赞美那一角钱一碗的汤里带猪毛的碎肉,却“又责骂它不值一角钱”,看到这里不禁让人心酸落泪,这种近于阿Q式的两重性格,正是源于时代悲剧投射在了一个善良父亲的背影上。所以,作为儿子的莫砺锋此时的感受,或比朱自清当年在南京火车站看着父亲的背影时的感情更加纯洁真挚:“我曾立志将来挣了工资后一定要把爹爹和姆妈都接到苏州,好好地陪他们游览虎丘、灵岩,并陪他们到松鹤楼那样的大饭店去吃一顿饭。”而这顿饭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兑现,未竟孝心的遗憾,让人刻骨铭心,所以,我都不忍再看那段莫砺锋为父亲送行的场景了。然而,巨大的家庭悲剧,只不过是时代汹涌波涛里的一朵浪花而已。
在《浮生琐忆》里,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段莫砺锋为爹爹扛牌子的描写:“第二天清晨,爹爹只好自己走去示众。我抢过爹爹手里的木牌扛在胸前,陪着他一同走到大石桥下。正是早市时分,观者如潮,我帮爹爹把木牌挂好,才挤出人群回家去。将近九点时,我又来到桥下,把木牌从爹爹脖子上取下来,接他回家。我们在半路上遇到邵根尼等一伙人,邵看到我扛着木牌,阴阳怪气地冷笑一声,说:‘真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濡湿了,思绪连绵。下乡插队时,我们也去宝应县城里观看过万人批斗大会,一个“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竟然敢于面对这惨烈的人生,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里,像这种家庭出身的子女,最多的就是恐惧,用沉默来回答一切是最好的选择。然而,还有一种叛逆的“革命者”,与“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回家责怪自己的父辈,认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是自己的不幸。更有甚者,为证明自己的清白,便“反戈一击”,揭发自己父母亲的“反动言行”,从而获得“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甚至带领一帮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去殴打自己的父母,以此“壮举”与家庭彻底决裂,公开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划清阶级界线,这样的范例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并不在少数。然而,像莫砺锋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能够挺身而出,做出如此异动,却是罕见的。除了勇气之外,它还需要深刻的历史洞见,归根到底,他认识到的是——人性才是克服和战胜一切的力量。虽然那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但是,人性的光辉毕竟冲破黑暗的云围,他率先用行动证明了这条千古不变的人类真理,这并不只是用简单的孝道就可以解释的心理现象,是现代文明中的人性、人道的力量驱使,让莫砺锋先行了一步。
莫砺锋双亲,摄于1948年
(出自《浮生琐忆
》
)
面对莫砺锋后来的一些关于传统文人的言行,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仁有些不解,读完这本迟来的书,我彻底消除了对他的误解——老莫是一条有思想的铮铮铁骨汉子!他在近期与我的简短私信中,清楚地表明了根植在他灵魂深处那亘古不变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意志。
《浮生琐忆》里写到了在那个动荡的“大革命”的时代,许多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时髦的带有红色色彩之名,甚至把姓氏也改掉,而莫砺锋却坚定地说:“我不想改什么名字,便强调我姓‘莫’,绝不可能把名字改成‘向东’或‘革命’,我仍然保留着爹爹为我起的旧名字。”是啊,只有在此时此刻,砺锋才能彰显出傲骨的锋芒。
我十分能够理解莫砺锋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心灵创伤,这也是我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创痛,虽然没有莫氏家族那样艰难困苦,却也时时有一团团黑云罩在我的头顶。说实话,在我的心灵中,那时更多的是恐惧,没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在《浮生琐忆》中读到爹爹的故事以及家庭落难的情形时,我竟凝泪无语,自惭形秽了。而莫砺锋却是一个大智大勇的时代叛逆者,一个思想的先行者。
“停课闹革命”的时候,莫砺锋回到乡下,显然是属于“逍遥派”,“不断有消息从苏州传来,……我的粮油关系在苏州,我回家以来已经一连几个月没领到粮票和助学金了,少几元钱也就算了,没有粮票可怎么办呢?我很想立即到苏州去一次,可是爹爹和姆妈不肯让我去冒险,于是又等了一个月。”咦嘻,不关心“革命”形势,只担心自己生计的莫砺锋,居然没有像阿Q那样“同去”革命意念,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异数。读到这里,我想到的却是鲁迅先生的另一篇小说《风波》,写到七斤嫂在七斤从绍兴城里回乡时,匆忙问道:“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七斤的回答倒是有深意的:“我想皇帝一定不坐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尽管后来莫砺锋如七斤一样去了苏州城里,但是,心境却是大不同的。当他看到满目疮痍的“武斗”残骸,如同一个从战争废墟上走过的“局外人”,他只心疼他的校园,只可惜他的读书生涯:“我们在苏州待了十来天,天天看着那满目疮痍的校园,百感交集。”至此,我看到的是一个被时代抛弃,而独立存世的大写的青年“读书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