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莎·纳斯鲍姆
文︱钱一栋
杰斐逊人文讲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创立,被认为是“联邦政府向人文领域杰出成果授予的最高荣誉”。讲座始于1972年,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972)、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2000)、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2007),乃至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2013)都曾受邀发表演讲。
今年的主讲人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纳斯鲍姆。在古典学、政治哲学、法学诸领域,纳斯鲍姆声名卓著。作为自由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她深入分析过古希腊罗马世界中的运气、德性和情感结构,这种分析连接着她对当代世界的思考。近年来,纳斯鲍姆的声望不断攀升,约翰·洛克讲座(2014)、京都赏(2016)等人文领域顶级荣誉都被她收入囊中,杰斐逊人文讲座则是她的最新斩获。
5月1日,纳斯鲍姆作了题为“无力感与责备政治”(Powerles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Blame)的演讲,其核心话题依然是她近年来着重关注的愤怒(anger)。2016年,纳斯鲍姆出版了《愤怒和宽恕》(Anger and Forgiveness),而她尚未付梓的新书《恐惧的君主:一位哲学家对我们政治危机的观察》(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将进一步考察愤怒与恐惧的内在联系。此次演讲的内容大多来自这两本书,集中体现了她最近几年的工作。
━━━━━
愤怒不容于民主法治
━━━━━
在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俄瑞斯忒亚》(Oresteia)的结尾,雅典娜以法律制度取代了血腥的复仇循环,但她并没有驱逐复仇女神,而是许以尊位,说服她们加入城邦。按一般理解,雅典娜的举动证明了法律体制无法脱离复仇激情,复仇女神虽然受到法律的制约,但本质一如往昔,充满了黑暗的复仇欲。

复仇女神
对此,纳斯鲍姆在讲座伊始便提出了异议。根据她的解读,故事最后,复仇女神已经洗心革面,转变了性情。雅典娜劝说她们平复愤怒,以仁爱取代仇欲,她们接受了请求:不仅性情变得温和,外貌不再令人心生怖畏,就连名字也变成了仁慈女神(Eumenides)。
纳斯鲍姆强调,复仇女神的转变与从复仇到法治的转变一样重要,并且,前者是后者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埃斯库罗斯向我们表明,民主法律秩序不能只给报复套上牢笼,而必须从根本上将自己从嗜血残杀的非人之物,转变为能晓之以理的人性存在,转变为保护生命而非危害生命的存在。”
复仇的愤怒不容于民主法治。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愤怒是种非理性的女性气质,有害于人类幸福和民主制度,纳斯鲍姆深以为然:“我们要抵抗自己的愤怒,抑制它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纳斯鲍姆也坦言,这一观点颇为激进,难免会遭致口诛笔伐。很多人相信,关心正义的人,必定愤懑于不正义的行为。唯有愤怒才能捍卫自尊:不以愤怒回击羞辱和不义之人,定是懦弱而易受践踏之人。在刑事正义领域,如今最流行的学说是报复主义,即认为法律的惩罚应该表现出正义怒火的精神。更有人深信,愤怒是成功挑战严重不义的驱动力。但在纳斯鲍姆看来,坚持埃斯库罗斯对愤怒的怀疑主义态度依然是可能的: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同样在为自己和他人的尊严而战,而他们表现出了一种“非愤怒”的精神。
于是,纳斯鲍姆此次讲座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愤怒作出哲学分析,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从规范立场来看,愤怒有致命的缺陷?
━━━━━
愤怒,
或复仇的致命缺陷
━━━━━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没有愤怒。”纳斯鲍姆说。
因为愤怒的前提是认为有人对自己做了坏事。但很快,婴儿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我饿、我冷是由于别人没照顾好我。我们初临人世,脆弱无助,不得不依靠他人,但他人却不总行我们所欲之事,我们便责备他们。责备教会我们一个策略:靠大发脾气、制造噪音来实现自我的意愿。责备也表达了一种观点:我们要求什么,世界就得给什么,不这么做的都是坏人。抗议和责备本身可能是积极的,因为它们致力于人自我状况的改善。但报复的愤怒往往会侵染责备的念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使那些应受责备之人遭受痛苦。有人把这种念头看作正义感的起源,但纳斯鲍姆认为这与真正的正义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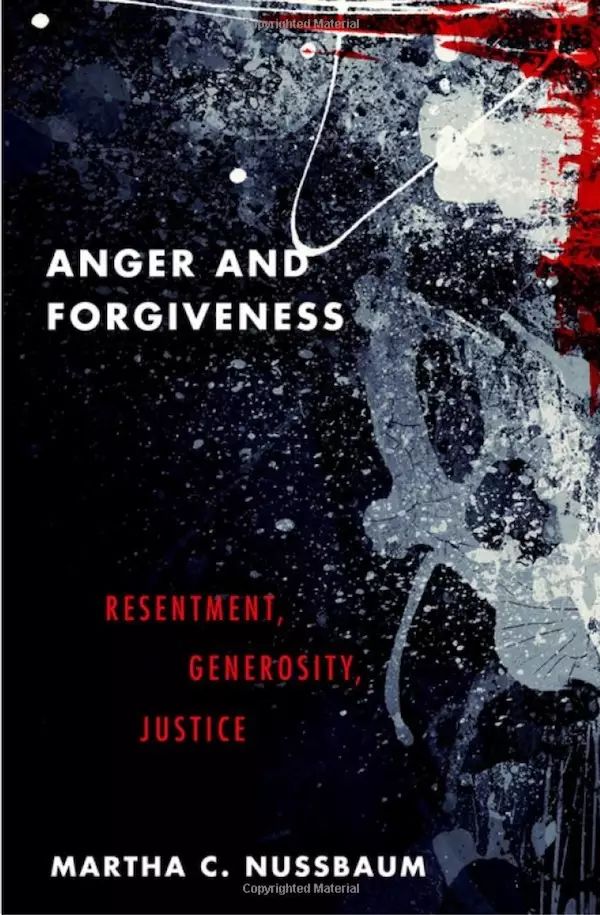
纳斯鲍姆:《愤怒和宽恕》
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愤怒是对我们在乎的人或物造成的伤害的一种反应,虽然愤怒是痛苦的,但也带有愉悦的报复愿望。现代心理学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愤怒分两个步骤:首先是痛苦,其次是希望报复。纳斯鲍姆强调,愤怒的两个部分可以分离,即可以因错误行为忿忿不平,却不抱有以牙还牙的念头。她相信存在一种不受报复欲干扰的“过渡愤怒”(Transition Anger),后者只有如下内容:“太不像话了!应该要做点什么才行!”过渡愤怒既表达了抗议,表明我们关切违反重要规范的行为,又面向未来:“它致力于发现解决之道,而非停留于对痛苦经历的回想。”就像父母常常因为孩子的错误行为而气愤,他们抗议错误,但不想施加报复,只希望孩子能在未来改正错误。
如果愤怒的问题在于复仇欲,那么报复究竟错在哪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可以用痛苦偿还痛苦。纳斯鲍姆认为这种想法犯了“偿还错误”。杀死杀人犯并不能挽回死者的生命;以痛苦回敬痛苦只能带来更多痛苦。甘地有言:“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盲目。”
此外,一些人愤怒的不是恶行本身,而是这些行为降低了作为受害者的自己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贬损了自己的荣誉。在这个意义上,报复确有几分作用:把犯错者降到相对低的位置,就把自己提升到了相对高的位置。但在纳斯鲍姆看来,这种思路错估了地位这一特殊价值的重要性。生活不只是荣誉之事,还关涉许多实质性事物:爱、正义、工作、家庭。着迷于地位是不安全感的征兆,还影响我们去关注更为重要的价值。
愤怒犯的第三种错误源于人们无法接受纯粹的意外。世界充满意外,“有时灾难仅仅是灾难,疾病和困苦仅仅是疾病和困苦”。面对意外,我们无法找出一个应受责备的对象。但我们有一种君主式的念头,希望整个世界都为我们服务,任何坏事都可归咎为某人的错误:当经济形势不好,找不到工作,我们责怪移民抢夺工作机会;当父母死在医院,我们相信这是医生医术不精造成的。这种念头蔓延到政治领域便产生了责备政治。问题难以解决,无力感带来了恐惧,而将问题归咎于他人既简便又舒心。然而,责备政治只会转移我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
尽管愤怒在规范层面问题多多,但纳斯鲍姆也不主张彻底抛弃愤怒。愤怒是恐惧的子嗣,是对严重伤害的反应,无法被伤害的人不会恐惧,无从愤怒。许多道德改革家劝诫世人不要在意自己无能为力之事,由此我们将无所畏惧。问题是,丧失恐惧也就丧失了爱。爱与恐惧的基础都是对在我们控制之外的人事的强烈关切。如果我们无法抛弃爱,就必须同时接受恐惧,接受愤怒。
到头来,纳斯鲍姆欣赏的是过渡愤怒——在抗议不正义的同时放弃偿还的幻想:“这一未来取向的策略包括对已经发生的错误行为的抗议,但不想归咎于谁……满怀希望地放眼未来,找出能使情况得到改善的计策……”她相信,埃斯库罗斯已洞察到了她的这一主张,而金博士不仅了解这一主张,还身体力行之。
━━━━━
理想政治秩序的情感基础:
纳斯鲍姆的意义
━━━━━
显然,在政治立场上,纳斯鲍姆是一位正统自由主义者。不过,她研究自由主义的学问进路颇为独特。
自由主义者往往是制度主义者。自由主义试图将政治建立在低俗而稳固的人性基础之上,如对暴死的恐惧,对享受的追逐。贪生怕死、趋利避害是无需教化的“自然人性”,它们稳固而强烈;古往今来的各种教化传统都想克服这种“自然”,将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但自由主义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试图在最低要求的人性基础之上,利用制度来构造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这种选择可能是策略性的,相信相反的做法注定失败,自由主义政治方案至少可以取得有限的成功;也可能基于怀疑主义立场,认为过往的教化传统只是特定的文化偏好,并无道理可言。于是,人性的教化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自我完善,在政治领域,有低俗而稳固的人性基础即可,最多再加一点正义感(罗尔斯)。是故自由主义者很少处理德性、情感话题,关注此类问题的往往是保守主义者。纳斯鲍姆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自由主义者,她深切关注政治秩序的情感基础:她对愤怒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分析便是一例。

罗尔斯
纳斯鲍姆的工作无疑可以开阔我们对理想政治图景的思考。
人治与法治,圣君贤相与理性制度……在漫画式的中西政治传统对比中,此类二元图景一直是大众意见的最大公约数。究其本质,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秩序把希望寄托于在位者的才德,而西方倾向以不依赖过高人性条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问题。且不论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中丰富的制度资源,单就西方而言,这一观点也太过简单。马基雅维利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但他却是一个“人治主义者”。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不厌其烦地教导君主,在无常命运和具体情境之下,应具备何种品性才能成就伟大。与文艺复兴的前辈相比,马基雅维利的新颖性体现在,他看到了单凭德性无法成事,有时必须诉诸武力和邪恶。但归根到底,他还是从君主品性这样一个“人治”视角出发来分析政治问题的。相较于马基雅维利所在的修辞学-人文主义传统,其对手、“愚昧落后”的经院哲学反倒更具制度思维。由此可见,西方不光是,也不该是中国现实问题的他者,真实的西方远为复杂。

马基雅维利
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什么?理想的政治秩序需要何种情感结构、人性基础?与具体结论相比,这类早已被遗忘的思考方式也许是纳斯鲍姆对我们的最大启发。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