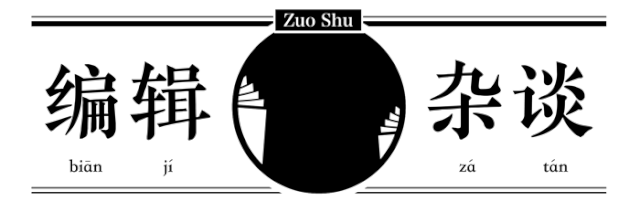
2019年北京国际书展期间的一个夜晚,一次聚会上,我和日本早川书房的编辑阿晶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喝酒。我们不知为什么谈论起一些非常天真的话题来,可能是因为我英语太差了,而且大家也都喝多了吧。他先客气地称赞我是一个fighter,然后谦称自己是一个liar,再进一步解释说,做出版嘛,大家都是在骗骗对方,也要骗自己,所以他是一个big liar。
我觉得这论点极为精彩,因为他用非常简单且反讽的语言便总结了出版的要义,不愧是在当年就把日本版《三体》卖出创纪录销量的文学编辑。“骗”指的是话术,就像任何行业的中间商,出版从来都是靠话术包装把东西卖出去的,区别只在于这个行业所贩卖的东西也是一种“话术”。
那么,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这个行业是否存在真实?以及这种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2020年是我在理想国工作的第九年,入编辑行当的第十二年。今年编辑的原创文学中,有四本书在年底榜单或销量上都取得了不俗的表现,是我工作经验中不曾有过的盛况,也使得今年显得意义非凡。依照出版顺序分别是:沈大成的小说集《小行星掉在下午》、路内的47万字长篇小说《雾行者》、林棹的小长篇《流溪》和郑执的小说集《仙症》。
虽然宏观来看,我们免不了要去谈论新冠疫情对于既有图书操作方式的改变,及其所加剧的行业困难,但从一个编辑的微观角度而言,我认为即使是疫情,也无法阻止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的发生。比如《小行星掉在下午》所收录的《盒人小姐》,因其对疫情下我们生存状况的神奇预言,立刻获得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不仅帮助这本书突破了疫情所造成的现实阻碍,还使得它迅速获得了更广阔区域内读者的认知。而《仙症》,本因疫情造成的嘉宾档期问题,连落地发布会都没做,却凭借作者《生吞》以来所积累的优良口碑和扎实的写作水准,保持了从9月出版至今每月都加印一次的稳健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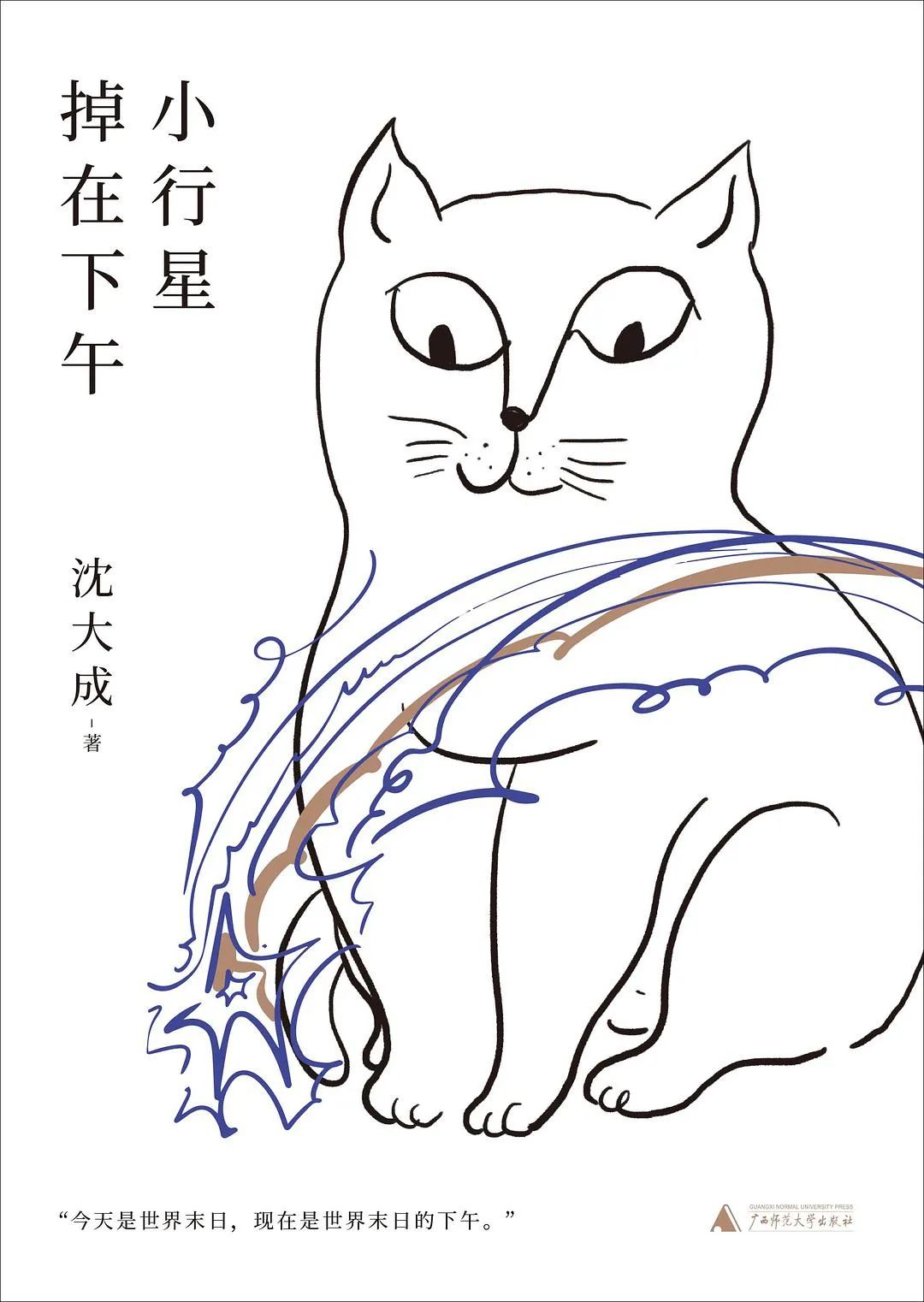
作者: 沈大成
出版社: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20-1
在我看来,
图书出版从来都不应是一个目标,而只能是一个结果
:书就好像是作者命运的延长线。每一本书,每一个作者,都各有其命运。那手感如此清晰,就像是在抚摸一匹鲜活的大动物。在我看来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真实。也是保持这种真实的意义之所在。
编辑是离书最近的人,只要静下心来,不出老千,每个编辑都可以触摸到所经手图书的那股真实的命运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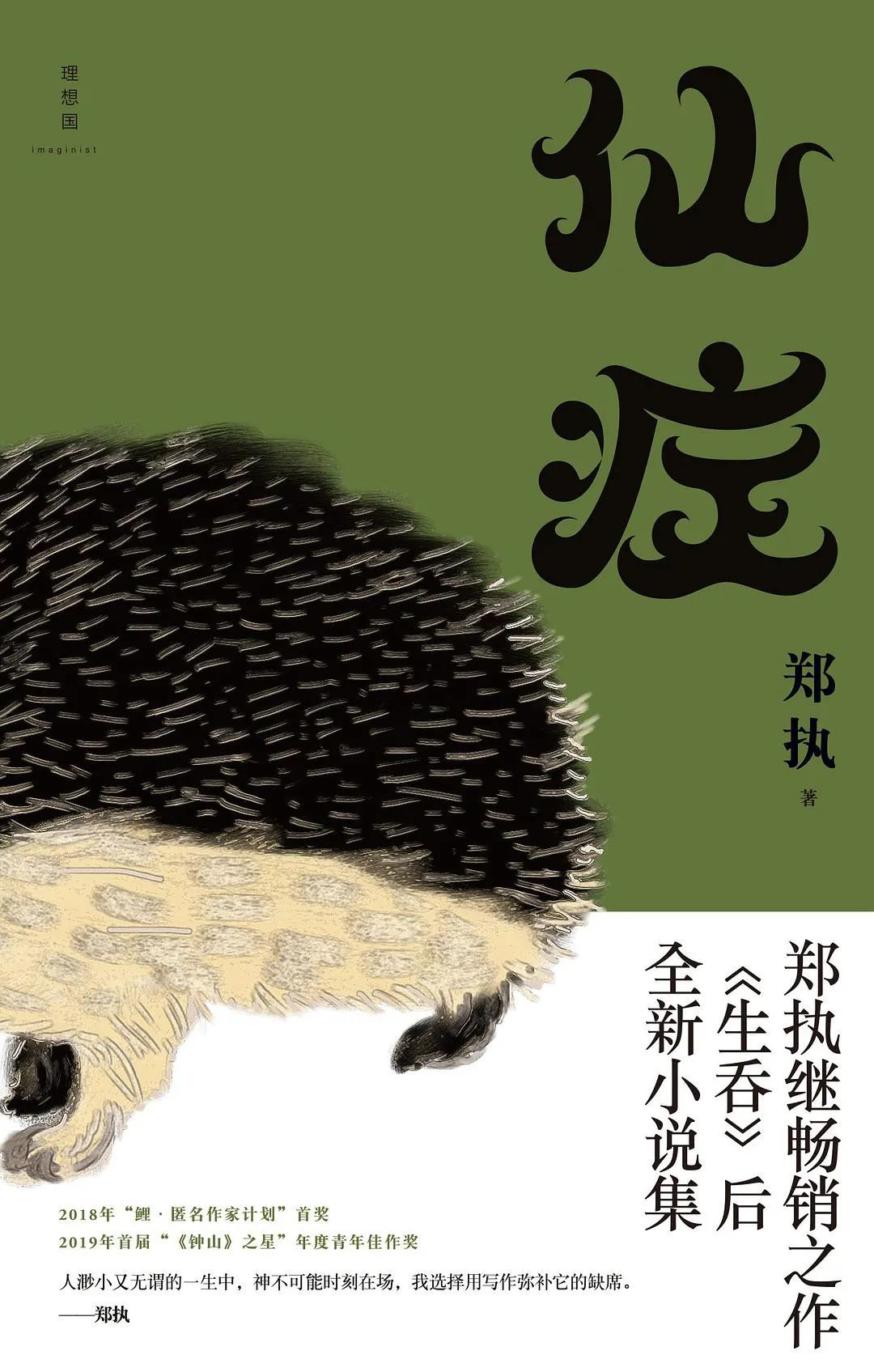
作者:
郑执
出版社: 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20-10
2020年11月上旬,我作为责编,因《雾行者》入选“深圳读书月”三十强被公司派往深圳出差。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发现这里温暖、潮湿,城市像是战胜了当地所有野性植物之后凭空出现的,宽阔的滨海道路又有点像加利福尼亚的梦境。我有一位作者在那里,是林棹。她十六岁时就已经在千禧年前后的地下文学论坛写作并小有名气,但今年才刚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就是上文提到的《流溪》。
或许说今年才第一次去深圳也是不准确的。2006年时,我是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的一名大二学生,在香港一家外汇黄金交易所实习,中间需要在罗湖口岸重新入境一次,那才是我第一次去深圳。那次实习结果让我觉得金融所关心的主体过于虚幻。钱本身什么都不是,仅是抽象了的欲望,并且除了自身之外,什么都不创造。
这世上是否存在一种切实的、具体的、可以真实感知的东西呢?之后我常逃学到北京去。我第一次去了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那时“图书沙龙”这个词还极为新鲜。冬夜里,棉布帘子掀开,雾和灰尘的味道留在外面,室内也是夜色,因为正在放电影。有烟囱被烧热时的铁的味道,眼镜一下子水汽弥漫,依稀可辨长条形的空间里挤满了站着的年轻人,投影上放着的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大家就这么人贴人地站着看完这部晦涩的电影,记得放映之后还有不少于三个回合的讨论和发言。我则急于希望自己能理解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
转眼间,我们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厌恶晦涩和非常规的时代,这从一些书的豆瓣短评就可以看出端倪。网友们喜欢说书的某种写法毫无必要、没有意义。那么,我又想知道的是,世界上究竟什么才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说回2020年11月的深圳和林棹。我不久前刚在北京见过她,因为她凭借《流溪》入围了本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短名单。在颁奖仪式之后的晚宴上,她说起自己几乎跟深圳同龄。而深圳的一切都是人造的。她问我,你的乡愁之味是什么?我说(同时觉得有点煞风景),煎饼果子……她说她是麦当劳。我就顿时觉得拥有煎饼果子的人生也还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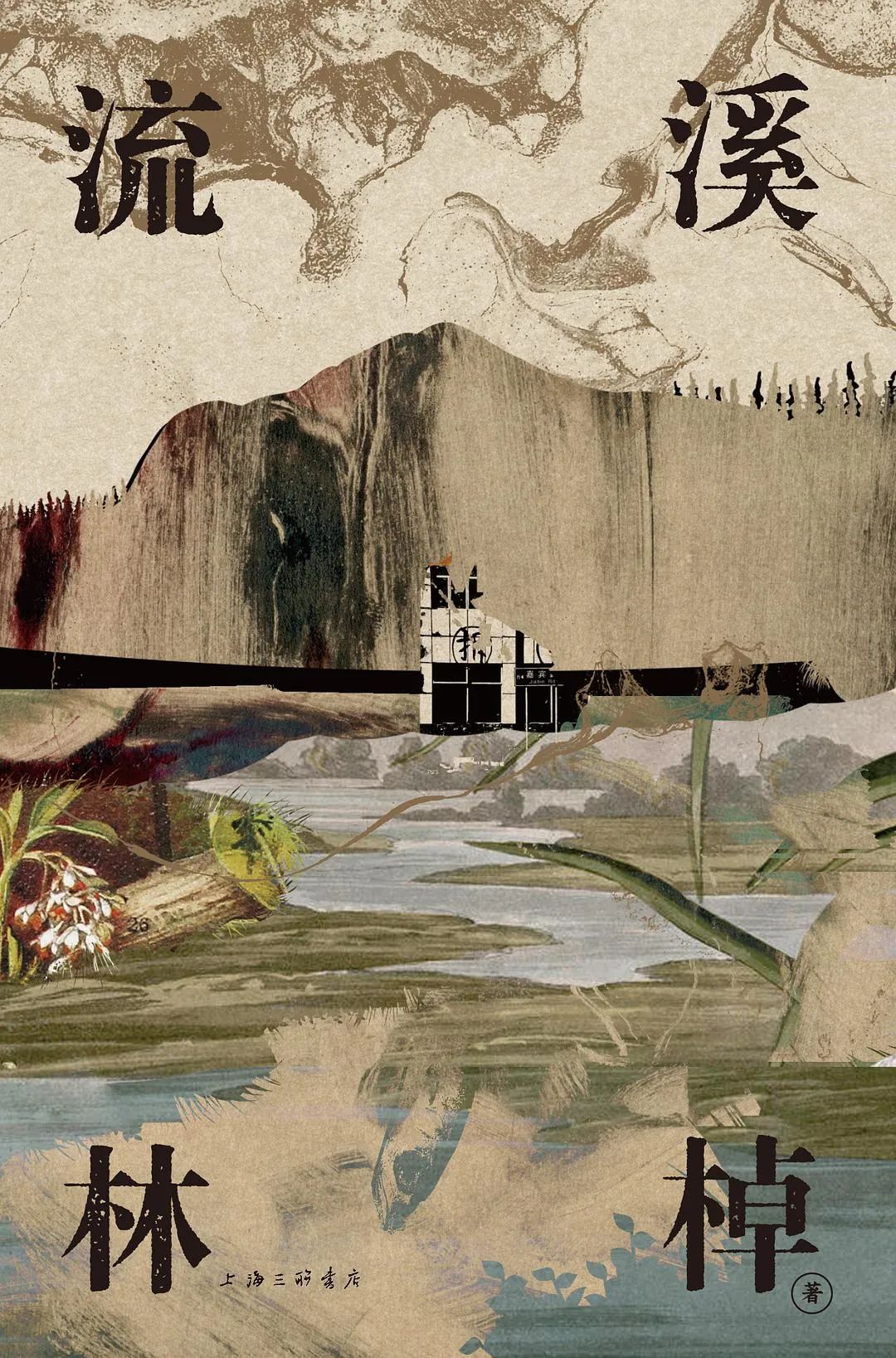
作者:
林棹
出版社: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20-4
林棹在自己的老家看起来跟在北京时有点不太一样。显得比较凶悍。而且我发现她在深圳也不大认得路,我想跟着她坐地铁回酒店,结果进入了一个貌似地铁、但实则是废弃的地下通道的地方,我们只好又爬出来重新找路。但她对于一些具有心理意义的地点掌握得准确,比如在《流溪》里也写到过的蔡屋围(刚被拆迁掉,只剩一堆瓦砾),或者哪里的高层景观位能俯瞰到一些重要景色等,所以我判定她基本上是个在梦的维度里行走的人。由此也有点担心她在现实世界的安全。
就在那个可以俯瞰到深圳与香港边界、蔡屋围遗迹,以及罗湖口岸的高层景观茶座里,她问了我一个经典的林棹式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神灵,城市的各个地方任你可选,你要住在哪里?也正如她的小说一样,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思考这个问题(或阅读她小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到自己的灵魂既出离了自我,又返回到了自我的深处。这就是她的小说所能帮我们抵达的地方。与何者必要、何者没必要无关。
后来我们又去了另一处她不会迷路的地方,是一个过了旅游季的海滩乐园。夏天啤酒品牌商搭建的简易凉亭还遗留在那里,捕梦网迎风飘荡。那个下午所有出没在那片海滩上的人在我这个北方女人看来都十分可疑,男人们看起来个个像亡命之徒,一男一女的则都像是私奔的情侣。但是林棹告诉我这就是住在附近出来遛弯的当地人。在那个时刻,我忽然感知到自己确实身处于南中国的边缘了,这里的风物跟我所熟悉的北方如此不同。大家(包括林棹自己)看起来都像是抛弃了什么之后流窜至此的(未必真的如此,只是我的幻想)。
那天的海浪很舒缓,充满了自由和闲暇的感觉,好像可以从这里驾一叶轻舟直划到银河上去。属于北方的、忙碌焦灼的一切忽然都变得遥远。这情景也像她的书,但更像她刚写好的第二本长篇,那里有段讲一个乞儿出身的画师带着他的怪胎青蛙朋友在黄埔望大船,两人用娴静的语言讨论着海的那边是什么这一原始问题。
2018年时,我曾做过《鲤》的“匿名作家计划”,在发布会上,嘉宾们主要讨论的便是隐去作者的姓名阅读小说是否可能。我当时私下在心里想,或许终归是不可能的吧。名字就像坐标,标记了书和作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直到今年的这本《流溪》,我才算是碰上了一个真正“匿名”的作者。而这次的事实表明,匿名是可能的。书刚出版的前三个月,销售十分惨淡,因为是毫无名气的作者,写法又奇特。有同行跟我讲,觉得完全读不懂,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本书。目前,在出版8个月之后,这样一部确实存在了一定阅读门槛的纯文学作品已经印过四刷,印量近两万册。这本书写二十岁少女自我杀戮与自我捡拾历程的小说切实地打动了许多年轻读者的心。
我不禁想,
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人员会被自己的所谓“职业判断”带偏多少;作为出版者的我们,有时会多么过度估算读者的接受力,有时又会多么过度轻视读者的理解力。
我相信那位同行并非看不懂这本书,只是它异于当下潮流的书写方式让他感到不适。然而,不平庸的文学不就是该有着自己独特的脉络与步调?
在讲了书的命运之后,我又想谈一谈作为编辑的命运。《雾行者》对我来说是一本命运之书。而且在所有对这本书的阅读中,我可能是最奇怪的。我首先读到的是第二章,因为那是当时路内唯一肯给我们看的章节。那是2019年5月,我和中心领导又去了一趟上海,纠缠路内,试图拿到《雾行者》的稿子。
在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上,路内终于给我们发了小说的第二章(事后他解释说最开始只肯给第二章是因为这章写得晦涩,而第一章是常规小说的写法,怕我们顺着读到第二章的时会觉得不好卖而临时去叫他改稿)。我想我永远都会记住第二章开头的这句话:“写小说的年代,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像舌尖舔到铁锈,奇异的味道。那些写小说的年轻人舌尖上都留有铁的滋味。”但是很奇怪,我并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那次我在天津临时决定下车,因为想顺路回家看爸妈。高铁停在天津南站,一个荒凉的刚刚建好的站台,我此前从未来过。只记得那天的太阳很脏,猛烈地照着我,感觉狼狈,像是在长久的奔跑之后终于抵达了世界的尽头。但依旧奇怪的是,这里并不是世界的尽头,而是我出生并一直生活到二十岁的城市。仅仅因为这里是之前没来过的郊区,显得有点陌生而已。
《雾行者》对我而言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如果用客观的语调来讲,我会说,这本书讲了一群悬浮着的人,他们没有可以回去的家乡,也没有时间,甚至连记忆都在被逐渐抹除,所以总体而言,他们是一群被诅咒的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居然在这本书里,在某个时刻,可以获得一种真实存在的安慰。
如果用主观的语调来讲,我会说,这本书写的就是我,而它也切实地安慰了我。我推断这种安慰的获得可能是因为路内致密的写法,使得全书像一张质地厚实的大网,包裹住了所有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下坠的人。那么,我又想再问的是,如果这样的安慰的取得是与文本的密度相关的,那么谁又可以判定哪一部分的书写是有必要、有意义的,哪一部分的书写是没必要、没意义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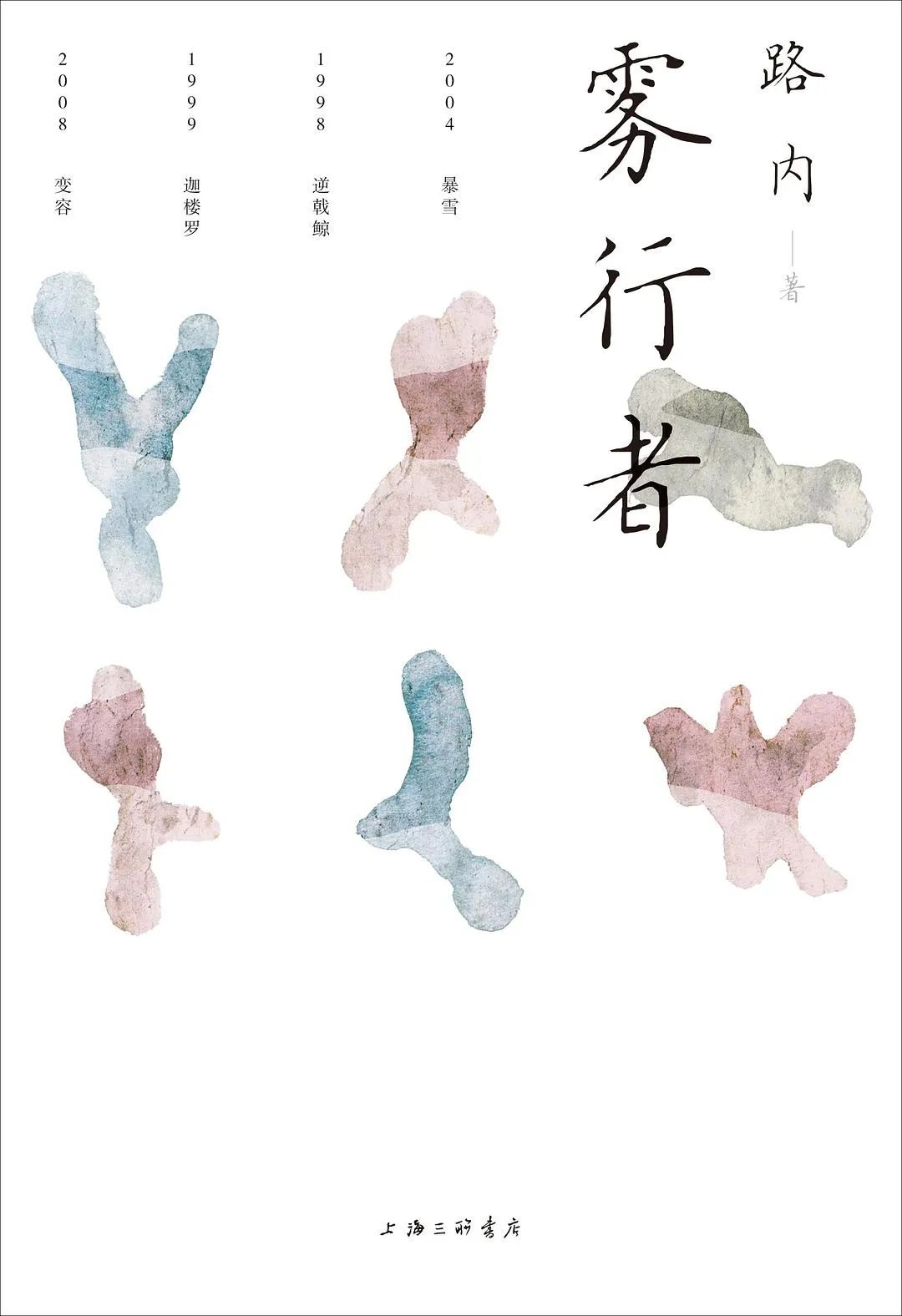
作者:
路内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20-1

















